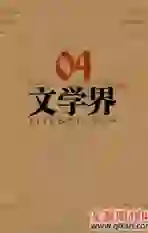红薯的记忆
2009-04-26杨林
杨 林
至今我依然记得祖父吃红薯的样子。深秋的午后,祖父从外面忙活回来,用搭拉在肩上的那块长灰白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来到灶屋,伸出有轻微抖索的手取下挂在头顶的饭箕,掀开盖饭的丝瓜络网,里面有早晨没吃完的剩饭和与饭一起蒸熟的红薯。祖父从中拿了几个熟红薯握在手里,然后又将丝瓜络盖上,将饭箕挂回原处。
祖父腾空了的另一只手拿起一个熟红薯送进嘴里,那红薯皮上还粘着饭粒。他一口能将红薯咬一半,腮帮子就鼓动起来。午后寂静的灶屋里响起了“吧唧、吧唧”的咀嚼声。
“爷爷!你吃红薯怎么不剥皮的啊?”我看祖父吃得香,连皮都没有去掉就吃而问道。
平时母亲教导我吃红薯要将红薯皮剥了再吃。母亲每次去沅水边那个城市探望父亲回来,都会带回来一些新鲜的生活习惯,也许她在城市中见人吃红薯一定是要剥皮的,所以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要求我们这样做。
祖父见我发问,笑着对我说:“皮也可以吃的呢。”他一边吃,一边还将红薯上沾的饭粒揽进嘴里,然后眯起眼睛对我做一个笑脸。
太祖母见到祖父吃相,定会说祖父像个“饿痨倌”,犹如前世没吃过饭一样。太祖母说完这句话后,会叹气,那双有眼疾的眼睛会黯然流泪,不知道是眼疾的原因,还是想起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祖父在今生是挨过饿的,差点在那次饥荒中饿死,是红薯救了他的命。
太祖母说,在大炼钢铁那会,需要大量的木炭,祖父被生产队派到深山里烧炭。那已经是进入了深冬的季节,可是烧碳的人们身上只有单薄的衣裳,脚上穿的是草鞋。最要命的是吃不饱,供给的食物与劳动需要的能量严重的不平衡。上山砍柴,筑窑、还要将烧好的碳挑着走几十里送往指定的地点。那时一天的口粮只够一顿饱饭,在半饥半饱的情况下,干着超强度的劳动,祖父的身体累垮了。在完成了烧碳的任务后,祖父拖着疾病与饥饿的身躯回到家中。
那个冬日阴冷的下午,太祖母在屋里的火箱里坐着,带着还在襁褓里的孙子,听到屋外有人剧烈咳嗽,还有一声强烈撞击木板壁的声音。她起身问:“是谁啊?莫将板壁撞烂了!”外面有人回答:“是我!”声音低沉、无力。太祖母觉得那声音有点像祖父的,但疑惑儿子的声音怎么会变成这样了。于是她继续问:“是细毛崽嘛?”得到了肯定后,才抱着孙子出来看。此刻,祖父正坐在屋檐下的木板凳上,无力的靠着板壁,面呈灰土色,身上抖索着,头发稀乱,颧骨突出老高,想必身上也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衣服已被荆棘划得像烂抹布,大冬天里只穿着两件土布单衣,一条土布裤子,脚上穿的是草鞋。随祖父挑回来的装炭箩筐,又黑又破,斜在那里。
太祖母见此情形,早已抹起了眼泪,赶紧把祖父牵进灶屋里,将火塘里柴灰扒开,露出里面的火种,覆上松叶,将火点燃,让祖父取暖。
可是屋里实在拿不出食物可以让祖父填饱一下肚子,或是找到一点大米为他熬点稀饭……那时整个中国农村都处在人民公社时期,搞的是大锅饭,社员们一起吃饭、一起下地干活,吃饭都是定量的,个人哪里还有机会私藏粮食?何况那时我家为了响应号召,已经放弃了单门独户老屋,搬到生产队里,一举一动都处在别人的目光之下。
祖父不能出工了,只能躺在屋里,家人知道是劳累和饥饿所致,但是却苦于没有办法。作为病号的祖父,不可能享受出工社员的饮食标准,供应的饭只是全劳力的一半,可祖父因为烧碳,超强度的劳动已经使他的身体透支,出现了营养性水肿。若再不弄点吃的改善一下,他就有可能被饥饿和病痛夺去生命。可是去哪里多弄一些食物呢?只有三十多岁的祖父像残烛的老人一样在瑟瑟冬风中发抖。
祖父还是生存了下来,得益于一筐红薯。祖父惟一的姐姐给他带来了一筐救命的红薯。我的那位姑婆在生产队秋收后的红薯地里,如筛子筛过一般找到了这筐红薯,即使那些红薯个儿很小,她都一一收贮,以备饥荒。可她得知弟弟情况后,在一个深夜背着红薯走了几十里地来到了苗田(我老家所在地),悄悄地敲开了房门。家人见此,感念流泪。姑婆却还来不及与家人说上几句话后又匆匆消失在夜色中。
那一筐红薯救了祖父的一条命。白天,不用出工的太祖母趁生产队社员出工后,悄悄地将藏在床底下的红薯摸出几个,怀揣在衣袖里来到灶屋。坐在火塘边的凳子上,带着孙子假装取暖,快速地将火塘里的灰扒开,将红薯掩埋在热灰里。柴火燃烧后的余热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将红薯烤熟。当时间差不多后,太祖母悄悄的去火塘中取出红薯拿给祖父吃。太祖母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小孩子,我的姑姑和二叔。二叔在襁褓中,姑姑已经几岁了,大人都吃不饱,何况她一个小孩子,见了熟红薯自然会哭闹着要吃。太祖母只好每次将一个红薯掰一小半下来塞到她的嘴里,悄悄的告诉她别做声,快点吃。
当那一筐红薯吃完了后,祖父逐渐从劳疾和饥饿中走了出来。
在多年以后,太祖母都念念不忘那筐红薯,她说要不是那筐红薯,祖父也许就走完人生路了。而我的祖父亦感恩红薯,所以他喜欢吃红薯,也爱种红薯。
在我懂事的时候,虽然已经分田到户,但是家中只是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依然还要为粮食吃不到来年而发愁。为了解决这些困顿,家人只好开荒种植红薯、土豆和青菜,以做补充。那时我家分别在老家屋场两边的山坡上凿了两口像竖井一样的地窖,地窖上小下宽,上面用杉木皮盖好,深约四五米,需要架着楼梯才能下去,里面储存着的是红薯、土豆。
在秋冬的日子里,隔一星期左右,祖父就会扛着楼梯,提着箩筐去地窖取红薯。取出的这些红薯一半用来喂养家禽家畜;还有一半,则每天洗几个与米同煮,饭熟后,红薯也熟了。家人吃得七八成饱的时候,就吃红薯将肚子填实。在乡下,一般中午不吃午饭,饿了就去饭箕里拿几个熟红薯充饥。
那时将红薯、土豆、玉米、高粱都称为杂粮。杂粮的吃法很多,也很简单,如将红薯或土豆切成片,放进水里煮,煮熟后,放些葱花、盐,味道也很好;将红薯磨浆与米粉混合做成粑粑,也很甜;如玉米和高粱用石磨磨成粉和糯米打成糍粑,一种金黄、一种深红,对儿时的我很是有诱惑力;有时在锅里烧上水,放少量的米,待米熟后,放入泡好的干青菜煮烂,调上一点盐,被称为烂饭,烂饭是春夏之交那段时节里一家人吃得最多的早饭。
在那些困顿的年代里,家里养的家畜、家禽也怪可怜,人都为粮食发愁,它们只能吃个半饱了,且都只能吃猪食。动物们开饭的时候,祖母将煮好猪食分成两盆,鸡、鸭、狗享用一盆。到开饭时可真热闹,狗双脚趴在盆沿上,占据了半壁江山,让鸡、鸭都不敢上前,不停地鸣叫。狗依仗自己蛮横将猪食中的红薯、土豆,或稀少的饭粒全挑来吃了,鸡、鸭只好任之,无可奈何;也有不惧狗的一两只鸡不时来到盆子前,啄食几口。当狗吃得差不多的时候,鸡、鸭才一窝蜂涌到盆前,来个大扫荡。由于家禽多,盆子里的猪食被啄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些细微的谷糠沾在盆子上。鸡、鸭吃不饱也没办法,剩下的只有靠自己了,所以它们在野外、稻田里觅食格外起劲。而猪的光景就好些了,因是重点喂养的对象,在猪栏里独自享用一盆,吃饱了便睡,不用和其它家禽、家畜抢食。由于少粮食,家禽、家畜生长得并不快,一年到头,还是皮包骨头。
每年插完晚稻秧,祖父就开始忙着种红薯了。这种习惯他延续了几十年,尽管后来已经不再为粮食发愁,过上了比较宽裕的日子,祖父依然要种很多的红薯。红薯比那些猪草有营养多了,红薯藤也是猪上好的饲料。每年要喂两头肥猪,一头卖钱,另一头用于过年,招待回家的儿孙们。
祖父会在二、三月间从地窖中取出些薯种,埋在一小块地里,几番春雨过后,红薯便开始发芽长藤后了。过了夏至,祖父就将红薯藤割回来,与祖母一起在家里用剪刀剪成一节一节,然后用簸箕挑着来到翻好的地里。祖父在贫瘠的土地上用锄头掏沟,祖母则跟在后面将那一节节的红薯藤放在沟里,然后祖父再回来用锄头扒土将红薯藤埋上。自从我认识红薯开始,就被红薯顽强的生命力折服,栽在地里的红薯藤,经过初夏太阳火一般的炙烤,当你以为那些种植的藤已经枯死的时候,在一场雷雨过后,红薯藤便让你感到意外地萌出新芽、新叶,并疯长起来。期间可见祖父会在大热天里、太阳下戴着斗笠为红薯除一下草;在雨后去割一些红薯藤回来喂猪。直到阴历的十月后,他便挑着箩筐和祖母去挖红薯了,那时红薯藤已经割掉了,对着那些红薯蔸一锄头下去,用力一拉,薯根系着红薯被挖了出来。看着满地丰收的红薯,祖父满面微笑。 一次与一位搞农业研究的朋友聊到红薯,她告诉我红薯还有紫色的。开始我还不相信,后来一查,果然如此。那一刻我在想,若祖父还在世,我一定给他弄几棵紫色的红薯种一种,他一定会很喜欢。
责任编辑:远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