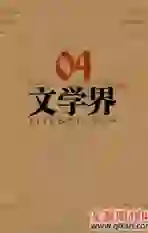天那水
2009-04-26韩三省
韩三省
下午两点,上班铃响了两遍。
上班铃装在男宿舍和女宿舍中间那堵墙上。每个人走进宿舍前,抬起头都能看见这个黑色的铃铛。这个莫明其妙的主意,来源于人事主管董寒。作为这个厂惟一坐办公室就能拿工资的主管,董寒在工人们面前曾这样夸口,他说他所有的主意,都建立在人性化之上。还是生产车间的唐彩云格外有心肝。唐彩云是个益阳姑娘,普通话里头有股浓重的益阳腔。跟她要好的几个工友,老是学她的口气,把吃饭说成掐碗。那天下班,大家伙吃完饭一起往宿舍赶。当然跟附近其它的工厂一样,这个厂为工人提供的宿舍是集体宿舍。不过在经过了一天手脚不停的劳动之后,再集体的集体宿舍,恐怕你也会争先恐后往你的床铺赶。许多人在宿舍前面,停下了步子。厂里的电工张重阳,那时正搭着一条凳子,凳子就放在男宿舍和女宿舍中间那堵墙旁。他的穿黑色袜子的脚掌,看起来很小心地撑在凳面上。大家都看着张重阳,张重阳也双手用力,将一样不知什么东西往墙里按。后来张重阳从凳上跳下来,大家才看清这是一个黑色的玩意。最开始发表看法的人说,这是一盏壁灯。他刚这样说完,马上就有人否决他,说这要是壁灯,黑夜来临的时候,肯定起不到任何作用。后来又有人说,这是个用来装饰墙面的玩意。也不知是谁,用一种很有把握的口气说,这是一个监视器。这句话说完很久,没有一个人出声。直到这时,张重阳才得意洋洋张开嘴巴,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电子铃铛,每天到了上班的时候,它就会嘀嘀嘀地叫喊。有人恍然大悟地说什么电子铃铛,讲得直接点不就是个上班铃。有人还好奇地问,既然是上班铃,为什么不装在上班的地方?这人的话音刚落,唐彩云发出了一个哧的笑声。唐彩云说这还不简单,将这个主意想出来的人,是怕我们听不见铃声,误了上班。
上班铃响第一遍,第一个从宿舍冲出来的准是张重阳。中午休息的时候,厂里的机器也要休息。张重阳迈开步子,来到机电房。厂里头所有重要机器的开关,几乎都躺在机电房。他眯着眼睛,看也不看,第一个打开的肯定是生产车间的气泵开关。只有将气打足了,车间的喷枪,才会有足够的力气把油喷到玩具娃娃们身上。张重阳从机电房出来,上班铃已经响过两遍。机电房旁边就是生产车间,这时候的车间,已经像一锅开得不能再开的水,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所有的工人都坐在工位上,他们一边挥舞着喷枪,一边将玩具娃娃们抵在模具上。各种颜色的油漆从枪嘴里跑出来,毫不客气地冲向模具。然后将玩具娃娃从模具下拿出来,油漆就透过模具的模版,贴在了玩具娃娃身上。张重阳从车间门前走过,眼睛朝里边晃了晃。他的眼睛从车间收回来,看见了前面走来的生产主管李广。张重阳大大咧咧问李广,你们车间又来了一个新的女娃?张重阳是四川人,坚持管所有的女孩都叫女娃。李广的头低着,好像没有看见张重阳。至于张重阳的问题,李广表现得压根没有听见。张重阳不由笑了,他的笑有些自我解嘲的味道。接下来他又望着前面,不知道是不是告诉自己,这个女娃还挺漂亮!
张重阳说的女娃,其实就是坐在唐彩云旁边的姑娘。这个姑娘现在正低着头,一声不吭对付着手中的喷枪和玩具娃娃。可是她胸前的工牌出卖了她,她的工牌告诉我,她的名字叫胡水兰,年龄那一栏里,估计是董寒的文秘,用黑色的圆珠笔填了个阿拉伯数字十八。至于其它更详细的资料,我只能抱歉地说,她的工牌又不是人事档案表。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就像张重阳说得那样,胡水兰真的挺漂亮。胡水兰有双水汪汪的眼睛,她的眉毛又细又长,就像我们常常在电影里看到的女主角那样。她还有个小巧的嘴巴,这个小嘴现在被她抿得更小了。估计她遇到了什么困难,她就这样抿着嘴巴,一只手用力扣着喷枪,另一只手用力抵着玩具娃娃。她真的很费了一些力气,这点我看出来了。她头顶的车间上空,挂着八个吊扇,八个吊扇在呼啦啦转,可是她额上挂着一层汗,她背上的衣服也被汗浸湿了。那是件蓝色的、质地实在不怎么好的工衣,坐在她旁边的工人都穿这种工衣。她把玩具娃娃从模具后拿出,再把它放到旁边的盘子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这只手了。她的五个手指微微向上,好像要将它伸直都有些困难。其中的两个手指,指头中间的位置,还红红地起了两个水泡。她放下枪,用右手摸了摸这些水泡。这些刚刚起来的水泡,在她的抚摸下,疼得让她的整个左手都一颤。她停止抚摸,将右手拿开,又捡起枪,开始将枪里的油喷到玩具娃娃身上。
这样喷了很久,胡水兰将一个玩具娃娃放进盘子,再次放下了枪。她这次没有抚摸水泡,她只是伸开左手,看了看手上的水泡——水泡在长时间的、上顶玩具娃娃的作用力中,早已经变得溃烂——不过她也就看了看,然后她犹犹豫豫站起来,绕过盘子,直接向车间外面走去。她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她的脚踢翻了一桶放在地上的油漆。这桶油漆放在生产车间的过道上。这桶油漆旁边,还放着好几桶其它颜色的油漆。其中的一桶油漆桶口,横放着一根沾满油漆、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的金属丝。你要是在玩具厂做过,肯定知道这些油漆和金属丝为什么要聚在一起。让它们聚在一起的人是李广,李广要利用这些油漆,调出另一种颜色的油漆。李广在调的中途,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身去了办公室。他从办公室里出来,胡水兰刚好踢翻了油漆。那桶红色的油漆就像一朵花,它在嘭的一声后使劲地贴着地面绽放,不一会就在胡水兰脚边流了一大摊。
谁也不知道李广怎么回事,李广像个疯子,只见他三步两步跨过来,劈头盖脸就这么很大声问胡水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刚才到哪去了?胡水兰将头低下,她都不敢看激动得满脸通红的李广,她嗫嗫嚅嚅地回答说,我我我我我,我去了卫生间。李广还是那么大声,你去卫生间也不跟我说一声,你不跟我说一声我怎么知道你干什么去了?我还以为你打算甩手不干了!李广这么说的时候,其他的工人都抬起了头。他们的目光从面前的模具,刷地一声聚焦到了李广和胡水兰身上。胡水兰还是低着头,一个字都没有。李广猛地踢了一下那个已经泼得只剩下一个底的红油漆桶,红油漆桶一路从李广脚下,骨碌碌滚到了一个工人的脚下。它在滚动的过程中,发出了一种咚咚咚的、很不识时务的声音。同时它还将残留在桶里的那点油漆,毫无规则地淌到了地面上。李广的脸板得像一块不锈钢。李广接着很过分地说了一句话。李广说你赶快给我收拾干净地面,要收拾得没有一点油漆。
这句话说完,李广转过身子,丢下胡水兰去了办公室。不知道哪个工人突然咳嗽了一声。一直将脖子伸得很长的唐彩云,这时也豁地一下站起来。不过她想了想,接着又豁地一下,坐在了刚才离开的凳子上。唐彩云的这个动作,惹得许多人都将头扭到她所在的方向。胡水兰也扭过头,看了看唐彩云。将头再次扭过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胡水兰没有任何表示。她只是站在那里,将头低下。她的上边的牙齿还悄悄地咬着下边嘴唇。她的左手和右手在不觉间已经十指交叉,两只手的掌心不停来回搓动。她这样搓了一会,两只手从空中相互放开。她在大家的注视中,一路向车间左侧走去。车间左侧的靠墙位置,放着几把扫把,一个垃圾铲,还有两个拖把。她抓起一把扫把和垃圾铲,还提着一个拖把,转过身走向她踢翻油漆的地方。
十几分钟后,地上的油漆被胡水兰处理得差不多了。不过那块湿湿的地面上,还有好几块顽固的、不肯被胡水兰轻易收拾的墨红色痕迹。胡水兰又转过身,放好了扫把垃圾铲和拖把。她再回来的时候,两只手小心地捧着一杯天那水。杯里的天那水挥发出一种强烈的、类似于敌敌畏的气味。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在玩具厂做过,肯定知道天那水是油漆的克星。胡水兰放好天那水,又从自己的工位上,找来了一些零碎的、被她使用过的布条。她把碎布条放到天那水里,直到碎布条吸满天那水,才将它取出来,然后她一下一下,用力地使用碎布条,擦拭着地上。
又过了十几分钟,地上的痕迹不见了。就算我睁大眼睛,也无法凭眼前这块地面,判断出几十分钟前这里曾发生过某件事情。胡水兰从地上站起来,活动了几下手脚。她将身边的碎布条捡起再扔进垃圾铲后,回到了自己的工位。她捡起喷枪,试了试喷枪的气压,之后就拿起一个玩具娃娃,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手中的喷枪。
这样喷了好一会,坐在她旁边的唐彩云,很突然地将头扭向了她。唐彩云还用眼睛看着她,眼神里隐隐约约地有种期待。胡水兰惯性地扭过头,看了看唐彩云。不过她马上将头扭回来了。她狠狠地扣着喷枪,枪嘴里的油漆,发出了轰的一个声音。她扣得太用力了,这一模的油漆喷得实在过头。油漆从模版的边缘跑过去,跑到了玩具娃娃不用喷的地方。她拿出玩具娃娃,娃娃的胸前到处都是油漆。她咚的一声,将娃娃扔到堆放返工娃娃的盘子上。唐彩云扭回头,不过很快又将头扭了过来。胡水兰什么反应也没有,看起来她十分专注地望着玩具娃娃。唐彩云的嘴角动了动,胡水兰还是看着玩具娃娃。唐彩云最后什么也没说,她反而转过头去,朝着另一边的何碧青耳边,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这句话很有效果,何碧青马上笑起来了,唐彩云笑得更大声。胡水兰就在唐彩云的笑声里,紧紧地咬了咬嘴唇。
下午六点过一分,下班铃很准时地叫起来了。将下班铃后延了一分钟,大概这也是董寒的主意。还是用唐彩云的话说,唐彩云说坐办公室的人就是精明,厂里头一两百人的一分钟,汇集起来就是一两百分钟。生产车间就在宿舍旁边,可是它们之间隔了堵高高的墙。要是与上班铃声相比,下班的铃声在墙那边显得细声细气了许多。不过再细声细气的铃声,在盼望下班的人听来,都要比上班铃精神许多。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放下的枪,好像只过了一会儿功夫,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手上的动作。他们从工位上站起来,脸上的表情疲惫中又有些喜气洋洋。有几个年轻的工人已经忍不住,放开了腿朝车间外奔去。这几个年轻人就像领头的羊,一会儿大家都跟着他们走向了车间外。就是这天下午呆在办公室很少出来的李广,他的身影在办公室里晃了晃,不一会也关掉了办公室的灯。
这种轻松的离场中,大概谁都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注意胡水兰。胡水兰跟大家一样,她在下班铃还没响完时放下了手中的枪。只不过她在放枪的时候,很突然地用眼睛瞟了瞟枪罐。枪嘴里跑出来的油漆,谁都知道它们来自枪罐。紧接着我看见她站起来,摸了摸裤子口袋。她的手从裤子后面口袋出来,拇指与食指之间夹着一个塑胶袋。那是个小小的塑胶袋子,袋子的底部还遗留着一些馒头的残渣。要是我没猜错,这天早上,胡水兰的早餐是一个或者两个馒头。她用这个袋子装着馒头,吃完馒头之后,不知怎么就将它放进了裤子口袋。望着指间的袋子,胡水兰没有任何动作。不过我看见她的唇角旁边,有一抹笑容不动声色地浮出来。
下了班,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当然是去食堂。有句俗话不是说过,人要是铁,饭就是钢。就像附近的许多工厂,这个厂的食堂也分成了大小两个。大食堂的饭菜都是用大锅大灶做出来,然后将它们一勺一勺,分配到工人递来的饭盆中。要是跟大食堂相比,小食堂的饭菜就精致了许多。小食堂的饭菜统统用小锅小灶做出来,然后将它们一盆一盆,端到职员们围着的桌子上。我这里说的职员,当然是不用在工位上坐着的主管们,组长们,还有那些成日都趴在办公桌上、不知在忙些什么的文秘们。小食堂与大食堂挨在一起,每个排在大食堂窗前等待打饭的人,都可以看见小食堂及小食堂里的职员。胡水兰排在队伍的尾巴上,她的手里拿一个黄色的铁制饭盆。她的黑色的眼珠转到左边时,不可避免地就看见了小食堂里的李广。李广看起来有些无精打采,面对着桌上的饭菜半天都没反应。顺着胡水兰前面的队伍一直数,一直数,我就数到了队伍前面的唐彩云。唐彩云现在正回过头,津津有味地和排在她后面的人说着话。两个人简直越说越有劲,眼看都轮到唐彩云打饭了,还是后面的那个人推了她一把。
吃完晚饭,晚饭后不用加班,接下来要做的,似乎只剩下冲凉和清洗冲凉时换下来的衣裳。当然也有些工人不愿意马上冲凉,他们更愿意走出厂门,融入到外面的人群和夜色中。大食堂的右边就是冲凉房。还是跟附近的工厂一样,那是一排低矮的、一间一间的、窄小得不能再小的冲凉房。胡水兰还在吃饭,唐彩云已经拎着桶从宿舍出来。她的桶看起来有点沉,估计她所有冲凉时要用的东西都放到了桶中。胡水兰就那样一口一口嚼着饭,一嚼一嚼地看着唐彩云。唐彩云走进一间冲凉房,关上门,门里头传来一片哗哗的放水声。胡水兰也在这哗哗的水声中,停止了嘴里的咀嚼。她近于无聊地,一下一下用筷子敲击着铁制饭盆,饭盆的底部发出一种当当的声音。她的眼珠子也在眼眶里,配合着这种声音,一忽儿转到了左边,一忽儿又转到右边。
唐彩云从冲凉房出来,胡水兰终于消灭掉了饭盆里的饭。她在冲凉房旁的水龙头底下,不紧不慢地洗着饭盆。不时有水花通过饭盆溅到她身上,她对这些水花的态度是不理不睬。唐彩云提着桶,眼看就要从她前面离开,她便突然地叫了一声,唐彩云。唐彩云扭过头,不知道谁在叫她。谁都没想到胡水兰这时会将水龙头关掉,然后笑眯眯地又叫了一声,唐彩云。胡水兰对唐彩云说,刚才有个人找你,叫你去一下厂门口,有人在那里等你。唐彩云看了一眼胡水兰,谁都可以看出她此刻的脸上有一点喜气洋洋。她想都没想,放下桶,让胡水兰帮她看一下桶,然后她转过身,飞快地跑向了厂门。她的背影跑得完全不见了,胡水兰才提着桶,冲进了一间冲凉房。胡水兰没有将冲凉房的门关严,她只是顺手关了一下门。所以我可以透过很宽的门缝,看见她在里头的所有动作。她将那个塑胶袋子,再次从口袋里掏出来。那个被她系得很紧的袋子,袋子里躺着好多油漆。她将袋口解开,提起了唐彩云的裤子,十分麻利将袋里的油漆,倒在了裤子的裤腿之上。她这样做完,接着又将桶提出来。然后她根本不管那个桶,两条腿很快地跑起来。
好几分钟后,再看到胡水兰,这时候她已经站在厂门外面的大马路上。她出来的有些仓促,身上的工衣都没换。不过她身后的厂门那里,同样有几个穿着工衣的工人,正在和几个穿着便衣的人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谨慎细小,细小得甚至有些私密。胡水兰看了几眼他们,然后她就很轻快地,踩着大马路的路面向前走去。她走了好几分钟,路过一家诊所。这家诊所的规模很大,可是它规模再大也是诊所。又走了好几分钟,她的面前是一个市场,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市场里传出来,跑到了她的耳中。她想都没想,一脚迈进市场。并且很快在一家卖鞋的店面前停了下来。不过她没有走进店面,她看着那些摆在玻璃柜台上的鞋子,它们在灯光的作用下闪闪发亮。她离开鞋店,没多久又在一家卖衣服的店面前停了下来。她走进了这家店面,她的视线还被一件衣服吸引,那是一件绿色的、有许多流苏的、将腰掐得很细的齐膝短裙。不过她也只是看了看,接着又离开这家店,继续向下一家店走去。过了好长时间,她走进了一家书店。书架上密密麻麻地码着书,她抽出了其中一本。这本书被她拿在手上,拿了好一会,她还是将书放到了原来的位置上。
胡水兰最后走进去的那家店,是家卖小挂件和小头饰的小精品店。她看中了一件头饰,这是套外形设计成卡通娃娃的发卡。这套发卡的标价签上,端端正正地写着两块钱。她拿起这套头饰,做一个往头上戴的样子。她做了好几个这样的样子,便拿着发卡来到了精品店的收银柜台。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接着从里面挑出两块钱,非常利索地将这两块钱,放到了收银柜台的台面。
胡水兰从市场出来,时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晚。她的影子被路灯拉长,在她身后跟着她的步子一晃一晃。走到诊所的时候,她的影子很突然地跟着她的步子停住。因为这时候她看到了李广。李广正从诊所出来,就像他下午刚从办公室里出来一样。不过还是有些东西,变得与下午不太一样。他的背上,现在背个孩子。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孩子已经在李广的背上睡着,他用双手抱住了李广的脖子。一个女人走在李广旁边,女人的年纪少说也在六十以上。女人的左手,绑了层厚厚的纱布,一根白色的布带从女人的肩膀两边垂下来,吊住了她的左手。女人的年纪实在大了,导致她脚下的步子有些蹒跚。走在右边的李广就伸出左手,挽住了女人没绑纱布的右手。李广的右手还伸向背后,紧紧地托住背上的孩子。不知道胡水兰和我的想法是不是一样,胡水兰朝李广的身后看了看。她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背着孩子的李广,还有李广身边的女人。她这样看的时候,李广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打完哈欠,李广呶了呶嘴巴,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诊所门口的灯光很暗,路灯的灯光又很昏黄,不知是不是灯光的原因,李广的脸色显得蜡黄蜡黄,蜡黄的额头上面,悄悄地趴着好多皱纹。也就是这时,背上的孩子将头扭了扭,扭完头孩子便松开了他的手,他的身子当然也跟着这个动作滑了下来。李广便赶紧伸出了那只挽住女人的手,两只手一起努力,托了托背上的孩子。李广这样做完,又赶紧收回手,挽住了身边的女人。
也许是真的没有精力注意胡水兰,李广从诊所出来,迎面走向了胡水兰。胡水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从胡水兰身边过去时,根本都没有看见胡水兰。胡水兰还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李广。直到李广都走去好远了,胡水兰才转过身,继续朝厂门那边走。胡水兰将头低着,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更长。她现在走得很慢,她好像拖着身后的影子,在那里一步一步移动。
不一会,胡水兰走进了厂门,走向宿舍。走进宿舍的时候,胡水兰探着头朝里面看了看。她看见了何碧青,何碧青正躺在床上,非常娴熟地织着一件毛衣。毛线和毛线针在何碧青的手上,就像是一群听话的狗,何碧青让这群狗往东边走,这群狗肯定不会走往西边。她看见了其她的几个女工,她们都躺在自己的床上,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几个女工我看了几次都没看见,这几个女工中就包括唐彩云。胡水兰讨好地问何碧青,你有没有看见唐彩云?何碧青停下手中的编织,想了想说,半个小时前,她在外面碰见了唐彩云,唐彩云说冲完凉可能有个老乡来找她,可是她在厂门口没有看到这个老乡,于是她懒得回厂,决定去外面逛逛。何碧青这样说完,胡水兰已经转过身子,很快地朝着宿舍外面走。何碧青冲着她的背影喊,你先别走,你帮我看看这件毛衣。何碧青的话没说完,胡水兰已经走出宿舍,她的身子朝右边一闪,何碧青又低下头织起了毛衣。
出了宿舍,胡水兰去的地方是冲凉房。这个时候的冲凉房,已经在一片热闹之后变成了四下里无声。她在某间冲凉房的门口,看到了唐彩云的桶。她俯下身子看了看桶,桶里的衣服一动不动。最上面的那条裤子,正是她之前扔下的裤子。她拎起裤子,裤腿上有一片醒目的油漆。她放下裤子,接着就走向了生产车间。车间的卷闸门现在已经关上,纹丝不动地守在那里看她。她没有走向卷闸门,而是走向了门旁边的推拉窗。这个厂最大的车间,就是眼前的这个车间,这个车间一共有八扇推拉窗。她推了推她走向的第一扇窗,这扇窗已经从里面锁上,它在她手里面紧紧地一动也不动。她接着又走向第二扇窗,这扇窗还是一动不动。直到她走向第四扇窗时,她稍一用力,手中的推拉窗很快发出了哧哧的移动声。她将这扇窗彻底推到一边,然后她迈上窗台,敏捷地跳到了里面的车间。她从窗台上面再次跳出,她的手里已经捧着一杯什么东西。这杯东西在夜色中悄悄地散发出来一种强烈的、类似于敌敌畏的气味。不用猜我也知道,这是一杯天那水。她关好窗户,就捧着天那水,非常轻快地向冲凉房走去。
她走到冲凉房后,找到了唐彩云的桶。她将上面的裤子提出,直接将裤腿展开,铺到了一间冲凉房的水泥地上。她将天那水泼在油漆上面,一下一下地直接用手搓着油漆。她的手估计受不了天那水的刺激,尤其是有了水泡的左手。时不时地将裤腿放下之后,她都会赶紧用清水冲洗双手。她这样搓了很久,油漆终于在她的攻克之下,慢慢地从裤腿上淡去了。她拎起裤腿,对着灯光,她的眼睛都快贴到了裤腿上面。放下裤腿之后,她继续在裤腿上面泼了一点天那水,继续用双手搓着腿裤。她这样做的时候,远处的不知什么地方,突然传来了一阵歌声。她停止搓动,凝气屏声,可是这歌声离她实在太远,压根就听不出这歌声唱了些什么,唱歌的是什么人……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