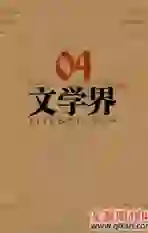皎皎空中孤月轮
2009-04-26安敏
安 敏
小时候,每逢我过生日,母亲都会给我煮两枚盐蛋。那时的盐蛋,金贵着呢。从年头到年终,我却从未见母亲为自己煮过一次。
母亲一生都在大山里转着圈圈教书,打从解放后土改时候开始,就一直没有走出那一片大山。我至今记得我们家的一对笼箱,那两个能摆放能挑着走能放置很多东西的大箱子,是母亲出嫁时最豪华的嫁妆。在很多的假期里,总见母亲把衣物家什码在里边,请了个农民伯伯挑着,两手拉着我和弟弟,就上路了。我们问母亲又去哪啊,妈说又调学校了。我们兄弟俩就这样跟着她在一座又一座的乡间小学校里长大。小时候好像是很少见到父亲的,说父亲在外面,其实父亲在一个农场劳动。后来母亲把父亲弄到了她教书的当地农村插队,一家人才到了一起。
母亲姓周,年轻时很漂亮。她个子不高,两只眼睛又圆又亮,里面总是汪着一泓笑意。母亲爱笑,而且是那种哈哈大笑。偶然见她和当地农民打“纸胡子”(字牌),打出兴致时就站起了身子,一只脚踏在凳子上,那笑声,便走出七八里远。有时父亲在家时板着个脸什么气也不哼,也不搭理一家几口嗑着瓜子啃着干薯片说的闲话,母亲就戏他:“你老气横秋干吗呀!”逗不笑父亲,母亲就逗我们兄弟俩:“你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呀?”要我们回答,是不是从她腋下钻出来的。我们当然一脸茫然,这时父亲就“嘿嘿”地笑了。“你晓得‘嘿嘿啊,我还以为你痴呆了呢!”母亲说。
母亲经常在学校里演戏,演给学生看,演给当地农民看。她一般都是扮很俏的姑娘,比如胡大姐之类的。有一回却演了个旧社会的贫苦母亲,那戏的题目叫《出了苦海见青天》,还要个演儿子的,就把我带上了。每回演出时,我都要用那柴火烧出来的锅底灰把脸涂黑,演出前母亲又在家里煮一碗很老的青菜,在台上我就抓在手里当旧社会的野菜咽。这就让我知道了旧社会的苦难与黑暗,也使我从乡民们那如醉如痴的脸上看到了这戏的神圣,就爱上了演戏,在我妈教书的那些乡间还成了名角。演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时,从乡村老邮递员手上借了顶毛帽子和一件蓝色的中长大棉袄披挂了,又在家里穿了一双长筒套鞋当马靴,再捡根放牛梢当马鞭,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了!乡亲们就夸周老师养了个好崽,那戏唱得!母亲每次都看,在人群里打着“哈哈”乐。
农民们都跟母亲说得来,晚上收工后,我们一家四口一间房子的那个家,就成了农民俱乐部。附近的农民都来我家扯谈,扯的都是乡间野语,有时把间小小的屋子吵翻了天,我母亲都由着他们。有一年要新修一条县级公路从学校门前过,全区各乡农民派工来修,民工集中的那几天,我家就天天会场一样。原来,是我妈这么多年来在这区里很多乡校当过老师,这些民工们很多都是我妈在各地教过的学生,或是她的学生的儿子。
那些个晚上来我们家玩的乡民们,来得早的一进门就扯开煮饭的锅盖看,看到锅巴就抢。母亲知道他们没吃饱,便每次煮饭都有意煮出厚厚的锅巴来。家里有什么我们穿不了的衣服和戴不了的帽子,便都给了那些穿不暖的学生也就是这些乡民的孩子。来客人我们就过节了,因为就有好菜上桌。这乡间小学来的客也就是区里、公社里的学校老师或领导,其实我妈只是普通的村小老师,不管接待,但他们一进校门就大呼小叫“周满满”,这些来的老师也好领导也好大多是我妈在方围峦转教书时的同事和领导,还有不少都是她过去的学生,都知道周老师热心热肠,都喊“周满满”。那个时候干部们到群众家里吃顿饭是要数钱的,我母亲自然是不要,每次都十分快乐地迎送着他们。有一回一个区文教办的老师,是我妈曾经的学生,吃过饭后攥紧了拳头伸出来,笑着说:“周满满,反正吃你的饭是不要钱的,这次要不要啊?”我妈看着那拳头的握法,肯定那里边没钱,是戏她,就爽快地把手伸过去:“拿来!”那拳头就在我妈掌心里松开了,可就变戏法一样掉落几毛钱来。我妈知道上当了,那老师却早笑着跑远了。
那时我家并不富裕,只有来了客人时,桌上才有好菜。其实有好多次,我发现母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落泪。我父亲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公职,被下放了。父亲开始是没开除公职的,他的右派帽子也是在运动扫尾时补指标补进去的,受批斗时他既想不通又受不了,在家里的床上想用绳子勒死自己,被母亲发现了。母亲不知道去救他,只是吓得大喊大叫,就引了人来,人来了问题就大了,说我父亲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就开除了公职。有好心人劝母亲离婚,说为了两个儿子。可母亲只是微笑不语。后来,她又四处求人,将我父亲从农场转到了她学校当地的生产队落户,我们一家才得以团圆。
但我始终不知母亲的生日。
直到我有了工作,我父亲复职以后的一个中秋节前,我对母亲说我这两天有事出差,要八月十六才回,不能在家过中秋。母亲想了想说:去吧,就等你回来再过中秋。八月十六我回来了,爸说:今天过节还好一些呢,今天是你妈的生日。
母亲的生日?从小到大,没见母亲过过生日,我也从未细想过。母亲怎么会没有她的生日呢?是我这个做儿子的,太疏忽太不孝了!我满脸内疚,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睛。母亲却乐呵呵地,不停地,为我和弟弟夹菜。
从此,我们家的中秋节就改到了八月十六日。母亲的日子,也越过越舒畅了。每次回家,隔老远,我就能听到她那爽朗的哈哈声。有回母亲身体不大舒服,我连哄带劝,将她带到长沙做了次全面检查。谢天谢地,并无大碍。然而,在满大街的车流中,母亲显得那么手足无措。一辆汽车开过来,她竟吓得不知道往哪里躲,尖叫着在马路上乱窜,让司机和我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当时差点落泪,这就是我那个当了三十年老师的母亲吗?是那个打纸胡子时把一只脚踏在凳子上的母亲吗?
没想到,身体并无大碍的母亲,竟未能迈过六十岁的门坎。
那是1990年,我从县城调到市里工作还不久。因岳母腰痛病发作,跟着我在临时宿舍小住的妻子带着孩子回去探望,第二天晚上,她突然打来电话,说妈不行了。我说哪个妈,她说你妈,意外事故!我放下电话就往火车站跑,正好有趟车。是趟慢车,慢条斯里地折磨着我的焦急。但我当时还没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半夜过后,等我下了火车小跑着冲进医院的病房,看着母亲在病榻上发出的手拉风箱般的声音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液氨罐爆炸的毒气冲进气管把肺烧坏了。医生边说边摇了摇头。我当即就在凳子上昏死过去。医生把我弄醒后,我求他们想想办法,他说这本来就无能为力,加上这天资江大桥上一辆小客车从桥上冲开护栏坠落,医院全力以赴抢救遇难者。我说可以送长沙吗?他说在路上就可能出事。看看能不能顶过今晚,顶过了也许有救。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无比渺小。最亲最爱的母亲躺在我面前痛苦地呻吟,而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我极力克制自己,不想让母亲看到我的泪水。我装做很有信心的样子,安慰母亲好好养伤。我告诉母亲,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住两天就可以出院了。母亲开始还低低地,唔唔地答应着。我不停地说着话,可我突然发现,母亲没有唔唔地答应我了。我凑近些,母亲表情平和。开始我还以为母亲累了,想休息一下。细看又觉得有些不对。我一把攥住母亲的手,大声呼喊着医生……
我怎么可以相信,我的母亲就这样离我而去了!
之后的那两天,我总是一个人站在灵堂里,痴痴地看着母亲的遗像,任凭泪水在我脸上恣意奔流。
我的母亲,她知道媳妇和孙子要回来了,便早早做好了饭等着。等到天黑,她又想出门去接。谁知一个化工厂把一个注满液氨气体的罐瓶随意置于门口,我母亲路过时,它突然爆炸了。而这个厂家,除了负责我母亲的安葬费用之外,再无其它赔偿之举。我们也没说什么。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换回我的母亲了,赔偿不赔偿,又有什么意义!
之后,我常常梦见母亲。在梦里,我四处寻找母亲,却见她站在一个土坑里,面容憔悴。我说妈我接你回去,说着就要往下跳。母亲狠狠地瞪着我,大声说:你快走,快去找你爹!这时,我发现自己原来站在一堵墙上,我还想往下跳,母亲好像伸手推了我一下,我就落在墙这边了。我又往前走了几步,就听到有人喊我,是父亲,他正站在我家阳台上。而母亲,却不见了。我怎么喊都喊不应。我急得嚎啕大哭,直到妻子将我推醒……
如今,我家还是八月十六过中秋。炒几个菜,摆几个月饼,给母亲摆一双筷子、一个碗。然后,我仰望皎皎夜空,我祈求那轮孤月,千万照亮天堂之路。因为我的母亲,她要从天堂回来一趟。她要和我们一起,过她的生日。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