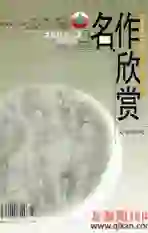女性的“他者”化
2009-04-21张锦
张 锦
关键词:女性 他者 性别视角 《尘埃落定》
摘 要:本文从性别视角审视《尘埃落定》,认为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被“他者”化了,主要表现在女性人物并未构成小说的写作重心、作者对女性的观照上表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女性形象塑造上的失败等等。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尘埃落定》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展现了浓郁的异域民族风情,以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为我们演绎了一段土司制度土崩瓦解的时代挽歌,从而成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但是,如果从性别视角对其加以观照,我们会发现《尘埃落定》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被“他者”化了。
首先,女性并没有构成《尘埃落定》的写作重心,故事自始至终都在围绕着男人展开,男人处于无上的主角地位。土司制度的兴盛与衰败,土司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勾心斗角,土司贵族们最初的梦想与最后的堕落,男人都是这一系列故事的当然主角。如麦其土司在国民政府黄特派员的指点下在其领地上遍种罂粟,其余土司绞尽脑汁盗取罂粟种子从而引发罂粟花大战,麦其土司在傻子二少爷的建议下改种麦子,使得麦其家族的领地人口规模空前。傻子二少爷推倒院墙将封闭的粮仓变成开放繁荣的贸易市场,开仓卖粮,公平交易。他还在自己的官寨建立税收体制,古老封闭的阿坝地区第一次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业集镇。所有的这一切几乎都由男人来上演,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陪衬,是故事的点缀。透过这些男人间的故事我们看到了金钱与罪恶、爱情与权力、战争与历史、崇高与卑劣的组合。阿来说:“小说的另一个情结是埋在我心中的英雄主义梦想,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血液中遗传的精神气质。——我用小说去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的浪漫。”以这样的创作动机来写作小说,女人的故事只能在那些所谓的“大的浪漫”之下被轻视或忽略,因为英雄从来都是与历史和男人联系在一起的。醇酒与美人向来都是烘托男人英雄气概的物件。君不见,那些打打杀杀的争夺战,自古以来都是男人的战场。历史几乎都是由男人创造的,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在女扮男装之后才能被载入史册,而从古至今能被选入中华民族正史加以歌颂的女英雄恐怕也只有木兰一人。其余能流传于今的女子要么被指认为红颜祸水,如西施、杨玉环,要么被充做交易的礼物,如王昭君,其余不入史的女子几乎都成了男人性欲的发泄对象或生殖的器具,消逝在历史的烟尘里。历史是男人的专利,《尘埃落定》中那个书记官记载的从来都是男人的故事,女人的事情怎能入他们的眼?
其次,《尘埃落定》在对女性的观照上表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在“我”眼中,“女人不过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第二章)。“一般而言,我们对于这些女人是不大在乎的,她们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我们都不大在乎”(第五章)。女人不是具有独立价值意义的主体,而是与物无异的存在。女人是不干净的,喇嘛告诫土司:“为了保证法力,不要靠近女人和别的不洁的东西。”(第四章)在男人的心目中,女人都是不洁的,《尘埃落定》还告诉我们,“对三太太央宗来说……她的存在好像仅仅就为了隔三差五和土司睡上一觉”(第五章)。女人生存的意义,不过是满足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生殖的工具,或者充当洗衣、做饭之类的奴隶。女人生下来,便被指派照顾男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以男人为中心。桑吉卓玛是服侍“我”多年对“我”忠心耿耿并将自己的身体都献给了“我”的下人,当她出嫁后与“我”再度相遇时,卓玛在“我”的眼里却发生了变化:“这个卓玛再不是那个卓玛了。她身上的香气消失了,绸缎衣服也变成了经纬稀疏的麻布。……她的声音都显得苍老了,再也唤不起我昔日的美好感觉。”(第四章)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就可知晓,卓玛之所以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卓玛,只是因为她衣着破旧、声音苍老,不再年轻和漂亮,那么在此之前“我”所喜欢的只是年轻的卓玛的肉体。而且侍女在我们的男主人公眼里都是“下贱”的,是不值得尊重的,主仆之间存在着的森严的等级界限根本不会抹平,“平等”一词完全不存在于“我”的字典里。所以她们被侮辱、被奴役都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中国数千年来男权文化的典型心态。卓玛和随后代替卓玛的小侍女塔娜都是“我”发泄性欲的对象。“我”对于她们,是没有任何爱情可言的。她们所付出的一切,对“我”而言是在尽她们的义务,甚至是“我”对她们的赏赐与恩宠,只因为“我”是土司家的二少爷,我就能颐指气使地凌驾于她们之上,对于她们的问题,“我”高兴回答就回答,不高兴回答就不回答。而“我”对于妻子塔娜,也只是震惊于她的艳丽,她只不过满足了“我”的色欲,是出于一种生理的本能。这又怎能说这是对于女性存在的尊重?
最后,《尘埃落定》在对女性形象进行塑造时并没有渗透进多少女性意识。在有限的几位女性中,麦其土司太太作者着墨较多。与其说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而存在,毋宁说她是男权文化的忠实执行者更为恰切。她教育儿子这样对待家奴:“你要记住,你可以把他们当马骑,当狗打,就是不能把他们当人看。”(第一章)这种语气语调与其丈夫麦其土司毫无二致,那是一种等级制下统治阶级对下层群体的痛恨与不屑,她大概忘记了自己也曾经是一个出身低贱的女子,是一个有钱人买来送给土司的。她由奴才上升到主子的地位,就将从前的事情完全遗忘,以主子的身份仗势欺人,对下人肆意凌辱、百般欺压。当“我”与侍女塔娜发生了一点小矛盾后,土司太太竟然不问原由“伸手就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嘴巴”(第五章),让“我”睡下,让她一直跪在“我”的床前。作者本可在土司太太身上挖掘更复杂的文化因子,但由于男权意识所限,倒不如说她是一个男权符号更贴切。傻子二少爷的妻子塔娜在《尘埃落定》中被视为爱情的象征,美的象征,她在“我”的眼里,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与美神阿伏特洛依。但是,这哪里是爱情?哪里是美?塔娜出身贵族,她之所以能成为“我”的妻子,完全是作为一种交易的筹码,是茸贡土司为了麦子问题和麦其土司所做的一个交换。在此,《尘埃落定》与传统女性观表现出了一致性。“我”爱上塔娜完全是为她的美貌所吸引,塔娜对于“我”则不存在爱情可言。只有当“我”一步步逼近权力的制高点时才能博得她的垂青和喜爱,而一旦“我”丧失权力,她便水性杨花,趋附权势,背叛我甚至舍我而去。塔娜在权力面前拜倒,权力作为一个幽灵遥控着她的身心。阿来在塑造这些女性人物的时候完全屈从于传统的男权视阈,女性不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只有在男权文化下才能获得她们存在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土司太太、桑吉卓玛抑或美女塔娜都是在行动与对话中呈现出她们的性格特征,应该说这是阿来塑造人物的独特之处。但是,人物如果没有了具有标识性的外貌,也就没有了此人物区别于彼人物的重要特征。于是年龄、性格大体相近的某一类人物之间完全可以等同。我们想象不出桑吉卓玛年老时与傻子二少爷的奶娘长相有何不同。当然作家描写人物的方式不同,但这是否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作家阿来漠视女性的心理呢?《尘埃落定》中女性是以某一类人所具有的形象特征出场的,而不是以一个人的形象特征出现的。她们都被贴上了标签,如主子、奴才,而所谓的主子或奴才只不过是古往今来具有此类性格特征的人物的交集,或者说被划归为某一类的女人都应当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思维方式,一样的个性特点。这样就导致了《尘埃落定》中女性人物的千人一面、僵化与简单化。所有的女性都具有同一个名字:女人。女人只能由男人来命名和体认,从属于男人的安排和需要。试问:如此描写女性人物是对女性的尊重吗?
综上所述,从性别视角来看,《尘埃落定》对于女性人物的书写并没有取得太多的突破。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国家,男权社会的文化传统把男性塑造为社会文化的主体,而女性则在随意的书写中被扭曲,充当着工具和附庸。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女性与男性在审美地位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女性被置于“对象”的地位,被“他者”化,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只是权力规范下的审美对象和消费对象,成为一个被大众窥视的性对象和男人欲望的承载者。《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在将笔触对准女性时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大男子主义倾向、男权文化优越论等思想,从而最终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在此,笔者衷心地祝福中国作家能够更加彻底地摆脱男权意识的障蔽,在21世纪的文学麦田里收获更多丰硕的果实。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张 锦,文学博士,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姜波、耿春明.深邃的哲理思索普遍的人性追问——评阿来的《尘埃落定》[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