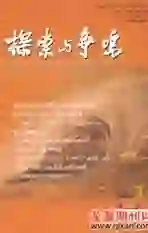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征约的原则、观念及方略
2009-04-21方汉文
内容摘要 世界性的流失文物征约是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是世界上文物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文物流失主要是由于侵略战争和走私盗运造成的。中国海外文物征约势在必行。文物征约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对侵略战争和走私盗运流失的文物应无条件征返,不以回购方式进行。海内外应共同协商共同征约外流文物,这是关系到民族文明价值评定与树立民族自尊的重要举措。
关 键 词 中国海外文物 文物流失 文物征约 文明对话 方略
作者 方汉文,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州:215006)
世界文明对话视域下的文物征约
西班牙当代学者、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所谓文化,我且称之为表现一个社会的行为和物质特征的复合体,就它的某些成分而言,历来是在各种文明之间交流不息的。”[1]这句话提示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文化关系的复杂性。事实上,当今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个层面是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层面的交往;另一个层面则是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交流。后一层面涉及到历史的语境。虽然涉及到的相关层面不同,但两者同等重要。因为现实的文明关系是在深厚的历史底蕴之上形成的,而经济与物质的交往则与文化遗产之间水乳交融,无法断然分开。
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文物征约(Requisition,也有人称之为追索)愈演愈烈。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性文物流通如拍卖和展览等的介入,更是将不同文明观念的对立带进了必须以法律、行政、经济与外交方式解决的阶段。中国是文明古国,海外流失文物居世界前列。从16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来,由于文明交往与殖民扩张,中国的大量文物流失境外,成为文物占有国的收藏品。这种情形本身即是一种嘲讽,1900年八国联军从中国故宫掠夺的东晋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竟然堂而皇之地摆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展厅中,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行宫中满藏着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劫的中国国宝,更遑论收藏在日本各大博物馆内侵华战争时期掠夺的各种珍贵文物。其实以上所举,也仅仅是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的沧海一粟。但是2009年初发生的佳士得拍卖行不顾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公开拍卖海外文物的事件则提醒我们,世界性的文物征约已经势在必行。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并且确定我国在文物征约中的原则、观念与应对策略。
文物是民族文明创造的物质性结晶,所有文物的最终主权归文物宗主国国家所有,文物宗主国有保存、收藏、利用、流通和保护本国文物的义务、权利与职责。流失文物的征约从本质上看,是维护民族文明的尊严与价值的行动,更是促进民族文明发展的保障。同时,通过协商方式将不同历史阶段因战争、盗卖、偷运、走私、不平等交换等各种不合法与不公平的方式占有的文物归还宗主国,是有利于世界文明和谐发展的。文物的征约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是一种互补性的联系,这一观念正在成为全球文明研究的共识。
联合国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是巨大的,特别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公约》(The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1972,简称《公约》)等三个文化相关公约的签定与实施,对于世界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联合国早在1981年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博物馆与私人或是国家收藏机构全部或部分地将非法收藏文物归还给文物宗主国,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负责编写这类文物的目录。近年来,世界各国尤其是文物流失严重的文明古国,文物征约工作进展迅速。2001年,埃及政府成功向英国追回了被走私贩运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皇后奈费尔塔丽石刻头像;1997年,希腊从美国麦克尔·沃德博物馆追回被盗运的迈锡尼金银物与雕刻,使得公元前13世纪即已闻名地中海的迈锡尼工艺返回希腊。近日,秘鲁等国正在向耶鲁大学追讨美洲古代文明文物。但是勿庸讳言,正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专家戴维·思罗斯比(David Throsby)所说:“同时世界文化遗产正遭受着来自各方面的越来越多的威胁:空气污染和其他环境破坏的侵扰;国际旅游剧增带来的压力;战争和冲突的破坏;保护措施的缺乏和各方面的全然漠视。”[2]但无法否认,世界性的文物征约是文明对话的无可回避的事实。中国是一个文物流失大国,明确中国海外文物流失的现状与我国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来征约流失文物,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国海外文物流失的历史原因与模式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种途径和方式:第一类是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中的文物劫掠。从鸦片战争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连续战争中被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惊人,其中以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后的大洗劫与抗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军政与商人的劫掠最为突出。外国入侵者与军阀汉奸互相勾结,以暴力形式强抢文物,如震惊世界的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烧毁劫掠圆明园与1900年8月16日八国联军再劫圆明园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圆明园前后经五位皇帝营造,历时150年,是当时举世无双的文物藏品与艺术园林建筑,其规模与价值是后世任何一个博物馆所无法比拟的。在战争中,存放《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的文渊阁被焚;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人摹本被劫。法国于1863年专门建立了枫丹白露宫中国文物馆,收藏有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文物中精选的1000余件珍品,其中如乾隆御笔白玉方玺等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国宝精品。康有为赴法时得见此物,称“昔在北京睹御书无数,皆盖此玺文,而未得见,……见圆明园宝物令人伤心”。不仅如此,该博物馆还藏有大量的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历代名人书画、大小金塔、玉册图录、金曼达、象牙、玛瑙犀牛角、水晶、珊瑚、玉器等。伦敦大英博物馆等藏品不仅品类繁多,而且质量上乘,尤其是圆明园长春园海宴堂的十二生肖铜兽首像更是弥足珍贵。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劫掠中国文物为历史之最,在世界文物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据初步统计,大约有图藉300万册,重要文物12545件,其余未列入者不计其数。194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专门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著名文物专家马衡、梁思成、李济、傅斯年、徐森玉、蒋复聪,法学家徐敦璋,经济学家吴半农,学者吴文藻、谢冰心、王世襄等人参加,历时两年多,追回了部分文物。但是由于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对于中国文物追索工作并不热心,甚至有部分美国专家与日本政府态度暧昧,致使工作进展不大,令爱国人士深感失望。
第二类是以偷运、盗卖与盗抢等非法手段占有中国文物。从16世纪开始,随着海上航线的开通,欧美各国的传教士、商人、考古学者与各色人等,以考古挖掘为名,在我国进行文物偷盗与非法盗卖活动,历时长久,盗取文物数量巨大。其中仅以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物为例,先后有俄罗斯的奥勃鲁切夫盗得藏经洞写本两箱(1905年)、匈裔英藉冒险家斯坦因第一次盗得经卷写本24箱绣品5箱价值连城(1907年),第二次盗得经卷写本5大箱570余件(1914年),归藏大英博物,英藏经卷写本达到15000卷之多;法国伯希和盗得藏经洞精品6000余件10余箱(1908年),归藏法国罗浮宫等处;俄国冒险家奥登堡盗得逾万件汉文残卷,200余件藏文写本及绢纸壁画无数(1915年),归藏俄沙皇冬宫(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美国兰登·华纳(Langdon Warner)盗剥壁画精品26方32006平米,归藏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其余还有日本、印度、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也通过盗卖、走私等手段获取了大批敦煌文物。中国历史学家陈垣痛心疾首地说道:“……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赅。”[3]敦煌只是中国流失文物的冰山之一角,但已经是世界文明关系史上令人惊悸的一页。
第三类是国际文物走私而致的流失,这是目前中国文物面临的最大危险。近年来文物走私猖狂,相当数量的中国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被偷运出境。笔者多次看到近年来新开掘的陵墓和遗址文物保护单位的珍品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或是文物商店里,令人触目惊心,不胜伤感。以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例,这些竹书于1994年发现,分别由上海博物馆与香港友人张光裕先生联系朱昌言、董慕杰、顾小坤、陆宗霖和叶仲午等五位先生出资55万港元购得后捐献给上博,大约有竹简1200余支,39000余字。[4] 当时香港文物市场上新出土的楚国漆器等文物相当多,这些竹简也是新出土的,但是至今连出土地和遗址状况也完全不清楚,这必然是以走私方式流失到香港的。这不仅对文物保护是一种挑战,即使对我们购回后的文物研究也是极大的障碍。近年来对这批战国楚竹书的研究就是在不明出土遗址状况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当然受到损害。
以上是海外文物流失的主要方式,其中不包括合法的中国文物交换、转送和赠馈,如国际间文化交往,私人文物损赠等。如1878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留美学生容闳在其出任华盛顿副公使后,将包括一套5040册的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私人藏书赠给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该图书馆还有简又文教授捐赠的藏品,包括太平天国起义军的藏品320种,如期刊、拓片、地图、钱币、印章等,其中尤为珍贵的是16世纪到18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地图,这些文物虽然收藏在美国,但是对于世界性的中国研究、对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各国的文明交往有推动作用。
中国文物海外收藏状况
中国文物的海外收藏以西方国家与日本为主,收藏历史最久的是英法德俄日等国,收藏时间集中在18世纪以后,藏品的年代历时久远,从中国石器时代到近代,品种齐全。举凡生产工具如石斧石刀,生活用品如陶器瓷品、金银器皿,其他物品如图录文献、珍玩古董、甲骨文、纺织品、字画、玉器等等,无所不有。由于数量巨大,收藏地分散,我们只能择其要者简单分类,指出主要收藏国与收藏地。
首先是英国。英国曾经是西方列强之首,特别是在西方殖民大扩张的过程中,英国劫掠中国文物最早。这些流失文物主要收藏在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该馆藏品历史阶段完整,包括新石器时代玉斧、商周玉人等,殷周青铜器,如商代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汉唐陶俑、宋明瓷器、宋辽佛像、清乾隆道光年间的铜钟等。最著名的当属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由英国所掠。大不列颠图书馆(即大英图书馆)收藏有世界数量最多的敦煌文献,这是斯坦因在中国与中亚地区所获全部文献。最著名的是清翰林院文渊阁本《永乐大典》,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劫得后藏于该馆。此外尚有伦敦的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伦敦大学的中国艺术馆与牛津亚士摩兰博物馆等,均有珍贵的中国藏品。
其次是法国。法国是最早侵略中国的欧洲国家之一。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后,法国将所获文物悉数收藏于巴黎的塞纳河畔枫丹白露宫,这些文物都是举世罕见的珍宝。这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至今未对外正式开放的收藏地,而且参观者不许拍照。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西域与敦煌文献也是举世闻名。法国人伯希和与英国人斯坦因都是盗取中国文物最多的人物,只不过伯希和的汉学功底远胜过斯坦因,他从敦煌所获得的藏经洞文书品质最优,有明确年代标记的达500多卷,使得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成为世界四大中心之首,超过了北京、伦敦与圣彼得堡。伯希和还盗取了一批艺术品,先是藏在卢浮宫,后转入集美博物馆。
集美博物馆是巴黎以收藏东方文物为主的地方,其所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如商代象尊、西周令簋、西周梁其钟等都是绝代精品。巴黎池努奇博物馆也收藏有中国青铜器,其中商代食人兽卣(又称虎食人卣),是湖南安化出土的,一共两件,大致相同,另一件现存日本泉屋博物馆。这两件青铜器在中国器物中殊为罕见,造型独特,猛虎正在吞食人形动物,如同西亚文物中常见的狮食人的造型,对于艺术与文明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再次是日本。如果仅从数量而言,日本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居世界之最。东京博物馆因藏中国陶器与书画而最为知名,包括大量的唐三彩、五代后蜀石恪的《二祖调心图》、元代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等绝佳绘画。京都国立博物馆、京都泉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出光美术馆等地,都有青铜器、唐三彩和绘画作品。日本的中国文物收藏特点是分布极广,各地馆藏都有自己的中心,研究家众多,研究水平相当高。如以甲骨文收藏为主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文库等,收藏的中国甲骨达到万余片,占现有出土甲骨文近五分之一。笔者的先父善书法,曾有日本所出的《书道全集》一部。笔者幼年翻阅即为其中所收入的中国历代书法精品所惊叹,但一直不知藏于何处,及至有机会看到日本东京的书道博物馆,才恍然大悟,原来此博物馆的创立者中村不折是参加过1895年中日战争的军人,曾于中国获得过《淳化法帖》等珍品。
最后是美国。现代美国收藏的中国文物数量之多不亚于日本。美国收藏的特点是藏品宏富,特别是以艺术与绘画最为突出,文物交易活跃。波士顿博物馆就是以收藏中国文物起家的。这里收藏的文物有:北齐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宋徽宗的《摹张萱捣练图》等,相当多的藏品是中国画家一生都难能一见的真迹。纽约的都会博物馆是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其中收藏的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图》、龙门石窟宾阳洞《皇帝礼佛图》、《皇后礼佛图》以及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楚帛书,也早为世界所熟知。此外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费城大学博物馆、西雅图艺术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中心等,无不收藏着中国文物珍品。伴随着这些珍品,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盗抢盗卖文物的历史故事。笔者曾经从美国东海岸向西海岸穿越北美大平原,每到一个城市的博物馆中,几乎都可看到中国文物,不禁为之感慨万分。
除此之外,德国的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爱米塔什博物馆,瑞典的远东古物博物馆与土耳其的博物馆,也收藏有宝贵的中国文物。
对于中国文物海外流失总数,各种说法不一,从数万到数十万直到百余万的说法都有。笔者原则上同意台湾学者王景鸿女士的看法,如果将历年流失文物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走私高潮的文物一起计算,总数可能达到170万件以上。数量之大,举世无双!
征约的途径与设想
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多元化,这就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文物是民族文明的物质化形态,征返殖民掠夺所造成的流失文物,是维护民族文明独立主体性与文明整体性的重要途径。同时,打击文物走私与盗运是当前文明对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建立新的世界文明关系与秩序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与有关部门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与工作。当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积极进行国际文物征约工作已经势在必行。笔者以为:
第一,根据国际法与联合国关于文物的条约,所有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中流失国外的中国文物应当归还中国。西方一些博物馆隐匿收藏,有意在出版物中不注明与不公展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文物流失既有国际文物流失的共性,又具中国文物流失的的特性。中国不同于希腊这样的欧洲国家,也不同于印度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旧地,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其文物流失途径与方式极为复杂。我国应当组织由历史学家、文物学家、比较文明学家、国际法学家与外交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团,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及相关国家进行对话,共同商讨文物征约的相关规定,建立起既有国际普适性又有中国适应性的法律与模式。
第二,对于由于中外文明的历史复杂语境而流失的文物,应当建立国际对话的有效机制,采取协商归还与有偿归还等多种方式进行。我国应首先明确流失文物征约主体与客体,落实主要征约主体,即明确由政府何种部门主管此事,不要一哄而上。以笔者之见,征约关系是高层次的国际文明关系工作,必须由省与直辖市级以上文物管理部门成立专门部门组织司事,征返到位的文物也应妥善保存。
目前,部分西方国家博物馆已经主动提出归还中国文物的意愿,如瑞典的远东博物馆是收藏中国古代彩陶器最多的地方,现在收藏在瑞典远东博物馆的中国彩陶器数量居西方国家之首。据有关方面报道,瑞典远东博物馆在归还中国文物方面态度积极,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在与其他国家文物征约尚未纳入相关进程之前,建议首先以瑞典远东博物馆等相关文物收藏地为切入点,通过协商,迎归中国流失海外的彩陶器,取得经验,推动下一步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文物征约工作。
第三,由于文物征约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复杂问题,部分文物可以采取先行展出的方式,即与海外文物收藏机构协商,有计划地定期将中国流失文物组织到国内展出。据有关报道,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单位正在与美国相商昭陵六骏石刻的中国展出事宜,这也是值得探索的一种方式。
第四,建议全国人大通过流失文物征约法,明确规定海外流失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禁止任何方式的买卖、赠予和转让。修改国家文物的法规与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禁止未经鉴定的文物交易,限制文物市场商店与个体的经营活动。打击文物走私,重刑治理文物盗掘、盗卖等。发现走私文物应当及时追回并与相关国家进行协商相关善后处理。逐步与相关国家签订互不进口与买卖文物协定,彻底杜绝文物流失现象的发生。
第五,规范文物市场与私人收藏。对于海外个别以蠃利为目的的拍卖行、典当行与文物收购部门,通过所在国与国际法中关于文物买卖方面的有关条款进行交涉,直至采取相应的制裁行动。文物征约关系到民族文明创造与历史价值的评价,民族尊严与信心的确立,近代以来,数辈仁人志士为保护中国文物与文明传统贲志以往,贡献身家性命靡不有计,更有甚者累及家族世系,这些都是我们所难以忘怀的。在全球化时代中,从理论上认识征约工作的重大意义,是我们目前相当重要的任务。
论述至此,笔者认为还有三个相关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爱国人士的捐购,即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爱国人士购买流失文物后捐献给国家的爱国义举。港澳台及世界各国的华侨爱国人士是活跃在中国文物征约中的重要力量,这是早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的。港澳台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厚感情,是最主要的动力。世界大航海以来,欧洲殖民先行者从不同方向汇聚在南中国海,完成了世界性的大殖民。南中国海的港澳台经历了四个多世纪的殖民风雨侵蚀,是中华民族负担最为沉重的直接承受殖民侵略的地区,港澳台民众目睹了西方殖民主义掠夺中华国宝的暴行,他们宁愿舍弃家产也要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每一次捐购与赠送都充满爱国之情。同时,由于经济发达,财团众多,华商实力雄厚,他们有实力购回流失文物。2000年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竟然公开拍卖十二生肖铜兽首中的三件文物,国家文物局曾正式致函两拍卖行,然而,拍卖竟然继续进行。现在十二生肖铜兽首中的五件经保利集团及港澳台人士购得捐献国家,其余七件仍然流失。已经收回的是2000年保利集团从香港拍卖行购回的牛、虎、猴三件,2007年何鸿燊购得后捐献国家的马、猪两件,另有鼠、兔、龙、蛇、羊、鸡、狗等七件尚未能收回。但是,中国人回购文物也使得国际文物投机商有机可趁,他们大量走私中国文物,哄抬文物价格,骗取资金。因此,在中国文物征约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是做好港澳台各界人士的工作,首先要积极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同时要动员各界人士不要轻易捐购因战争原因或非法出境的文物,根绝文物非法买卖。同时,欢迎爱国人士以其他各种方式促成文物归返中国,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二是国内研究机构出于科学研究需要的购买活动。近年来,国内科研机构通过各种方式购回了流失海外的大批文物,其中也有受到国际国内企业或个人赞助的。应当肯定,这种购买活动都是爱国之举,并且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考古、历史、古文字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但是所购回的文物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近年来走私的文物,如20世纪末期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的战国楚竹书,近年来清华大学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单位购回的竹木简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古墓被盗现象严重,大批珍贵文物被走私海外,文物走私贩非法谋利,国家遭受了重大损失。这种文物回购会激起走私贩更大的贪欲,对于国家形象也不利。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国家立法禁止各单位团体与个人购买境外文物,同时希望各单位与学者不购买非法流失文物。笔者本人研究比较文明学,深知重要的陶文、金文、竹木简、甲骨文与石刻文字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尤其是涉足这些领域的都是硕学巨儒,其中很多人对于笔者都有赐教授业之恩。但为了国家与民族文明的利益,务请原谅冒昧建言。
第三是台湾地区文物部门如何应对海外流失文物征约的问题。台湾在国际文物市场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并且有很强的购买力。但是台湾学界一些同行与我们大陆关于文物征约的见解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讲学台湾期间,台湾学者多次与笔者在学术讨论会上涉及流失文物征约问题,相当多的学者主张购回文物。因此,如何协调海峡两岸文物相关部门的合作,共同拒绝非法流失文物的回购,联合起来征约海外流失文物,也将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欧文·拉兹洛. 戴侃、辛未译. 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
[2]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3.
[3]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845.
[4]上海大学古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