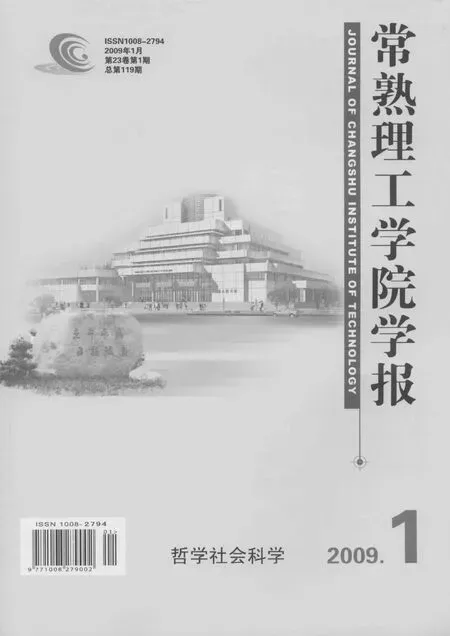诗运与时运
——二十一世纪诗坛预测
2009-04-20施议对
施议对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
诗运与时运
——二十一世纪诗坛预测
施议对
(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
孔夫子考察子贡,看其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与言诗,其中有个条件就是,告诸往能否知来者。可见,所谓知来者,亦即预测,实际上就是对于诸往的一种回顾与反省。主要看,能否从中吸取点什么。故此,对于本文,亦当只作一般文章看待。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诗词读本的出版状况以及诗界、词界领袖人物的预测;第二部分,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生死搏斗;第三部分,总结经验,预示未来。
新体白话诗;旧体格律诗;死而复生;生而复死
一
中国传统诗词,自两千多年前的古歌、古谚谣,到诗经、楚辞,到汉魏乐府,到五、七言古诗,到唐代近体诗,到宋词、元曲,乃至于当今的各种流行歌曲,品种繁富,姿彩各异,为大中华的文明建设,提供宝贵资源。二十世纪,对于新诗与旧诗,亦即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两种不同的诗歌样式,究竟孰胜孰负,孰存孰亡,这么一类问题,纷争不已。直至世纪之末,权威出现。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1]新诗与旧诗,方才相安无事。
我这里所说旧诗,所指乃一般的古典诗词。这一种诗歌样式,通常被叫做旧体诗,或者古体诗。这是相对于新体白话诗而说的,因称之为旧体格律诗。二十世纪,自从胡适声称,五百余年来诗词为“半死之诗词”①胡适《札记》第十册五年四月五日夜有云:“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参见《尝试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3页。,旧体格律诗就一直不得翻身。既不受史家的重视,作者与读者也不敢正面对待。世纪之末,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也有让人忧虑的问题。比如:大家都来写作旧体诗词,大家都是诗人。诗坛上,既有诗官,又有官诗;既有诗商,又有商诗。各种各样的交易,各种各样的诗集与词集。有序、有跋,有题、有赞,风头十足。无论自己出钱买书号出版,还是不要书号,应有尽有,令人应接不暇。这一状况,究竟好或者不好?其发展前景又将如何?1999年12月31日,在新世纪到来之前,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以“百年回顾,迈向新世纪”为题,刊登程千帆、饶宗颐、王伯敏、葛路、朱金城等十四名学者文章,以表达观感。应主事者之邀,对于二十一世纪诗坛,本人亦曾尝试作了两项预测。
第一,出版读物:从经典读本到经典读本。
第二,领袖人物:(1)从胡适之到胡适之。(2)从王海宁到吴海宁。
两项预测,通过回顾以往以展示未来。出版读物,是有关诗词的阐释文本。二十世纪,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五十年间,真真正正走了一个大圆圈。先是诗界前辈的几部读本,如余冠英的《诗经选注》《汉魏六朝诗选注》,冯至、浦江清的《杜甫诗选》,以及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甚是受到欢迎,堪称经典;再是鉴赏热的出现,带抄连炒,将原有作品解读变成为诗学辞典、词学辞典,而所谓美学阐释及文化阐释,又将原有诗学之发明,换上玄学包装,两个方面的读本,充塞市场,掩盖万有;最后是白文文本出现,预示,一切将从头来过。白文文本,不加任何注释、品评之读本。这是对于抄风、炒风以及玄学之风的反动。新旧世纪之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有关诗经、楚辞、乐府诗集以及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李白、韩愈、杜牧等作品全集,即为其中精品。二十世纪,出版界之由经典读本到鉴赏辞典,由鉴赏辞典到阐释文本(美学阐释以及文化阐释),由阐释文本到白文文本,其种种迹象,已清楚表明,二十一世纪的出版读物,必将返回经典。而所谓经典,则应当包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读本,有清代或清代以前之所传,亦有近人之所述作。对于出版界所出现的这么一种循环,于世纪之末,在有关文章中,本人曾以下列程式对之加以描述。

至于领袖人物,说的是新体白话诗的出路以及词学批评模式的运用问题。新体白话诗,从它的诞生,到成长、壮大,到困惑、迷茫,至今已将近一百年。在这一期间,词学研究经历其开拓期、发展期,乃至蜕变期,同样处于困惑、迷茫状态。谓:从胡适之到胡适之。指新诗旗手,除了胡适之外,还应当是胡适之。一百年前,胡适领导文学革命。试图“为大中华,造新文学”(胡适《沁园春》词句)。在以白话写作新诗过程中,有“胡适之体”,为展示康庄。“胡适之体”是以白话(或口语)创造的格式解放、体质充实、风格诙谐的新词体。可称之为“解放体”,或“白话体”,与大陆诗坛所通行的“干部体”相当。为诗?为词?身份并不怎么明确。例如《飞行小赞》:
看尽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也腾云无碍。
这是一首词,也可以说是一首诗。1935年4月7日,发表于北平《独立评论》第一四五号,后收入《尝试后集》。前四句说“飞行”,不须半天时间,便看尽柳州、桂林山水;后四句为“赞”,不修不炼,腾云无碍,赛过神仙。当年上海文艺界展开所谓“胡适之体新诗”的讨论,有人将其作为“胡适之体”的例证,胡适亦认可。曾说:“其实‘飞行小赞’也是用‘好事近’词调写的,不过词的规矩是上下两半同韵,我却换了韵脚。我近年爱用这个调子写小诗,因为这个调子最不整齐,颇近于说话的自然;又因为这个调子很简短,必须用最简炼的句子,不许有点杂凑堆砌,所以是做诗的最好训练。我向来喜欢这个调子,偶然用它的格局做我的小诗组织的架子,平仄也不拘,韵脚也可换可不换,句子长短也有时不拘,所以我觉得自由的很。”[2]66其时,胡适明白指出,自己乃以词调的格局做小诗组织的架子。可知,其用意似乎已不在作品本身,而在于以“倚声填词”的方法写作新诗,为新体白话诗创作开辟新路。不过,对于胡适的用意,无论新诗作者,或者旧诗作者,亦无论当时的诗评家,或者后来的诗评家,几乎都不曾理会。故此,世纪之末,我曾以“旧文学之不幸与新文学之可悲哀”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以表达观感。以为胡适的“文学革命”,令旧文学白白挨了一刀,新文学对之也并不领情。进入二十一世纪,诗界倘若还有什么革命的话,不知是否仍将胡适的帅旗扛将出来。谓:从王海宁到吴海宁。指词界领袖人物,于王海宁之后就是吴海宁。两个海宁,一个是王国维,另一个是吴世昌,皆浙江海宁人氏。二氏生世艰难,而都颇具开拓精神。王国维倡导境界说,创立中国新词学。王之前,词的批评模式是本色论,以似(词)与非似(词)论优劣,属于旧词学;王之后,推行境界说,以有(境界)与无有(境界)定高下,属于新词学。王国维堪称中国当代词学(新词学)之父。二、三十年代,境界说被推演为风格论,由“词以境界为最上”,变成为“词以豪放为最上”。之后数十年,直至蜕变期的反思探索阶段(1985-1995),某些具有一定创造精神的论者,包括风格论者,相继认祖归宗,回归境界说。吴世昌标举结构分析法,以生(联系)与无生(联系)为中介,通过事,将物与我、景与情,联系在一起;使情、景、事三者重新组合,造出另一境,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由结构分析法到词体结构论,为词学本体理论的确立奠定基础。二十世纪,境界说之被异化及再造,从离开本位到回归本位,无论其反面,或者正面,都源自王国维,乃王国维的世纪;而词体结构论,不知何故,却颇难获得认同。进入二十一世纪,由李清照、王国维、吴世昌所建造的三座里程碑、三种批评模式——传统词学本色论、现代词学境界说、新变词体结构论,随着词学新生代的崛起,也许将越来越引起注视。
两项预测,前者从图书市场的变化,看读者的价值取向;后者从批评模式的转换,看词学学科的衰微与兴盛。2000年4月,在中国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闭幕式讲话,曾说及这两项预测。(详见拙文《以批评模式看宋代文学研究》,载《新宋学》第一辑)。以下,准备说第三项预测,关于旧体格律诗的创作问题。
二
1916年7月22日,胡适第一个尝试以白话文创作新诗。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因此进入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将近一百年时间,如果将诗运与时运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那么,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争夺过程,即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16年至1976年,为第一阶段,六十年;1976年至2036年,为第二阶段,亦六十年。第一阶段,已成为过去;第二阶段,方才过去一半。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诗之工与不工,与时运究竟有何牵连?于这两个阶段,应可获知大概。
第一阶段(1916-1976):旧体格律诗之死而复生
二十世纪,由胡适所引起的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争夺战,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两种不同诗歌样式的生死搏斗。但是,六十年间,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却并非完全处于互不相容、互相排斥,或者互相替代的状态,而曾两次相互调换位置,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动。一次是旧诗向新诗的流动,另一次是新诗向旧诗的流动。两次流动,我曾称之为当代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当是十分有趣的一种现象。不过,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就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发展趋势看,这是两次生死轮回的必然结果。
(一)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第一次生死轮回
胡适所作第一首白话诗——《答梅觐庄》,计一百余句,一千多字。其时,作者就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原本只是友朋间有关死字、活字问题的争辩;没想到,事情越弄越大,竟“引起了一场大笔战”。事缘当年,《留美学生季刊》同仁在绮色佳聚会,任叔永有四言长诗《泛湖即事》寄胡适。胡适看后写信说: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二十世纪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叔永不服,回信辩驳;而梅光迪(觐庄)则致书代抱不平。谓文学革命“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3]113-118。以此之故,胡适做了这首白话游戏诗进行答辩。但是,正因为如此,所谓新文学与旧文学以及活文学与死文学,才有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这里,先看看胡适当时,究竟是怎样将事情做大的。1916年8月21日,胡适日记记载:
我主张用白话作诗,友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他人亦不必都用白话作诗。白话作诗不过是我所主张的“新文学”的一部分。前日写信与朱经农说: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章:
(1)不用典。
(2)不用陈套语。
(3)不讲对仗。
(4)不避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5)须讲究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6)不作无病之呻吟。
(7)不摹仿古人。
(8)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面。
能有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话。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要捣毁我的实验室。[4]
在与友朋的答辩过程,胡适尽量避免意气用事,考虑问题,都较切合实际,并且善于从对面设想,于另一个角度进行反省。胡适深知,人各有志,不必强同。因将自己的主张,归结为新文学八事。依此八事,进而撰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为“文学革命”纲领。就方法论而言,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提升。而实际效果,即将朋友间的答辩,纳入“文学革命”轨道,令其以白话作诗的主张,成为“新文学”的一部分。
1917年1月1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新青年》杂志二卷五号发表。2月1日,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亦于《新青年》杂志二卷六号发表。此时此刻,诗运与时运,已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因而,这场“大笔战”,也就不单单是友朋间的事情。当时,《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其二卷五号,除刊登胡适的文,还刊登胡适的白话诗《蝴蝶》。1918年,四卷一号(1月15日出版),刊登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白话诗九首。《新青年》遂成为最早发表白话诗的刊物。至1919年,《新青年》外,并有《星期日》、《觉悟》、《星期评论》、《工学月刊》、《学灯》、《少年中国》、《新生活》、《新潮》、《平民教育》等杂志及报纸副刊,亦相继刊登白话诗。1920年,胡适《尝试集》及另外两部新诗集(《新诗集》及《分类白话诗选》)出版。所谓时势造英雄,胡适之作为文化革命的旗手,局面已经展开,地位亦已经奠定。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新体白话诗,是借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声势而兴起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著书立说,“警辟之至,大快人心”(鲁迅语)①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出版之前,曾寄赠鲁迅。鲁迅于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书云:“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过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成,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参见《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以白话文创作新体诗,当其初起之时,生机蓬勃,甚是引人注目。而旧体格律诗,随着旧文化、旧文学之遭受抨击,则出现濒临绝境的危机。其时,若干旧诗作者,如沈尹默、俞平伯诸氏,纷纷改途易辙,写作新诗。于是,诗坛上出现第一次流动,乃旧诗向新诗的流动。
沈尹默,“五四”之前已有诗名,“五四”时期为《新青年》编辑之一。俞平伯,四代家学,旧学根基深厚,1916年所作五律《丙辰上巳公园》,技法已甚圆熟。沈、俞二氏,尤其是俞,其对于刚刚出世的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体白话诗出现,有反对者指出:“你们这班人都没有诗人的天才,要来冒冒昧昧改造中国是决不行的,好比一个极好的题目,给‘冬烘先生’糟蹋了,你看《新青年》、《新潮》登载的白话诗,不中不西,像个甚么呢!”对此,俞平伯即予反驳,并说明:“不是我们大言不惭说我们的确有诗人的天才,我们并且还承认我们恐怕不是;但尽管不是天才,学做几首诗,也没有多大害处,果然真有极好的新体诗出现,我们自然愿意‘改途易辙’的。太阳出了,萤火灭了;雄鸡叫了,夜猫没有声音了;我们做萤火、夜猫的资格,谁还能说不够呢!我以为天才既没有一定的标准,也不是‘生而知之’的,我们是个现代的人做现代的诗,不论好坏,总没有甚么不可。至于谁是天才,谁不是天才,将来自然知道。现在只要大家往前去,有一分力做一分事,我们也丝毫没有客气。”[5]
1918年5月,俞平伯于《新青年》四卷五号发表新诗处女作——《春水》,与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同时面世。1922年3月,于亚东图书馆出版《冬夜》,乃继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之后,中国最早新诗结集之一。俞平伯不仅在创作上努力实现“极好的新体诗”的出现,而且在理论上对于新诗所谓“真正精神和价值”的存在加以科学说明。俞平伯主张: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就得先明白怎样做人。这就是俞氏的诗学观。那么,从这观点出发,其所谓“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6],也就能够比较有意识地显示新诗的精神和价值。
胡适宣称,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7]57。他将以白话(国语)作诗,当作建设“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一场大辩论,他的信心更加坚定。胡适以为:“白话文学在小说词曲演说的几个方面,已得梅(光迪)任(叔永)两君的承认了”,“现在我们的争点,只在‘白话是否可以作诗’的一个问题了。白话文学的作战,十仗之中,已胜了七八仗。现在只剩下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可说是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3]119
(二)勒马回缰与批判反省
由于胡适的坚持,即使“同志太少”,“须单身匹马而往”,也还是努力做他的试验,诗界最后壁垒,终于被攻破了。旧体格律诗与新体白话诗所展开阵地争夺战的第一个回合,新体白话诗占优势,旧体格律诗败下阵来。但是,“文学革命”毕竟不同于文化运动,诗词创作毕竟也不同于白话运动,不单单是个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问题。因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新诗阵营亦曾展开反省,有的作者甚至还给自己的阵营来个回马枪。1920年8月15日,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曾坦率地说:《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两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
1922年3月10日,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又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922年5月,梁实秋在《读〈诗的进化的还原论〉》中称:“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闻一多以为“新文学兴后,旧文学亦可并存”,以为“律诗亦未尝不可偶尔为之”[8],而对于一味依傍外国,盲目按照别人的声口腔调写诗的做法则持怀疑态度。1925年4月,闻一多致函梁实秋,附录旧体诗四首,其中“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一首云: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舌鴃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9]
1926年5月13日,闻一多于《晨报》副刊发表《诗的格律》,提倡音乐的美、建筑的美、绘画的美。谓:新诗的格式区别于律诗之处在于,律诗格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而新诗的格式层出不穷;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因内容而异;律诗的格式由别人决定,新诗的格式则“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10]。闻一多并有《死水》诗集,为新诗创作提供样板。
(三)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的第二次生死轮回
新诗阵营,自我批判精神,甚可钦佩。只可惜,此后几十年,新体白话诗创作仍然不如人意。其发展、演变之具体情状,究竟如何?所谓困惑、迷茫,是不是已经到达走投无路的境地?有关种种,尚待新诗界有识之士对之加以描述。这里,只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些状况,而且主要是大陆诗坛状况。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此言一出,颇有些震撼,而论者则各自发表观感。或以为,十分伤感而又无奈,或以为,是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的彻底否定(因曾调侃新诗,说给二百块大洋也不看),或以为,主张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将导致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复归,白话诗下台。看起来,时势发展似乎对新体白话诗不利,实际上,当时的旧体格律诗,命运也不见得比新诗好。由于早在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中,就曾指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并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体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因此,旧体格律诗的创作活动,大致都在地下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似乎都遵循着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须要有身份、有地位者,方才有资格发表旧体格律诗。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诗坛,则只有毛主席诗词和误以为毛主席诗词的诗词独领风骚。
1985年9月,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曾将《光明日报》《东风》副刊自1958年1月1日创刊至1984年间所刊载的旧体格律诗选编出版,其中所录,词作品不到百篇,诗作品二百余篇。有关作者包括:沈尹默、俞平伯、高亨、唐兰、沈从文、赵朴初、吴晗、邓拓、邓云乡等,皆非一般人物。而大批作者,包括长期退居乡里的老一辈诗人,其所作大多登不了大雅,只是自藏箧中,或者在二、三友朋中流传。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爆发“四五”诗歌运动。旧体格律诗创作,借势从地下转向地面。因而,也正是在这么个背景下,中国诗坛出现另一种景观——某些原来写作新诗的作家,如臧克家、陈迩冬、秦似、程光锐、刘征、丁芒、李汝伦等,皆转而专写旧诗或者写旧诗而兼写新诗。这是中国诗坛所出现的第二次流动,由新诗到旧诗的流动,也可以说是新体白话诗和旧体格律诗的第二次生死轮回。
第二阶段(1976-2036):旧体格律诗之生而复死
新体白话诗和旧体格律诗的第二次生死搏斗,旧体转败为胜,死而复生。旧体格律诗因此又被推上历史舞台。这一过程,如从“四五”运动算起,至今也已三十二年。就中国大陆而言,这是翻天覆地的三十二年。其间,诗运与时运,较前六十年,情况亦有些变化。不过,旧体格律诗于复生期,同样经历一场大辩论。议题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旧体格律诗究竟是虫,还是龙?为什么一再打不倒?论辩多时,至八十年代,各地诗词学会(协会)成立,在许多人看来,旧体格律诗不仅不再是一条虫,而且简直变成了一条龙。而且,随着开放、改革浪潮之兴起,旧体格律诗这条龙,更是从田间飞上了天。所谓形势大好,或大好形势,诗国处处,经常都能感受到这一气氛。
(一)复生期——由民间走向台阁
1.诗坛上的“两个凡是”
1976年10月,“四凶”覆灭。政治上出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随之,诗词界也有“两个凡是”:凡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会写诗词,凡是平反昭雪都要发表诗词。
1978年5月28日,北京《人民日报》于赵树理病逝不久,曾发表其遗作《金缕曲》,并附说明:据赵树理同志的亲属记忆,此词写于一九六五年初。原词无标题,词牌名为编者所加。原载《诗刊》第五期。其词云:
岁历翻新页。喜回头、一年过去,奇峰千迭。铁臂银锄高下舞,改变乾坤陈设。看不尽,山飞水越。处处红旗赶大寨,听歌声、洋溢乎中国。传捷报,满腔热。神州豪气多风发。任凭他、迷天雪乱,压城云黑。高举大旗红浪涌,多少雷锋王杰。开万世,太平事业。宇宙无穷无尽愿,愿征程、奋翼冲天阙。射白虎,揽明月。
其实,此词并非赵树理所作,而乃发表于1966年1月5日该报之《贺新郎》,题称《新年献词》,作者赵朴初。词云:
岁历翻新页。喜回头、一年过去,奇峰千迭。铁臂银锄高下舞,改变乾坤陈设。看不尽,山飞水越。处处雄心超大寨,听歌声洋溢乎中国。传捷报,满腔热。神州意气多风发。任凭他、迷天雪乱,压城云黑。高举大旗红浪涌,多少雷锋王杰。开万世,太平事业。宇宙无穷无尽愿,愿征程、奋翼冲天阙。射白虎,揽明月。
二词对读,只几处字面稍有改动。如“雄心超大寨”,改作“红旗赶大寨”;“意气多风发”,改作“豪气多风发”。为什么出现这一状况?同样一首词,两名不同的作者,先后于同一报刊发表。除作者自身所造成,比如,赵树理当时,或许见到报上新发表的词章,觉得不错,就将其抄录下来,存抽屉里,身后无知,致使家属误当手稿,找出发表,此外,一个重要原因,应当就是为着平反昭雪。所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发表旧体格律诗遗作,正显示其身份及地位。此类事例,在那个以道德政治为最高人生价值的年代,并非绝无仅有。
2.“一文一武两皮包”和“一武一文两草包”
1987年5月31日(端阳节),中华诗词学会在北京成立。以老一辈革命家及老一辈骚人词客为旗帜,以弘扬中华文化、继承传统诗教为号召,登高一呼,八方响应。无多时,全国二十几个省市,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诗词组织。直至今日,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已经有一万四千多名,加上各省、市、县诗词学会(协会)的成员和众多诗社社员,全国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人数,据闻,已在百万以上。旧体格律诗的组织及创作,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声势之盛,乃有史以来之所未有。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其创立之初,筹备委员会中几位核心人物之奔走、策划,亦甚艰辛。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果没有当初,也就没有今日。用某老干部的话讲,叫做发挥“余热”。即趁自身离开官场不太长久,加紧为诗词做点事情。从批个房子,给点钱,到拨巨款、办刊物,并配备编制,确实功不可没。2007年5月,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诗会元老、发起人之一王澍,曾撰《参与筹建中华诗词学会的往事钩沉》一文,用以备忘。而诗人荒芜,早在学会成立不久,则有《长安杂咏》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中一绝,歌咏诗词学会。有云:“一文一武两皮包”。1995年,撰写《新声与绝响》,误将荒芜名句之平起格记成仄起,变作“一武一文两草包”。王澍说:“草包”云者,不像荒芜风格;其谓“皮包”,乃指诗会筹委会相当于一家皮包公司。据此,我作了更正。但所谓“草包”云者,仍然在自己的脑海中,就像是一团黑云,始终挥之不去。因借此机会,忆古思今,以表示对于几位筹委的怀念,包括钱昌照、周谷城、姜椿芳以及周一萍、汪普庆诸前辈。不过,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讲,似乎也为诗词之走向台阁,令“草包”充当“司令”,创造条件,提供机会。这应是当初所料想不到的。
(二)覆亡期——变新声而为绝响
1.一步错着,生而复死
六十年,诗界领袖人物有胡适;第二个六十年,找不到代表人物,大家都是首领。诗词走向台阁,一批从第一线退了下来的老革命,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多年的革命精神及经验,带到诗词中来。所谓“臣之壮也,犹不如人”,自己的过去既已成为过去,那么,眼下之发挥“余热”,就当将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因此,一方面是,历史重任在肩,使命感沉重空前;另一方面却是,诗词自身之为篇幅所限,或者四句二十八个字、八句五十六个字,或者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七字《鹧鸪天》和《步蟾宫》,皆不堪重负。旧体格律诗创作,处于极端的两难局面。怎么办呢?有的人将自己的头颅,拴在人家的马车上,跟得紧没问题,如不小心,误踩禁区,或者忘记将临街的窗帘拉下,那就十分难堪。在这一情况下,为着政治正确,唯一办法,就是牺牲诗词。比如,将某些意思不太明确的意象,换上义界分明的概念,或将某些比较委婉的表达,换上直接的说教,以概念堆砌替代意象、意境创造。诗词活动,政治行先,以求得自我完善,一般不犯大过错。但是,破诗体,诬诗体,诗词自身则受到最大的损坏。第二个六十年,“干部体”的出现,令这一状况,愈演愈烈。
“干部体”,乃从“胡适之体”而来,又非完全等同于“胡适之体”。当初,胡适的试验品,尽管也有人不愿意接受,以为“没有一首不是平庸的”(朱湘语),但其“为大中华,造新文学”,于创作方法上的提示,于今相信并未过时。第二个六十年,“胡适之体”经过修正与蜕变,出现两种情况:一为胡适真传,一为其变种。所谓真传,就是对于“胡适之体”的效法与承继,能够真正得其佳处,接其衣钵。比如宋亦英,其以白话入词,解放词体,对于胡适建造新词体所产生的弊病,既能够妥善地加以克服,在词的体貌亦即艺术形相及作风上,又善于吸取所长,弥补其不足。因令其承袭胡适之格式重构,不至太离谱,有关“意近而旨远”的表现方法,亦收到较佳效果。其作风,亦于诙谐、幽默之外,补之以庄重。颇有出蓝之胜。这是“干部体”中的优秀代表。多年来,诗界之效法胡适,大多到不了这一层次。至于变种,乃“胡适之体”蜕变的结果。“胡适之体”的蜕变,指的是胡适解放词体之有关弊端与偏颇在中国诗坛所产生负面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其中,既包含“胡适之体”对于词坛的误导,又包含词坛对于其体的错解。相关事例,我在《中国当代词坛“胡适之体”的修正与蜕变》一文中,已加以揭示。这里,所谓误导与错解,既说明大陆诗坛之所以产生这么多政治标本,胡适摆脱不了干系,又说明无论是新诗作者,或者是旧诗作者,对于胡适当初之所创立,大家都会错了意。因为胡适之“胡适之体”,原意乃在于,为新体白话诗创作寻找生路,并非为着旧体格律诗。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对于胡适的试验品,新诗作者不学,旧诗作者学。而旧诗作者之所学,大多避难就易,不学好的,专学不好的。这分明就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而,新诗与旧诗之有今日,也当是一种历史的宿命。
2.诗词前景,可堪忧虑
二十年前,编纂《当代词综》,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词作者,依其词学观念及创作活动,我将其划分为三派:解放派、尊体派、旧瓶新酒派。当下,对于旧体格律诗作者,如依其地理分布,我看亦可将其划分为三大门类:台阁诗词、山林诗词及学院诗词。至于网络诗词,大体上应当也包括在这三大门类之内。
三大门类,而非三大派别。说明并非互相排斥。那么,各个门类之具体情状又如何呢?上文着重说台阁诗词。此外两个门类,山林诗词及学院诗词,尽管与之有所区别,而其弊病,却仍有共通之处。
文化大革命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对于旧体格律诗作者曾提出忠告:
你最好不要采用旧的律诗、绝句和各种词牌。例如,你用了《满江红》的词牌,而又不是按照它的格律,那么,最好另外起一个词牌的名字,如《满江黑》或其它,以便与《满江红》相区别。[11]
事隔三十余年,1998年9月,被学界推尊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在其为另一位国学大师饶宗颐《清晖集》所作序中,亦曾指出:
五四运动以来,白话诗兴。羡林平生不为诗,白话诗之成败,得与失,实不敢赞一辞。然而,既称之为诗,必有诗之形式。今之为诗者,实为散文,而必称之为诗,且侈谈理论,滔滔如悬河泻水,意气昂然。以外道如不佞者视之,诚属方凿圆枘,又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内容与形式之矛盾,登峰造极矣。间亦有从事旧体诗词之创作者,又多不识平仄,无论诗韵,致为新派所诟病。[12]
邓拓所说,指的是当时许多“笑掉人牙”的作品。挂着招牌,只是按字数多少填制。不管平仄韵部,也不管有无诗味、词味,填够字数,就算是一首“满江红”或“沁园春”。湖南一位农民诗人,曾以《浪淘沙》,嘲讽其做法。词云:
何谓浪淘沙。同志知吗。仄平声韵竟全差。若谓填词填字数,笑掉人牙。
学海本无涯。多读名家。滥竽充数误童娃。实在无聊难打发,喝碗香茶。[13]
而季羡林所说,则包括新诗与旧诗。新诗问题,留待下文细叙。至旧诗,谓不识平仄,似未点中要害。因为这些年来,经过多种训练,相关作者,于合辙归韵,大致上已不成问题。但序文所揭示内容与形式之矛盾,却带一定普遍性,新诗、旧诗,二者皆然。
就目前状况看,台阁体之备受非议,主要在其诬诗体与破诗体,而山林诗词及学院诗词,于体式、体制,一般技术、技巧,虽多讲求,但在意识形态上,紧跟、或不紧跟,激进或保守,亦经常令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三大门类所遭遇的困惑,依旧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问题。然而,最要命的还是,三大门类的作者,似乎都缺乏危机意识,缺乏自我批判精神。大多只看到一面,忽视另一面。自我感觉良好。似乎自己就是天生的一部诗词制作机器,丁亥、戊子,诗集、词集,没个完了。令得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堆积诗国与诗城。十多年前,曾向编辑、出版此类书籍的某主事者建言:以控制数量的方法保证质量。非但未见效应,相反却越出越多。没有刹车迹象。长此以往,诗将不诗,词将不词,奈何?
三
新诗与旧诗,其发展、演化,经历两次轮回,既为自身生长规律所制约,亦与时事相关。两个阶段,两次流动,须认真加以反省与回顾。两千多年前,孔夫子之考察子贡,看其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与言诗,其中有个条件就是,告诸往能否知来者。可见,欲知来者,必先对于诸往有过深刻的了解。而预测云者,亦然。
(一)形式与内容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一早就可以白话与文言进行划分,而新体白话诗和旧体格律诗两大类别之相互对立及相互融合,却于二十世纪方才出现。具体地说,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诗坛乃旧诗一统天下,以白话语体文作诗,方才出现新诗与旧诗的争斗,出现新诗与旧诗的第一次轮回。
论者以为,旧诗格式固定、格律森严,难以容纳新的思想内容。新诗之兴,其所推行变革,从语言开始,进而乃方法。1915年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转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火车上用叔永游戏诗韵,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寄给绮色佳诸友。其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3]103作诗如作文,就是要求用白话语体文作诗。而具体做法,胡适将其归结为两大步骤:第一,革新工具;第二,改良方法。谓:“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3]106至于方法问题,则谓:“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7]72。其创“胡适之体”,并将其经验归纳为三条戒律: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2]70-74。胡适以为,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谓:“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7]181
十分明显,这一新诗运动,旨在打破旧诗原有模式,借助西洋典型,以重造现代中国诗歌,其目标亦甚高远。
但是,新诗的成长,偏重于借鉴而忽视继承。所谓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培植不得法,几十年来,其成效一直未能达至令人满意的程度。胡适的试验,本来希望为新诗创作开辟生路。所作歌词,包括少数挂有词牌及多数不挂词牌而已被当作新体诗的词作品,本来就为着向诗界展示,以倚声填词的方法写作新体白话诗的经验。其良苦之用心及美好之用意,却一直得不到正面的回应。闻一多诸辈,从形式入手,进行音尺试验,尝试以新体格律替代旧体格律,并有《死水》为样本,亦激荡不起一丝涟漪。
第一个六十年,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困扰着新诗,却为旧诗的生存发展留下空间。第二次轮回,旧诗复活,新诗向旧诗的流动,在一定意义上讲,主要由新诗自身所促成。这当是新诗创造者胡适等人所料想不到的。
1987年,在《臧克家旧体诗稿》自序《自道甘苦学旧诗》中,臧氏曾明确宣称:“我爱新诗,更爱古典诗歌。我写新诗,也写旧体诗。‘我是一个两面派’。”并且,还以自己的实践论证:“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例如:“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这是臧氏所作七绝《灯花》的三、四两句。臧氏说:如果把它译成:“诗的感情不像潮水那般有定时,夜半袭来,好几次打开灯赶忙写下来。”[14]试比一比,明眼人自然会觉得哪一种有深味,哪一种平无特色了。
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诗歌形式创造史。旧体诗特殊的格式规定及其特殊的表现方法,造就一代又一代诗人。臧克家所谓“自道甘苦”,乃诗人体会有得之言,亦为重新选择及流动之重要依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本人有《胡适词点评》于香港刊行。曾辑录胡适挂有词牌及不挂词牌的歌词作品,计三十一首。试图通过点评,还以本来面目,以追究其创作原意。进入新世纪,并于北京中华书局刊行增订本。将其歌词增至现在的一百零三首。其中,二十九首挂有词牌,七十四首未挂词牌。未挂词牌者,皆已脱离歌词身份,作为新体白话诗,列归有关文集与诗集。今据胡适相关言论及有关词法,重新给挂上招牌,重新为之正名,谓为歌词,以见证其用心。但愿读者诸君,不会辜负老胡的一片心意。
(二)政治与艺术
中国诗坛,旧体格律诗之死而复生,至今三十二年。其所面临危机,与当初新体白话诗有所不同。新体白话诗的问题出在形式上,旧体格律诗的问题是,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障碍,主要在内容,亦即意象与意境的创造上。
二十世纪,时运决定诗运,体现于意识形态统治。这是非正常的决定,乃诗之不幸。而其自身,尤其是诗词作者,实际也应负上一定责任。如曰:“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或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旧体格律诗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非同于一般政治斗争工具,作者本来应有自知之明。只是,由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或由于其他什么缘故,当政治上某集团或个人,出现炙手可热状况之时,大多主动挂靠,自愿充当其羔与雁,以期成为一个组成部分。诗界这种自觉行为,自然而然,也就促进台阁诗词产生。三十二年来,官诗与诗官以及商诗与诗商两大景观的出现,已为提供无数事证。前些日子,台湾大选,国民党重新执政。诗界有人组团,带着颂歌,于清明节,赶往马翁墓前,为其祭扫。马屁拍到对岸,也是一有趣事证。不过,台阁诗词并非不能有。吉甫作颂,以雅以南。作为一介武夫,颂诗、赋诗,当时并未被剥夺资格。李白供奉翰林,其《清平调》三首,乃标准台阁体,同样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代伟大诗人。三百篇中,风、雅、颂,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作为颂诗,问题不在其自身,而在于如何赞颂。周谷城曾为慨叹:暴露黑暗易,歌颂光明难。在许多情况下,希望充当歌德派,看来也不太容易。尤其现在,政治斗争形势,如此错综复杂,碰上敏感题材,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为自己造成困局。此时,歌德派就更加难为了。这一状况的出现,除了主观意愿上的因素,应当还有意象与意境创造所产生的问题。
意与象,意象与意境,对其理解与创造,长久以来,大多以为内与外的关系问题,并依据唯物反映论将其划分为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即包含主观的意和客观的境两个方面,要求在创作上做到物我交融,意与境浑,心与物共,用一句比较通行的话讲,就是情景交融,或者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际创作活动中,由于意象本身的模糊性,有时亦产生歧义,造成误会。近日,某地一首歌咏地震的《临江仙》(废墟下的自述),就曾引起广泛争议,出现多种批评意见。而只就风与颂的立场看,有关争议则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或以为讽刺,谓不仅亵渎死难者,而且亵渎了词牌名,唤作“幸福鬼”可也;或以为讽诵(讽颂),谓“不为苍生说人话,只向豪门唱鬼歌”,民众尸骨未寒,已大跳忠字舞,应为文坛“谄媚派”之巨作[15]。这是一种情形。而另一种情形却是,作为意象自身,似乎也有一定期限。如说乡愁,用邮票和船票,乃至坟墓等物象以寄托乡情,虽曾产生过强烈的回响,由于时过境迁,不复依托,也就失去意义。眼下诸多物象,远不如白云、黄鹤,千载悠悠,来得长久。那么,为着紧跟,需要表态,只好以义界明确的概念替代意思含糊的意象,以色彩鲜明的政治术语入诗、入词,用直接说教的方式,替代意象、意境创造,因令得大量标语、口号、顺口溜一类作品,充塞诗坛、词坛。三十二年前如此,三十二年后,亦复如此。
当然,对于政治与艺术,乃至对于意象与意境的创造问题,也并非没有掌握得比较好的。前辈作者中,远一点的如李白,近一点的有刘永济,都曾为此积累宝贵的经验。刘永济精通文史,并懂得列宁、高尔基。至二十九岁方才填词。对其所作,曾有这么一段检讨。谓:“予曾于己丑年,都录辛末以后所为词。分为三集,曰语寒,曰惊燕,曰知秋。共二百有余阕。并为自序一首,以述予作词缘起。后更检阅,觉其中讥讽时事,忧生闵(悯)乱之作,不出文人旧习。一凭主观,所觉于卅年来客观存在中,巨大历史变革,绝无反映其发抒心情,流连光景之词,亦不出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殊无存稿之价值。偶读高尔基回忆录,自称曾思将其中从革命中估计知识分子作用之谬见删去,继思留此以告世人有何不可,且举列宁人当自错误中学习一语以自解,谓留之使世之以主观论事者知其非。然则予亦可以高尔基此语自解,存之使世人知我之过。”[16]刘永济以为:诗人面向巨大的历史变革,除了“为时”、“为事”,还应当“为自己”——表现个人哀乐。前者据白居易所说;后者即况周颐所谓“君子为己之学也”。否则,殊无价值。刘永济似乎以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赋诗作词,无论怎么忧生悯乱,皆不出布尔乔亚(Burgensis)意识形态。如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小资”。这是有关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至于意象与意境创造,刘永济曾以“沉思”二字,为揭奥秘。这是当年初学词,游沪滨之时,以其所作《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请益蕙风(况周颐),蕙风之所亲授。谓:“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16]此所谓“沉思”,蕙风未说明,刘永济亦未说明,只是暗自高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以李白为例,试加阐发。李白的《清平调》,咏名花、咏倾国、咏君王,谓“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既将名花、倾国、君王三者关系摆平摆正,又能见性情。表明并非只懂得拍马的奴才。其关键就在于,“沉香亭北倚栏干”那一刻所进行的思考。即从春风所释放出来的“恨”,体悟到“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不常好”这一放诸四海而皆准并且千古不变的定律。这就是“沉思”所达致的艺术效果,亦李白之所以成为李白的体现。相反,如套用蕙风的话讲,即可说,凡作词不能道“沉思”一语,就只能充当一名言必称“喳”的奴才。
眼下,中国诗界台阁、山林、学院三大门类,其所面临问题,尽管各有侧重,但对于前辈经验,无论正面,或者反面,都应当引以为镜。
[1]艾青.《马万祺诗词选》序[M]//马万祺诗词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2.
[2]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M]//尝试后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3]胡适.四十自述[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4]胡适.留学日记(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1002-1003.
[5]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M]//俞平伯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597.
[6]俞平伯.《冬夜》自序[M]//俞平伯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641.
[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M]//文学改良刍议.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8]闻一多.律诗底研究[M]//闻一多全集:第10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66.
[9]闻一多全集:第1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222.
[10]闻一多.诗的格律[M]//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137-144.
[11]邓拓.三分诗七分读[M]//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79:25. [12]饶宗颐.清晖集[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13]伍锡学.田畴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4]臧克家.旧体诗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15]刘鉴强.只向豪门唱鬼歌[J].亚洲周刊,2008(25).
[16]刘永济.录稿后记[M]//诵帚盦词.影印本.1980.
The Destiny of Chinese Poetry:A Prospect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21st Century
SHIYi-dui
(Department of Chinnese Macao University,Macao,China)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publishment of Chinese poetry and a prediction of leaders in poetic circles;the second about the struggle between free verse in the vernacular and metrical poetry;the third a summary of the past experience and a prediction of the future versewriting.
free verse in the vernacular;metrical poetry;reborn after death;
I207.22
A
1008-2794(2009)01-0032-10
2008-12-20
施议对(1940—),男,台湾彰化人,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