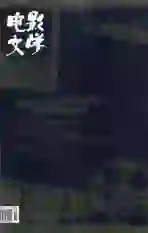从后结构主义视角看《呼啸山庄》
2009-04-16郑红莲
郑红莲
[摘要]《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的代表作,小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提供了大量有待阐释的材料。笔者列举了三个典型的片段,并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内容进行了解构和意义的建构,分析了三段的各自功能。
[关键词]《呼啸山庄》;后结构主义;解构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的作者是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30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19世纪及20世纪中22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讲述了一个爱情与复仇的离奇故事。19世纪,在英国约克郡一个阴沉的荒原边上,名叫希斯克里夫的一个吉卜赛男孩,被迪恩先生带到呼啸山庄。他得到主人之女凯瑟琳的钟爱,凯瑟琳在爱的同时,又无法拒绝自己想过优裕生活的愿望,而能提供这种生活条件的,却是邻居艾德加·林顿。希斯克里夫无意中得知后,悄然离去,凯瑟琳在愁苦心情中嫁给了林顿。几年后希斯克里夫风度翩翩地回来了,林顿的妹妹伊莎贝拉爱上了他,他买下了呼啸山庄,他与伊莎贝拉结婚以后,希斯克里夫的冷淡无情使伊莎贝拉很快枯萎凋谢,凯瑟琳也因为悲伤过度而濒临死亡。希斯克里夫在凯瑟琳弥留之际来到她身边,把她抱到窗前眺望那方岩石——那曾是他们的“城堡”,凯瑟琳曾说她会在那儿等待着,总有一天他们会团圆,然后死去。希斯克里夫心神错乱,在哀悼凯瑟琳、期待死亡中换了20年。他对周围一切人都极端轻蔑、百般折磨,直到凯瑟琳的幽灵在一个严冬的雪夜把他召唤到他们最喜爱的荒原上的某个地方,在死亡中重新聚会。
一、后结构主义概述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利用结构主义提供的基本命题继续推导,对符号、知识、主体性等范畴做了新的阐释,形成对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质疑,从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部分,同时也是许多反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语资源之一。后结构主义始于对作为结构主义基础的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的拒绝。索绪尔强调每个能指只有通过它在语言结构中的不同位置才获得其语义值;但后结构主义者们却通过例如尼采式的对强力的关注和弗洛伊德式的对无意识起源的关注来论证他们关于能指之间关系的说明。他们否认那种不变的符号统一体的存在,怀疑任何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语言的可能性。他们不相信作者对自己所写东西的真实意义具有最终的解释权,而是认为阅读是一个创造解释的积极活动,并非是对某个产品的被动消费。后结构主义拒绝关于意义的静态观念,敌视任何系统或任何去做系统构造的企图。认为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中定有真理并非是天经地义的看法,而意义也并非完全受制于真理性。思想彻头彻尾地由造成某个特定文化状况的习俗、常规、语言游戏和言谈所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力图颠覆对于语言结构的传统理解。
后结构主义强调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deconstruction),并且认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描写而得到的,是经过中介及被组织在话语中而领悟的,只通过“字”才同“物”联结起来的知识。结构不存在着终极意义,解释的任务不是去寻找意义,不在于关注它的普遍结构,而在于事物的本身和阐读过程,现实必须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解释”在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展开,而每一层又转化成为一个新的表意系统。因此,具体到文学领域,小说内容就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准确的表征,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中,阐述模式是需要重新建构的。阅读不仅仅是小说内容的转移和传递,更是读者主动建构图式的过程。
二、从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呼啸山庄》
为了更好地解构小说,分析全文结构框架,笔者以下面三个片段为例:
我把烛火放在窗台上,看见窗台一角堆着几本发了霉的书,油漆过的窗台上画满了各种字样,而那许多大大小小的字样,翻来覆去无非是一个名字罢了——“凯瑟琳·欧肖”,有些地方变成了“凯瑟琳·希斯里克夫”。后采又变为“凯瑟琳·林顿”了……(38页)
我曾经注意到在路的一边,每隔六七码,竖着一块石碑,连续不断地一直贯穿整个荒野。石碑还涂了石灰,好当做黑夜行路的指导,或是逢到一场像现在那样的大风大雪,两边的沼地与坚实的路径不可分辨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标志。可是这会儿除了这里那里露出几个黑点子外,这些石碑全都连影踪都不见了。(47页)
我在靠近原野的斜坡上寻找那三块墓碑,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中间的一块是灰色的,一半埋在石南树丛里;埃德加·林顿的墓碑脚下已爬上了草皮和苔藓,总算和周围的景色已有些协调;只有希斯克里夫的墓碑还是光秃秃的。
在那温和的露天,我在那三块墓碑前流连徘徊,望着飞蛾在石南丛中和钓钟柳中闪扑着翼翅,倾听着柔风在草上飘过的呼吸声,不禁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人能想象,在这样一片安静的土地下面,那长眠者竟会不得安睡呢。(285页)
这三个片段很相似,但每一段在呈现给读者的结构模式上有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使每一段都与其他任何一段不相协调。从语言表层上看,每一段都是“现实主义”描述,描述自然或人工事物。但所有的这些段落很可能不仅具有其所指涉的或历史的含义,它们很可能是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的象征或线索。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阐释,它们只是写出来,读者必须得自己去解读。只要你仔细阅读就会发现,每一个段落都体现了小说整体结构,体现了小说整体是怎样表现自身之外的意义的。并且每一个这样的段落都会导致对整体结构不同的论述。
1第一段从名字和姓氏的排列组合阐释小说
第一段导致的小说阐释,是从名字和姓氏的排列组合入手的。这种解读得力于两个家族谱系的血缘关系网,借助于解读主题。小说人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关系是通过几个人用一个名字,或者把几个人物的名字组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例如,“林顿·希斯克里夫”是希斯克里夫和伊莎贝拉的儿子的名字。这个人物的命名,采用了矛盾修饰法,它结合了两个不共戴天的家族的姓氏。《呼啸山庄》中的每个人物似乎都是系统里的一个构成因素,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具体的人,每一个人物是通过他或她在系统中的位置来界定的。整部小说,不仅第一代凯瑟琳的命运,而且第二代凯瑟琳的命运,还有第二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的关系,都浓缩在洛克伍德所发现的窗槛上刻画的名字当中,浓缩在他满脑子都是凯瑟琳的梦中。这个段落是整个小说的短暂浓缩。小说的全文拓展开来,是对这个缩影的意义的叙述。
2第二段为不同的总体化提供了模式
第二段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述了大雪过后约克郡乡村道路上的景象。如果认为每一处都可能是整体的一个线索,或整体背后隐藏的意义的线索,那么,该段落便暗示了整部小说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彼此连贯排列又前后隔开。读者的任务是在不同的部分之间连线,连出一个完整的图案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条连线便成了一条路,引导读者一步一步深入,穿过乡村到达终点,远离险途,最终进入安全地带。但如果犯了错误,猜测失误,假设了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路标,就会误入歧途、陷入困境。这种假设性的阐释过程所提出的论题或草案不足以发展。所以我们可以遵循伊曼纽尔·康德根据修辞学传统所提出的“生动的叙述(hypotyposis)”活动,在弄不清楚门路的情况下勾画出一个草案。这种做法给予那些没有实际名称或专有名称的事物以比喻性名称。就某种程度而言,读者的安全处境取决于他的正确理解。
3运用象征手法阐释文本和事件内涵的关系
第三段象征着整个文本和所叙述事件内涵之间的关系,叙事者和所叙述故事之间的关系,也是表明读者和故事之间关系的一种修辞手段。正像华兹华斯的许多诗是幸存者在墓碑旁边追念死者的墓志铭。小说《呼啸山庄》也可视为洛克伍德根据他零零碎碎的了解拼凑起来的回忆性叙述。当洛克伍德来到呼啸山庄时,第一代凯瑟琳已经作古,希斯克里夫还在痛苦地活着,但是他的“灵魂已经进入坟墓”。直到小说结尾,希斯克里夫追随凯瑟琳死去。最后,洛克伍德站在三座坟墓旁。墓碑是缺席的标志,整部小说中,洛克伍德无时不面对这种标志。他的叙述便是由此搭建而成的回顾性重构。小说的结尾处,洛克伍德的天真表现在,他无法想象死者还会在寂静的土地里不得安息。这片土地喧闹不安,这个地方隐藏着某种喧嚣的、不知名的生命,在洛克伍德看来,其证据就是石南丛中和钓钟柳中闪扑着翼翅的那些飞蛾。小说的结尾再次突出了一个讽刺性差异,即洛克伍德所知道的情况与他无意之中,止读者知道的情况之间的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以上三个段落中的每一段都体现了整个叙事的结构,体现了叙事整体与它所依靠的根由之间的关系,这个根由既是整个叙事的源头,又是它所指归的目标。无论把哪一处作为出发点,都能根据所提供的情况来阐释整部作品。每一种阐释都可以结合其他细节,以己为中心来建构,都可以导致不同的整体设计,而每一种设计都与其他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