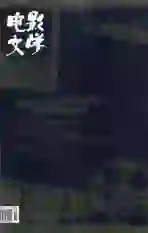论后民权时期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时代特征
2009-04-16唐红梅
唐红梅
[摘要]对于美国黑人来说,民权运动高潮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消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即后民权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对美国黑人女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后民权时期中登上文坛的新一代黑人女作家敏锐地感知了时代脉搏,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通过建构立足于个体体验的新价值观念,认同更加细化的黑人群体,呈现了作为道德自由主体的抉择力量,也体现了其文学创作具有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后民权时期;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时代特征
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趋向低落,由此开始的时期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后民权时期”(post-Civil Rights Era)。此一历史时间前后的社会文化差异,成为划分黑人作家不同代际的一个重要界碑。从美国黑人女作家文学创作的时代特征来看,在后民权时期成长和创作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构成了新一代作家群体。成长环境的变化,影响到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相对于此前登上文坛的黑人女作家而言,她们的作品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特征,而这些特征正是通过她们的创作与所处时代的积极互动反映出来的。对新时代社会变化的敏锐感知以及随之表现出来的主体抉择,成为后民权时期登上文坛的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时代特征。
一、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群体及其面临的问题
后民权时期黑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化,给黑人大众和知识分子精神与物资生活以重要影响。在后民权时期,美国黑人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都呈现出价值诉求多元化、内部分层更加细化、种族道德诉求弱化等的特点。。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对黑人作家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他/她们重新思考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影响到生活和文学中的需求,即对权威、真实性、代言人的新的构造和再现。”
而从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来看,社会变化产生的影响,首先通过成长于后民权时期的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反映了出来。在后民权时期,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仍然非常繁荣和昌盛。考察其内部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两个黑人女作家群体,一个为早在民权运动中就已经开始创作的黑人女作家群体,它以托尼·莫里森、艾丽丝·沃克、托尼·凯德·班巴拉为突出代表;一个则由民权运动退潮之后登上文坛的黑人女作家组成,它以特瑞·麦克米兰、阿莎·班德勒、丹泽·塞纳为突出代表。前一个创作群体大多出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民权运动时期成长并登上文坛,在七八十年代成名;后一个作家群体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之后,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尾声或高潮消退之后进入青年时期,在八九十年代之后开始步入文坛。
就美国黑人女性创作的研究来看,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第一个黑人女作家群体的创作发展,而较少研究新近登上文坛的黑人女作家群体的创作。然而,事实却是,时代的风云变迁及其对文学的新要求,却首先可能通过后一个作家群体的创作普遍地反映出来。虽然前一个作家群体继续在20世纪后期创作,并构成一股重要力量,而且也呈现了新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新一代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而言,她们的发展还只是一种在个人风格连续性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演变。以莫里森、沃克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在80年代已经抵达了自己创作的成熟时期,并登上了各种荣誉的高峰,失去了创新的冲劲与活力。深深地打上了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烙印的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民权运动高潮消退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
对于目睹或直接参加了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黑人女作家而言,种族隔离的社会制度和现实,是她们成长的社会环境,也是把她们联系起来,为黑人公民权利和种族社会平等而斗争的直接原因。跟这一代作家不同的是,成长于后民权时期的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她们成为前辈们为之献身的民权运动的直接受益者。她们的父母大多成了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成员,甚至文化精英人士。例如,阿莎·班德勒的父母都是纽约城市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丹泽·塞纳的父母都是享有一定盛名的诗人和作家。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优裕的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黑人女作家,她们的成长经历一定程度上折射了20世纪后期美国黑人女性社会空间拓展、物质条件改善、社会地位提高的现实。
在家庭和群体发生巨大变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黑人女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盛行于美国社会20世纪后期的消费文化之影响。大众媒体和新型传播方式,甚至流行的网络,都成为黑人特征被消费的市场,同时也成为黑人宣告自己存在的巨大空间。科拉·赞恩最初创作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其情色小说《沉溺》(Addicted)等先在网络中以电子版的形式流行畅销,然后才出版发表纸质版本。赞恩创作和其作品扩大影响的这种方式,就典型地反映出了当今美国社会黑人特征、黑人女性情欲、个体解放与网络文化、商品消费等因素复杂纠葛在一起的文学新现象。
在物质财富丰沛然而精神文化复杂多变,而且充满了差异和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新一代黑人女作家成长了起来。但是,她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在这个多元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盛行,种族压迫和歧视不再合法存在的社会里,个体相对获得更多的社会发展空间,价值观的追求、践行变得越来越具有随意性、个人化和生活化,甚至连社会道德伦理本身也在这个物质丰盈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被物质利益和消费主义所替代。代群体立言,即将个人价值通过追求群体利益而体现出来的道德实践行为,逐渐引起人们对这一社会行为的动机、目的之质疑或猜测;另一方面,不论是因为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一旦个体在社会空间的言说变得仅仅立足于、满足于个体自我经验的时候,其个体发言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合法性,但其言说本身却又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黑人女性知识分子进入公共空间不得不面临以上问题,它是后民权时期给新一代黑人女作家提出的社会问题,也是新时代带给她们的一个创作问题,需要她们进行艰难的主体抉择。如果她们仍然像前辈黑人女性作家那样,将个人价值实现,通过为黑人群体追求利益来完成,那么,她们将不得不面对种族内部倾向多元和差异的价值判断的挤压。如果她们放弃对群体的认同,就不得不面临自我创作的悖论,也即群体身份从个体文化身份的剥离导致言说本身社会针对性的丧失和言说立场的逼仄,稀释了其面向公众的写作行为本身的社会性,威胁了自己作品的权威性。如果这样,又如何建立其颇具说服力和公信力的言说立场和权威呢?又怎样使得自己的言说更具合法性与有效性呢?
二、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主体抉择
以上这些问题,就是新时代向黑人女作家就其创作的合法性身份提出的问题,也是思考黑人女性创作在新时代的发展以及后民权时期登上文坛的黑人女作家创作环境和创作特征时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在面对以上创作问题时,新一代黑人女作家没有回避,而是进行了积极应对,体现
出如下的主体抉择。
首先,面对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新一代黑人女作家并没有迷失在个人生活和情感的抒写中。以此逃避任何潜在的指责,而是积极承担种族文化使命,选择和建构新的价值观念,通过文学叙事积极回应现实生活中黑人女性的现实困境,以此呈现出对种族内外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姿态。对黑人女性生活的关注,或者以黑人女性的独特体验作为审美观照的切入点,是当代黑人女性作家的客观生活使然,也是她们自觉的选择。
新一代黑人女作家的创作都反映出来了她们将个体经验跟群体存在结合起来的特征,即通过认同某一黑人群体或黑人女性群体,她们为自己的叙事寻找合法性存在的依据。她们没有沉溺在个人的世界中,也没有在相对主义价值观的流行中丢弃对价值的质疑、判断与建构。科拉·赞恩的创作,可以视为这一特征的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例子。赞恩早期的创作行为是完全私密性的,为了打发孩子上床以后自己感到无聊的时间,她自己写作“有趣”的情色故事,并用电子邮件发给朋友,得到好评后,以假名“赞恩”放在了网络上。其创作中大胆、直白的性描写,使得其创作被称为“情欲文学”。但是,在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强调自己的创作与激进的黑人女权主义之间的联系。赞恩创作的发展,也许是源于她的权宜之计。但是,即便是如此,这也反映了黑人女作家面对现实问题时呈现出来的积极的抉择力量,即仍然通过认同黑人内部某一群体的价值诉求,而赋权于自我的文学叙事。
从个体的存在经验出发,由此走向与他者的认同,是这些黑人女性作家写作的策略,也是她们笔下黑人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阿莎·班德勒的作品《女儿》中,黑人女性米利亚姆最后在监狱中跟众多的黑人女性囚犯结为亲密无间的朋友;而小说对现实生活里被白人警察无辜枪杀的黑人青年名字的提及,也反映了作者将自我写作与群体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努力。在特瑞·麦克米兰的代表作《屏住呼吸》中,黑人职业女性群体直接成为其作品描写和赞扬的对象。
其次,如何在个人和群体之间找到合适的桥梁,从而避免评论界和读者对自我言说身份的质疑,在新一代黑人女作家认同更加细化、更具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群体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立足于个体的经验,代表与自己具有共同性的群体发言,而不是代表大而化之的社会和种族发言,是这些黑人女作家小说创作以及创作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征。更具个体性的物质和情感生活,成为她们感知、辨识可以认同的群体之出发点。同时,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带来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层,为黑人女性作家选择更加切合自我经验的、可以认同的群体提供了更具多样性的可能和合法性。例如,在《妈妈》《屏住呼吸》等作品中,作者特瑞·麦克米兰认同的是20世纪后期的黑人职业女性;在《女儿》中,阿莎·班德勒认同的则是受到具有种族歧视偏见的执法人员伤害的黑人女性;而在《高加索》中,丹泽·塞纳认同的是遭受歧视的黑白混血儿。
第三,新一代黑人作家的文学创作在价值诉求上呈现出新时代的气息和多样性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作品呈现的新生活和新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则是对种族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批判更具针对性和具体性。
对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批黑人女作家而言,马克西姆·X宣告的“黑人骄傲”信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她们的心中,致使这些黑人女作家在精神面貌上普遍地呈现出自主、自信、自尊、努力向上的特征。而随着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为社会权力“边缘之边缘”的黑人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社会进步的成果。于是,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纠缠在一起形成的压迫。渐渐被黑人女性面临的事业与生活的冲突、高强度的生活节奏导致的内心与外部生活的矛盾等等这些更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活矛盾所代替。
然而,当制度层面的不公得到纠正的时候,意识形态层面的偏见并不能一扫而空,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并没有从黑人女性的社会、家庭生活中彻底消失,尤其对于经济地位低下的黑人女性而言,这种社会和家庭的不平等表现得就要更为明显,也更加切实具体。
时代进步与意识形态滞后的冲突。成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生的一代黑人女性作家创作的社会背景,也成为她们创作呈现不同价值诉求的一个社会原因。对以特瑞·麦克米兰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而言,她们的创作更多地呈现了时代的新特征,侧重于建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上;而以阿莎·班德勒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来说,将黑人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种族压迫这一社会邪恶的具体体现联系起来,则成为她们创作的努力之所在。
总而言之,新一代黑人女作家对新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特征的认识以及这些认识在创作中的表现,反映出黑人女性文学在后民权时期的一些发展趋势。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的文学创作呈现了与上一代黑人女作家创作之间的承接,但是更多的却是其中的独特性,而正是这一独特性让我们看到了后民权时期的社会文化烙印。
在时代和个体的互动中,新一代美国黑人女作家承接了上一代黑人女作家表达群体价值诉求的种族文化使命,积极建构适应时代需要的、维护黑人种族道德尊严的价值观念,反击了黑人内部、美国社会蔓延的相对主义价值观。而通过立足于更具个体性的存在经验,认同更加细化的黑人群体,新一代黑人女作家得以在种族、性别多重因素的纠缠中,找到一个有效代群体立言的位置,不仅反击了来自种族内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责难,而且还开拓了一条积极有效的文化策略和创作之路,回答了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呈现了其作为道德自由主体的抉择力量和时代特征,推动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