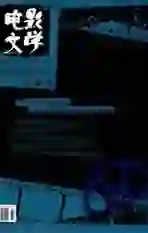论中国电影对书法美学思想的借鉴吸收
2009-04-14于军民
[摘要]中国电影植根于中国文化,故与中国书法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影的意境构成模式、蒙太奇组合技巧以及色彩的选择搭配都与书法联系紧密。中国电影应自觉在书法艺术等传统艺术形式中汲取有益养分。
[关键词]中国电影;中国书法;意境;组合;色彩
1895年年底,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他们自拍的《火车进站》等短片,以此为标志,电影宣告诞生。时至今日,世界电影的重心无疑仍在西方。美国好莱坞更成为全球电影人的梦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评奖和展览也在西方。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等享誉世界。
中国电影必须要追赶世界潮流,并要有雄心引领潮流。中国电影要想引领潮流,恐怕不得不立足于自己所在的文化土壤,以此为基础放眼全球,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找到一条融合之路、适己之路。所以,中国电影要想立足于本民族文化来谋求发展,就一定得在传统文化艺术以及古典文艺美学中汲取养分。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电影与绘画、文学、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不乏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揭示。比如,文学的各种体裁都曾经直接对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出现过诗电影、戏剧式电影、散文电影和小说电影。电影亦从绘画中借鉴了造型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在光线、影调、色彩、线条和形体上有颇多相通之处。而音乐更是电影必不可少的概括主题、抒发情感、渲染气氛的重要艺术手段。可是,作为传统艺术精粹的书法,对于电影的意义却始终鲜为人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书法艺术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在于它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以一种具体可感的形式融汇于这个民族的每个个体的生活中。跟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书法艺术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这种特点使它比任何艺术门类都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书法所折射出的美学观念,无疑是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的一种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家熊秉明曾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中国书法。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所以中国电影没办法不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中国电影应自觉地在书法艺术美学思想中汲取养料。
一
“电影艺术是通过画面、声音和蒙太奇等电影语言,在银幕上创造出感性直观的形象,再现和表现生活的一门艺术。”所以一般人认为,电影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画面和声音。人们通过画面和声音就能很容易看懂电影,不需要特殊的文化修养。但事实上,很多电影对于不少人来说显得过于晦涩、索然寡味,不明就里、云遮雾罩。观众看不懂电影,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恐怕与电影不全是画面和声音的产物有关。人物形象的喜怒哀乐不会完全通过言语来专递,很多时候是靠人物的一个眼神、一个身体动作来实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的。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关注正逐渐向内心体察过渡。如同恩斯特·卡西尔所说:“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显著。”因此,通过人物的眼神、肢体等非言语形式来传达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模式。这就不难理解尽管靠人物的眼神和身体动作传递信息和情感体验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性,但却是颇受电影导演推崇的一种表达方式,主要在于它具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美:富于暗示性、启发性、朦胧美,且虚实结合、境生象外。同时能真实而准确地传递言语无法传递的复杂多变的情感体验。电影的这种意境构成模式与书法很相似。书法同样是以一种相对抽象的方式传递意境的。书法虽然与绘画相比有“书画同源”之称,但事实上,以笔墨线条来抒情达意的书法艺术早已经脱离具体的物象之形而发展成为一门抽象的艺术。这种来自抽象线条的审美方式、意境构筑方式必须经过相应的专门艺术训练才有可能达到透彻的认识和理解。
电影和书法的这一特点告诉电影导演和表演艺术家,要在由抽象到形象的艺术传达方式上下足工夫,即是要在眼神和身体动作等非言语方式表演技法上努力探索,以无声胜有声,准确传递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人物性格的塑造更为典型、真实。书法线条常常一波三折、提按变化丰富,即使是最小的一个“点”画,其传达方式也决不是简单的一点了事,也依然要处理出一个含蓄的、耐咀嚼和玩味的“像外之像”“景外之景”来。这就告诉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决不可轻视作为角色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要知道并要努力去追求“举手投足间皆有戏”。
二
我们知道,电影是对一个个的电影镜头或画面以蒙太奇方式实现一个完整叙事的。这种画面的叠加与组合方式按照一定的时空顺序和审美要求叙述生活事件。而书法是以若干汉字的有序组合完成整幅作品的创作以表现书法家对生活的认知的,同样存在一个不容颠倒且经过精心谋划的时空顺序和审美主张。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影与书法亦表现出密切的相关与相似。
电影中的蒙太奇,本为建筑学用语,意为组装、构成。用于电影中,指画面、镜头和声音的组织结构方式。“组合”是蒙太奇最核心的美学内涵。“不但镜头与镜头、段落与段落,甚至画面与声音均可构成蒙太奇组合关系。”书法作品与此类似。在一幅作品中,字与字、字组与字组、段落与段落亦形成相应的有机组合关系,共同服从于作品的大章法,服务于作品意境美的营造。电影镜头有景别、焦距、镜头运动、角度、光线和色彩的丰富的变化。比如景别即有近景、远景、全景、中景、特写等变化,焦距亦有长焦、短焦、变焦等变化,镜头运动有推、拉、摇、移、降、升、跟等变化。电影镜头的这些丰富的变化的存在,使电影语言显得异常丰富。同时,这些丰富的镜头的变化形态又必须在剪辑时保持连贯与流畅,给人一气呵成之感。电影的这些美学特征使其避免了艺术行为最为忌讳的单调和呆板,同时又使电影画面极富感染力和表现力。书法作品尤其是最具艺术审美价值的行草书作品的每一个单字的处理,从总的方面说也是力求变化之美。书法家在处理每个字时,总是自觉地避免雷同;对于一幅作品中的相同的字,更是努力写出不同的笔法、字势与结构,以求变化。世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帖》,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成就即在于作品中二十几处“之”字的处理无一雷同,叹为奇观。此外,行草书作品还追求笔法的中锋与侧锋之变、藏锋与露锋之变、提按与绞转之变、方笔与圆笔之变;字法上,从线条对空间切割的均匀美与对比美着手实现“计白当黑”“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美学主张;墨法上,由于古人深信墨分五色,所以作品要体现浓、淡、干、枯、湿的墨色变化;章法上,要求大小、疏密、长短、欹正、缓急的结合,同时还要服从于通篇行气的贯通、流畅,前后字与字、字组与字组的呼应关系要明确。这些丰富的技法手段的变化、组合的变化,给书法艺术带来了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电影和书法的这些共同的美学特征,究其根本来说,正是中国哲学“对立的统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因此,中国的电影艺术有必要在书法艺术中汲取营养。一些具体
的处理技巧甚至可以一一对应。比如,电影里的长镜头,就好比是行草书作品里的一个长竖——饱含激情、不能自己、一泄如注而又曲折委婉、荡气回肠。这样的镜头或这样的线条往往成为整个作品的神来之笔,有画龙点睛之妙。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好比书法作品中放大的一个字形,不仅字形大,而且用墨厚重,极易吸引人的注意,是书法家重点表现的对象,这与特写镜头的初衷如出一辙。电影里的叙事段落,可看做书法里的字组或字群,这样的段落或字群往往表现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局部叙事或情感体验。
中国电影要体现民族特色,还必须在色彩选择与搭配上下足工夫,在色彩上体现民族审美意识。这一点,张艺谋的民俗和民族类电影体现得非常充分。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深谙中华民族对色彩的偏好,他的民俗和民族类电影只需透过画面色彩就能撼人心魄。《红高粱》中有铺天盖地的红色:红高粱、红酒、红色装扮的新娘、红花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黑色的院、白色的雪、红色的灯;《秋菊打官司》为了凸显红色,将卖猪改成卖红辣子;《我的父亲母亲》中年轻的母亲身穿红色大袄、扎着红头绳,成为观众内心永远灿烂鲜活的记忆。而《英雄》则以黑红两色为主,并融入李慕白的一袭白衣装扮。显然,张艺谋电影的色彩选择在有意识地强调民族性,强调通过色彩来拉拢与观众之间的审美距离。他的电影的三大主色调即是红、黑、白色。而这,亦正是中国书法的三大色调:白纸、黑字和红印。沈尹默说书法艺术“无声而具音乐之节奏,无色而具图画之灿烂”。书法艺术的黑白二色长期以来并不以它色调的单一而为人轻视,相反,却能幻化出无穷的魅力而让人顶礼膜拜,这是一件让人玩味的事情。事实上,书法中的黑与白,与太极图黑白两个阴阳鱼有着同样的哲学内蕴,意涉派生万物的本源,“一阴一阳之谓道”,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对阴阳、动静轮转,事物相反相成的宇宙观的体认。《老子》称:“知其白,守其黑。”这种“计白当黑”的虚实结合、境生象外的美学观“是中国艺术中最迷人的部分”,而书法无疑是最能体现这种虚实观的传统艺术。此外,书法作品中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印章,则选择了红色。一方面,红色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主色调,是喜庆、活力与生气的体现;另一方面,红色能起到厕龙点睛之妙用。虽然在作品中它偏置一角,本身并不会铺天盖地、随处出现,但却因能够与黑白二色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达到“对立统一”的功效,互相衬托、相得益彰,十分惹眼也非常必要。书法的这种色彩处理,毫无疑问可以为电影在色彩的选用、搭配、组合上提供参照——一方面色彩的选择与组合要符合民族审美习惯、民族心理,要努力达到相得益彰、互相衬托的功效,另一方面要善于借助色彩来营造一个让人迷恋、玩味的审美意境,给电影叙事以更多更丰富的意蕴暗示。
总之,中国电影由于植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书法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电影应自觉在书法艺术等传统艺术形式中汲取养分,为中国电影早日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尊重与赞誉而努力。
[作者简介]于军民(1974—),男,四川广安人,硕士,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