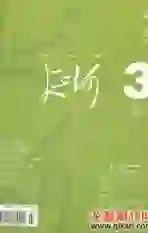碧血红叶
2009-04-13侯雁北
侯雁北 原名阎景翰,陕西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多篇。出版理论专著多部。
1
一大早,我就准时打开“李斐华图书馆”大门。门一开,我们的两位忠实读者就来了。他俩比负责借阅图书的女馆员——徐亚珍还到得早。我看看门卫室的电子钟,正是七点五十。徐亚珍是不会误时的。她的时间观念很强,从不迟到早退。我们图书馆没有生活用房,她住在距这儿很近的舅妈家。她常说她要对得起自己的爷爷,更要对得起李爷爷。她为自己定的规矩是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埋头苦干。
接着我便打扫院落。秋天来了,院内的两棵老枫树,每天都要落些半黄半红的叶子。馆长说这是两棵鸡爪枫。我的职责是看门和搞卫生,必须把鸡爪枫落下的叶子扫干净。连徐亚珍也发誓要对得起李爷爷,——她的李爷爷就是我伯父,她要对得起李爷爷,我能不对得起伯父吗?
我正扫着院子,徐亚珍果然来了。时间只差五分就是八点。
徐亚珍快速地踏上二搂,打开了图书借阅处的小窗户。
我打扫完院子,便去擦洗上下楼的扶手。正擦洗着,楼上便有人吵了起来:
“这书我一直借,你为啥要借?”
“这是你的书吗?你能借,我也能借!”
“我做笔记!做研究!”
“我也做笔记!做研究!”
徐亚珍从中调解:
“你俩别吵!好好协商协商。”
“没商量的,他能借,我也能借,这图书馆不是专给他盖的!”
“你一直读小说,这是一本药物学,你读得懂?”
“你能读懂,我读不懂?”
“你个神经病,你能读懂!”
“谁神经病?你才神经病!”
徐亚珍又从中调解:
“别吵!再吵,谁也不借!”
“不借?我不是读者?我不是云龙县人?”
“我不是云龙县人?我不是读者?”
他俩又一齐质问徐亚珍。徐亚珍为难了,站在楼道口喊我:
“李师傅,你上来一下,请你调解调解!”
徐亚珍在馆里一直称我李师傅。
我提着抹布走上楼去。徐亚珍还是个姑娘,她确实无法对付我们这两个最忠实的读者。
我得先了解一下情况。
这两个读者,一个叫郭大川,一个叫牛向学。郭大川前些年高考落榜,一心想当作家,这几年白日整天在这里读小说,晚上便开夜车爬格子。听说他已写了不少作品,也向几家报刊投了稿,但却一篇没发表出来,这便变得神经兮兮,连走路也撞过电杆;一次一辆卡车在他身后不住地响喇叭,他似乎根本没听见,急得司机跳下车来,将他拉在大路一旁。他站在大路旁像个木头人,呆呆地望着大卡车开走了,还不知那司机为什么要拉他。牛向学对中医钦慕已久,这两年一直在我们这儿抄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据说已抄了三大本,都装在一个蓝色布袋里,他每次来我们图书馆,手里都提着那衣袋。蓝布袋已变得油腻腻汗腻腻了。郭大川投稿不中,现已心灰意冷,昨晚才下了改学中医中药的决心,今天也要借《本草纲目》。
我对牛向学说:
“你也读读《千金要方》吧,那是药王爷孙思邈的名著。”
“我将《本草纲目》还没读完,不读《千金要方》!”
“这两部名著你结合着读。单日读《千金要方》,双日读《本草纲目》。……这样有好处!”
牛向学勉强地同意了,向我点点头。我问徐亚珍今天是几月几日?她说:
“公历10月31日,农历十月初三。”
我对牛向学说:
“公历、农历都是单日。好日子,好日子!今天你就借《千金要方》,明日再借《本草纲目》。两部名著参照着,对你大有好处!”
矛盾解决了,徐亚珍对我笑一笑:
“谢谢李师傅!”
我又下到一楼擦洗扶手。一楼的两间报刊阅览室,来了几个老年读者。他们把最新的报纸翻了翻,见多是证券、楼市、体育和贪官落马方面的消息,便拄着拐杖走了。
“李斐华图书馆”一下子恢复到平日的宁静。
李斐华是我远在国外的伯父。这图书馆是他十二年前回国探亲时为县上先捐款后修建的,也是以他的姓名命名的。
2
为了修建这个图书馆,我和县上的两届领导,整整扯了十年皮。伯父走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及时向他汇报图书馆修建情况。他说会上决定我有代表捐款人督促过问工程进度、质量的权利和义务。图书馆建成之后,我可以做馆里一名看门人兼清扫工,伯父少年时代的老同学徐启之伯伯的孙女徐亚珍,可以做一名普通馆员。我们的工资都由伯父连同捐款一次交付。伯父让我做看门人兼清扫工,是因为我们李家在国内只剩下我这个独苗苗了,前几年劳动时又伤了两条腿,不能再干重活,生活上困难很大。伯父要徐亚珍做一名普通馆员,是因为他原想让徐启之伯伯做馆长,——徐伯伯在我们县是很有学养的人,但徐伯伯坚辞不肯。他说他已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多年,身体又不大好。他请县上考虑,能不能让他的孙女徐亚珍在图书馆建成后做个一般馆员。他说这丫头已从高中毕业了,再上学家里肯定供不起。伯父听了这些话,就在捐款中加了十二万元,说我和徐亚珍就算是他的雇员,这十二万元也许够我俩挣一辈子,不许我俩因工资为县上增加财政负担。
为建这个图书馆,伯父究竟为县上捐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外界人士有说一千零十二万的,有说两千零十二万的。十二万这数字我记得很准确,因为这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我们这工资,当然也由县财政局管着,图书馆建成后,我们正式上班后,和其他员工同样按规定逐月领取工资。
使我痛心的是,伯父为了照顾我这双受伤的腿,却苦了我这双受伤的腿。
我已说不清为了和两届县领导扯皮,我往返在我们村县之间,一瘸一拐跑了多少趟。从我们村到县城,往返八十多里。一趟八十多里,十趟八百多里,二十趟一千六百多里,中间还要翻山、趟河。我大约每年的每个季度,都要去一趟县城。这样计算,我每年奔波的里程大约是三百二十多里,十年就是三千二百多里,当然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差得远。但我记得有人说,古时从西安到兰州,共有十八马站,也就是一千八百多里。这样计算,也就是说,十年来我迈着一双受伤的腿,几乎等于从西安到兰州,或从兰州到西安,差不多是打了一个来回!
这十年中,值得记述的事很多,几天几夜也难说完。下边只挑重要的说说吧!
第一次对我印象极深。那是伯父回国探亲后的第二年。记得是个夏天的中午,我好不容易赶到县政府。孟县长刚刚开完会,我在会议室门口见到他,他身后跟着个年轻人,替他提着皮包,端着茶杯。我说,孟县长,我想问问那件事。孟县长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问我,你们村上没村长?乡上没乡长?区上没区长?什么大不了的事,跑到县上来找我?……哦,他已不认识我了!这也难怪,因为前年他和书记、统战部长、招商引资办主任、城建局局长陪同伯父参观我们县惟一的新农村时,我尽管紧紧地跟在伯父身后,但那天我却是穿着一身新干部服的,脚上也是蹬着一双新皮鞋的。而这天,我却一身农民打扮,脚上也是一双土布鞋;浑身上下还有包谷花,鞋上还有田里的泥土,县长自然不认识我了。咱算老几,不认识也罢,但他不该忘了伯父捐了那么多钱修建图书馆的事啊!
说起那身干部服,尤其是那双新皮鞋,我心里不由得又来气。
伯父回到县城的前一天,县里就有两个干部来我们村子。我们村叫李家寨。我正在家里起羊圈。来人将我从羊圈喊出来,问伯父的老宅子现在怎么样,我说早就墙倒房塌了。问我们李家的祖坟现在怎么样,我说学大寨时,祖坟早平掉了。接着他们便接我到县城,坐的是他们开来的小车。村里人还以为我犯了什么事。到了县城,听说伯父晚上在省城还要作场报告,明天一早才能回到县里。县领导要我住在县委招待所。晚上,一个干部抱着一身崭新的干部服,提着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要我立即换上。我将皮鞋放在床下,将干部服穿在身上试了试,长短肥瘦倒挺合适,只是衣领太硬,箝着脖子,使脖子转动不便。这干部一再叮咛我:明天一定将皮鞋穿上!我答应他:“穿上,一定穿上,咱也开开洋荤,耍耍阔气!”
第二日我一穿上那皮鞋,便觉得太大,脚在鞋窝里哐里哐啷的,一抬步就掉,一抬步就掉。去新农村参观时,我一直挺着脚掌走路。我的两条腿受过伤,脚掌一鼓劲,腿就抽筋;脚掌不鼓劲,皮鞋就掉。去新农村,来回都坐着小车,只在那村子转游了一周,我的脚面就磨出了水泡,脖颈也被新制服领箝得难受。
孟县长终于回想起伯父捐款建造图书馆的事,要我去和城建局长谈一谈。
城建局长强调了很多困难,主要是伯父当年主张要把图书馆建在文昌阁旧址。文昌阁是他少年时代的母校。文昌阁现在已没了什么古建筑,只有两棵古老的枫树。麻烦的是紧挨文昌阁有几家“钉子户”,其中就有赵书记和孟县长的私宅。这几户如何拆迁、重建和赔偿,包括旧县城如何改造,开了几次会,一直不能决断,修建图书馆的事,也就这么一直悬着、摆着、搁浅着。
我问伯父的捐款到位没有?城建局长说钱早到位了,只是“钉子户”问题无法解决,旧城改造规划做不出来。
我第二第三次进县,哪位领导也没找见,不知他们到哪儿开会去了,参观学习去了。第四次好不容易找到赵书记,赵书记自然也不认识我了,他甚至连我伯父的名字也忘了。我从衣袋里掏出徐伯伯请省城一位著名书法家题写的“李斐华图书馆”牌匾字幅让他看,他好像才想起这件犹如隔世的事。赵书记的健忘令我惊奇。我提醒他,伯父回乡那年,赵书记曾先天夜里问我伯父最喜欢吃什么?我说伯父出国前我还没有出生,连他的面也没见过,压根儿不知道他的饮食嗜好。赵书记当时还启发我:听没听爷爷奶奶说过什么?我这才想起爷爷奶奶曾说:伯父年轻时最喜欢吃浇汤烙面和石子馍;可是那时他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一次浇汤烙面,过端午节时才能吃一块石子馍。根据我提供的这点历史背景,那晚县委招待所才请了会摊烙面和会打石子馍的人,整整忙了一夜!赵书记那晚还一再叮咛我:明日见了伯父,绝不能说墙倒房塌和平了祖坟的事,并强调这关系重大!第二日伯父在招待宴会上几次说他几十年再没吃过这么好的饭了!我一直没说墙倒房塌和平掉祖坟的事,为国家顾全了大局……经我说出这些细节,赵书记这才从他杂乱的记忆库里,翻捡出这宗陈年老账。但他没有向我透露任何有关修建图书馆的信息。和孟县长相同,他也要我去问问城建局长。
这次,我没找见城建局长,局里的人说他到深圳参观去了,学习有关城建的经验去了。我想,云龙小县,只有东西两条街,早年间还有城楼的时候,东城楼的人喊话,西城楼就能听见;现在城内人口还不上万,参观就是参观,旅游就是旅游,学人家什么经验呢?
后来等我再去县里,赵书记和孟县长已经调离,新来的刘书记和张县长,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为伯父在国外既那么有钱又那么有名而吃惊。他们问我,你伯父捐了多少钱?我只能说出伯父为我和徐亚珍预付的工资——十二万元。刘书记和张县长听了都很泄气,异口同声说:“十二万?十二万能干什么呢?”我说十二万只是我和徐亚珍的工资,前边不知还有几百万,也许是八百万,九百万,或者整整一千万。他们这才睁大了眼,互相对视着,跟斗眼鸡似的。从他们的眼神我看得出,他们怀疑这笔钱到底干了什么?这笔钱现在到底在哪儿?他们好像也要对这笔钱打点什么主意!
刘书记和张县长的怀疑,也引起了我的怀疑。六年过去了,伯父的捐献到底干了什么?到底存放在哪儿?单利息恐怕也不是个小数字!但我该去问谁呢?谁又肯向我说明真象呢?
伯父最近来信要我给他寄一张图书馆照片。伯父说他年事已高,不可能再回国了;他只想看看照片!但六年过去了,图书馆还是镜花水月,我该到哪儿拍这么一张虚无缥缈的照片呢?
3
时间又过了两年,我又去了一趟县城。这次我没有找刘书记和张县长,我找了已经退休的前任统战部长。因为近几天,我想起了他在欢迎伯父的会上那段慷慨陈词:“我们的海外侨胞是热爱祖国的,情系家乡的,祖国的建设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关心!……我们同为炎黄子孙,共同的血流在我们体内,共同的血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伯父和县领导签订协议的会,我和徐伯伯没有参加。我在招待所休息室听到了统战部长这段感人的讲话。我一直认为他的话发自肺腑!
我向统战部长说,伯父向我要一张照片,但我不知道图书馆到底动不动工?什么时候才动工?县上既然接受了伯父的捐献,图书馆为什么总迟迟不动工呢?统战部长说,李斐华博士当年捐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振兴科技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他认为我们国家之所以还赶不上西方先进国家,主要在于明清以来,科技文化事业落后,近些年又使传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破坏!而当时的赵书记和孟县长,却一再强调县上亟需修一条公路,架一座桥梁,办一个或两个果汁厂。双方的目的不一致,各持己见,会虽然开得很热烈,接待周到,情感融洽,那只是怕捐献者把数字往下压。书记县长们知道,这数字在他心里藏着,给多给少,他的情绪、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和血压计上的水银柱一样,可以忽高忽低。因了以上缘故,李博士走后,捐款尽管如期到位,但领导人的心却凉了,——“竟然只资助建造一个图书馆!可见这博士也只是个书呆子。这时代,谁还需要读书呢?谁还需要做个蛀书虫呢?”思想意识的不同,便使事情搁置下来,一直拖到现在。那笔捐款我估计是没有人敢怎么、怎么的!……
前任统战部长最后说,最近听说,又开会讨论了一次,也许下半年就会动工,馆址的选定自然要尊重博士的意见,——未来的图书馆必须建在文昌阁旧址,那里有两棵老枫树,那里曾是李博士少年时代的母校。
前任统战部长要我下半年再来县城一次。他说那时你虽照不到一张新馆照片,起码也会照张工地施工照片。我说,伯父快八十岁了,只怕那时……
我说这话时,只觉得鼻根酸酸的。
到了下半年,我又来到县上。这次,我没找任何领导,只去了文昌阁旧址。伯父捐献的图书馆终于动工了,工人们正在处理地基。我见一位师傅手里拿着几张图纸,问他这建筑共是多少平米,他说是1150平米。我记得原商定的是2410平米,怎么要减少一大半呢?我问这建筑是几层,他说是两层。我记得原商定的是四层,捐款数字是按四层、2410平米核算的,还包括砌一圈围墙,盖几间生活用房,制作书橱、桌椅在内。按当时的核算,这些项目都完成了,还会结余二十多万元购书费。现在怎么会拦腰砍掉一半呢?是不是余下的,准备全部转为购书费呢?
我不会拍照,也没请人拍张工地施工照片。我只在这工地呆呆地站了好一阵,从内心深处祝我远在天涯的伯父,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好好地活着,耐心地等待我把图书馆照片,向他老人家寄去!
日将落时,我便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只觉得双腿很痛。回家时,我经过了我们县惟一的新农村。这新农村现在已不很新了。伯父那年返乡时,参观的就是这个村子。那天,伯父在这村子看见一个弯斜着的拴马桩,曾用手摸了摸那顶部的小狮子,说这可是个好物件,距今最少也有三百多年!在这村子西头,伯父还看见一根断裂了的铁旗杆,曾问徐伯伯,关于这铁旗杆有什么故事。徐伯伯说,相传这村子原为老子炼丹处,明嘉靖年建有老君庙,后焚于火。铁旗杆原是好好的,后来不知怎么断裂了(其实徐伯伯知道这铁旗杆是那年大炼钢铁时被砸断的,只是他当时头脑还算清醒,并没有如实地这么说)。伯父说,那这就是李游村了,距我们村是很近的。从县上到李游村,原是要经过我们李家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见到李家寨?当时陪同伯父的县领导,都佯装没有听见伯父这句话,我和徐伯伯也佯装没有听见伯父这句话,谁也没有回答他的提问,都作王顾左右而言他状。因为那天,他们舍近求远,是故意绕开了李家寨的。舍近求远的目的,我和徐伯伯心里很清楚。那天,徐伯伯也是由县上特地邀到县上陪同伯父的,因为伯父少年时代的同学,那时在云龙县,只剩下徐伯伯了。他俩自小就很要好,又是同年同月所生,几年间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同睡在一个被窝里,真是情同手足!那天,在那根被砸断的铁旗杆旁,伯父和徐伯伯共同照了一张相。在他们一起合影时,我见伯父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老人家那年整70岁,头上戴着顶浅灰色西洋帽,穿一身咖啡色西服,胸前垂着一条淡蓝领带,皮鞋是褐红的,擦得油光贼亮。徐伯伯也穿着由县上令其换过的干部服,他说他脚上长着鸡眼疮,那天没穿县上先天夜里给准备好的黑皮鞋。在他们两位老同学合影时,我觉得伯父比徐伯伯,最少也要年轻二十岁;一个满面蜡黄,色若死灰,一个红光满面,神色飞扬……
4
“李斐华图书馆”终于建成,总建筑面积只有1150平米,上下两层。但这时县上的消息灵通人士,却传出了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前任书记、县长和现任书记、县长,各贪污十五万元,前任城建局长和现任城建局长,各贪污八、九万元。另一种说法的数字,恰恰与前种说法相反。这两种说法也许后一种比较准确,因为前后两任城建局长,都被双规了,而前任书记却被调到省上,县长也被上调到了市里,都担任了更为重要的职务,现任书记和县长,官位也都稳如泰山,一点事没有。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只按数字做判断,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贪污数字的大小,并不能说明官场的潜规则!在官场,贪污数字大而平安无事者大有人在!而前任书记和县长,当时又是特殊的“钉子户”,县上在对他们的私宅拆迁补助方面,听说就花费了不小的一笔款子。
也许各种说法都有理。对这些说法,我这个平头百姓根本无法弄清楚。我只关心着建筑面积和工程质量,我只想在工程落成之日去做看门人和清扫工。这时徐伯伯己经去世,享年76岁。七十三、八十四,徐伯伯也算高寿了!因此我也盼望徐亚珍从这时起,就能做个普通馆员,因为伯父在捐款中,早就预付了我们的工资。
但这件事却出了令人预想不到的麻烦。
一天我为此事去找第三届领导。书记和县长都很诧异。他们说,人事的事全要县上定,而且县上已经做出了安排。我问县上是怎么安排的,他们说这事我无权过问。我说我有权过问,因为伯父在十多年前就预付了我和徐亚珍的工资,那工资就是那笔捐款整数后的最未两位数。新书记和新县长问我有何凭据,我说我的根据肯定在当时的会议记录或会上形成的什么文件里,而他们却一口否认当时有什么记录和文件。
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位已退休了的统战部长。我以为他是个会说实话的好人。
我将情况向他说明了。谁知他却说他当时主要负责接待,负责统战,对这些具体的、实质性问题,根本不清楚!
这个好人真也是个好好先生!
我又问,那你记得当时有什么文字材料吧?他说文字材料肯定有,但不知道如今掌握在谁手里!
我知道从这个老好人口中再也打问不出什么了,这好好先生既不愿做人证,又不愿向我提供任何线索,我只有回家了。
从这时起,我开始重新计算自己一瘸一拐地、限难地奔走在我们村县之间的新长征了,而且使自己家的几亩庄稼,一次耽误了雨前施肥,一次迟浇了几天水,使收成受到了很大损失。
一天,我突然想起在伯父回乡那两日,和伯父离乡后好些日,县广播电台曾就伯父捐资兴建图书馆的事,播送了好多篇新闻。记得有一篇将伯父的损款数字和图书馆的建筑面积,以及今后的辉煌前景,用高度赞扬的语气,讲得很具体,很清楚。
恰好我们村有个叫李纯火的年轻人,在县广播电台任台长。李纯火是我的远房侄子,是我伯父的孙子辈。他毕竟是文化人,对李爷爷在国外从事的事业以及在科研上的成就,比我知道得更多更详尽。他为我们李姓人家有李爷爷这样的人物而感到骄傲,他为我们全村全县有李斐华这样的博士而感到荣幸。我想通过他能够找到一些文字材料和数据。李纯火说凡以前广播过的重要稿件,按说都是应该存着的。他对此事很关心,答应为我认真查找。
李纯火为我带回了一份复印件,上面除了几项重要数字、伯父为我和徐亚珍预付的工资外,还有会上确认我有督促工程进度和检查质量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决定。我将这些记牢了,便去找新来的书记和县长。我说这些我虽没有保存着正式文件,但却有当时自己做的记录,还有当时收听广播时的录音。书记和县长见我说得有根有据,便不敢再唬我了,而是把一切都推在馆长身上。他们要我去和馆长商谈这些具体问题。
馆长是个中年人,他说馆里已满了近四十个编制。我说原定最多只有十人,一位馆长,一位采购,两位编目,两位借阅、管理员,两位财会员,一位门卫兼清扫工,共九人,现在为什么超过了四倍呢?馆长为难地让我看了看名单,原来这些人都是前两届和新来的书记、县长和其他部长、主任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4岁,还有正上小学、初中的学生。看了这个名单,我不禁笑出声来。馆长说,我愁死了,你还笑?近四十人只有五个人来上班,这两天我就打报告辞职!我说你辞了职,谁批我来上班呢?馆长说你是当年的会上定的,工资又是伯父预付了的,你只来上班就行,看谁敢来赶你!
我真的就上了班,而且捎话让徐亚珍也来上了班。
书库里没有多少图书。原决定工程结余的钱全部转为购书费。现在工程算是完结了,余下多少购书费呢?谁也不知道,好像连一分一文也没有,要不书库里为什么是空空的!现在几张书橱上放的书,全是些旧书。这些书是县城内外三位老先生捐献的。一位是个老中医,《本草纲目》《千金要方》等等,都是他捐的。一位老先生捐的多是我国近现代和外国小说。一位姓吕的老先生捐的书比较杂,有《四六法海》、《西昆酬唱》、《石林燕语》、《豆棚闲话》、《香销醒酒曲》……。这几张书橱都是用五合板和三合板钉的,摇一摇就会散架,其余几张却都空摆在库里。
果然没人来赶我。新来的书记和县长回避我,我却偏要找他们!
我问:“近四十人的编制都是哪些人?一个79岁的老太太能上班吗?一个4岁的孩子能上班吗?上中小学的,到底是上学呢,还是上班呢?工程花费了多少钱?结余了多少购书资金?”
他们向我只是笑。笑我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要他们严肃点,别笑。可他们还是笑。笑我的生伧愣倔。
但我却哭了。我说我对不起伯父!……我要向伯父写封信,要他把这些事告诉给中央!
5
我没有向伯父写信。我怕将伯父气死了,反落个忤逆,反落个不孝之子。
我想为伯父拍一张新落成的“李斐华图书馆”全景。李纯火会拍照,自己也有相机。他忙活了一上午,总没法选好角度。
只有省上的大书法家题写的“李斐华图书馆”牌匾最有水平,最有质量。李纯火说这六个大字,写得遒劲而有书卷气。他总想把这六个字完完整整纳入镜头,但无论如何却达不到目的。图书馆占地太狭小了,四面又围着一圈土墙。稍向后退便是土墙,走出土墙,镜头便被遮了。向西站,西边的老枫树正遮着“李斐华”三个字,却映出墙外的“牛肉拉面”四个字,连接起来便成了“图书馆牛肉拉面”。向东站,东边的老枫树正遮着“图书馆”三个字,却映出墙外的“羊肉泡馍”四个字,连接起来便成了“李斐华羊肉泡馍”。这并不怪这两棵老枫树。伯父对这两棵老枫树很有感情,怪只怪图书馆占地大少了,几乎没有院落!怪只怪图书楼盖得距这两棵老枫树太近了,枫树的枝叶几乎可以伸到二楼的窗户里去!李纯火蹲在楼下将镜头朝上取景,“李斐华”三个字便变成“木非化”三个字,好像李斐华搏士只剩下三颗细细长长而又光秃秃的头顶,从头部以下,不知被什么人齐齐地砍掉了!“这太不吉利,太不吉利!”李纯火心里想,口里却没说出一个字,只是没摁快门。
我气愤到极点,也悲伤到极点。伯父捐出一千万元,却连张照片也无法看见,我不知他老人家如果知道了我们今天拍照的事,将作何感想?有何感慨?
李纯火无法完成我交给他的任务,我无法完成伯父交给我的任务,我们李家子孙,只有惆怅,只有悲哀……
这时,我们馆内最辛劳、最勤苦的采购员冯谊,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回来了。我看见他的自行车后座两旁,重重地下垂着两捆旧书,大约有五十多册。冯谊气喘吁吁,满头的短发尖上,都亮着一颗颗汗珠。他骑着车子倏地一下从我身边驶过去。我只见他的上衣背部,被汗水浸湿了大大的一块。这被汗水浸透的一块,很像我们共和国的地图。我们可爱的采购员,他负驮着我们共和国的疆土,整年整月地奔驰在我们县内的四乡八镇,在各个大大小小的村堡,搜寻征集一些破旧图书。这些书里蕴藏着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但是他不知道,现在谁还要读他征集来的这些书?谁还会珍惜我们的传统文明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