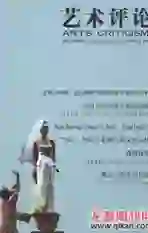舞台与现实的互动
2009-03-19高音
高 音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不由得把目光投向上个世纪风声水起的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无形中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座界碑,一种标杆。八十年代中期出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在他的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段:“现在正时兴回顾八十年代。至少,那时的文学确是常有新意,《上海文学》,李子云任执行副主编,他们发表的阿城的《棋王》,曾经多么轰动!……当然也时有争论。刘再复的主体精神论与性格二重论,引来了姚雪垠老作家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批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发表在《花城》上,她的骇世疾俗的有些说法和做法也令人反感。包括残雪的风格与高行健的小剧场剧作实验,说法各不一致。不一致,没有什么不好。然而整个的格局已经形成,文学正在开拓,精神生活正在日益活泼,希望与不安、矛盾与生机,尝试和误判都在发展。”[1]
舞台前史与现实认同
在进入“另一种解读”之前,先谈谈《天下第一楼》的舞台前史与现实认同。有必要提及一下1988年前后北京乃至整个全国的戏剧情状和动向,普列汉诺夫说过:“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他时代的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而且越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越强烈越明显。”[2]八十年代的戏剧创作始于话剧危机,但又在危机中显露生趣。有人曾总结说,新时期以来的十年话剧,是伴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在复兴与危机、反省与怀疑、困惑与惊喜中交替并进。在围绕“话剧十年”的讨论与反思中召开的“青艺第八届创作笔谈会”上,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指出,“形式上的创新值得鼓励,但它也有局限性,有难以为继的一面。要真正把话剧搞上去,还应有点更深的东西。用北京话来说,就是要有点干货。这个干货就是指对我们的时代,对我们的生活,要有深厚的积累,要有体验、思考和激情。艺术家应该把心踏下来,真正稳稳当当、扎扎实实地研究我们的生活,研究我们的艺术。好的作品往往都不是在那种大喊大叫中出现,而是在一种相对平静的情况下产生的。”[3]
1988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连上了两个大戏《太平湖》和《背碑人》,结果都不如人意。6月《天下第一楼》上演前,剧院让何冀平为剧场门前的演出预告写点什么。何冀平挥笔写下“桌前推杯换盏,盘中五味俱全。人道京师美馔,谁解苦辣酸甜。”这部承继老舍京味话剧醇厚意蕴的舞台剧,票房一直居高不下,使得曾经冷寂了近两年的首都剧坛陡然轰动热闹起来。时任《北京晚报》记者的过士行在当年6月13日的《北京晚报》上写道:“人艺再次成功地展示了她的现实主义戏剧的魅力,精致的布景和生活化的表演把观众领入一个舞台幻觉的世界。这样的戏剧演出样式,曾使无数观众为之倾倒。……剧中的堂头、掌柜、厨子,以及三教九流的食客个个形象鲜明,富有个性。精彩的台词,浓郁的京味儿,令人疑是老舍在与北京人艺重新合作。”剧协的老人李超挥笔《调寄〈唐多令〉》:《天下第一楼》,“台气象优。帏幕中,旧世重游。人艺风格尤展现,编导演,冠冕旒。商业靠良谋,孟实独善筹。也改革,矛盾不休。形象典型决造就,真实感,更堪讴。”评论家们也忙活起来,有叹这个剧“对于人生的历练;对于历史和世情的洞明以及语言运用的老到”[4];有肯定该剧对开放的公共空间的选用“为编导者提供了一个描摹时代风情、人生世态、历史变迁的极好机会”[5]。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祝肇年指出,《天下第一楼》能够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征服那么多观众,“就在于它占了一个‘真字。这是它最根本的强点。这里,一切精湛的技巧——写作的、导演的、表演的、舞美的,全都隐没在夺目牵魂的形象之中,返朴归真。这部戏是风俗画,但它展现的生活本身却含有哲理的内蕴深度,它给人以苦涩之感和宽广的思维空间……现实主义不是陈旧问题,对一些作家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画鬼容易画人难,《天下第一楼》受到赞扬,正说明它是现实主义解放的成果。”[6]
80年代中后期,在一些突破传统戏剧模式自觉探索实验的现代剧目锣鼓喧天粉墨登场之际,戏剧界就涌动着一股复归现实主义的暗流。其时,形式革新的话剧作品大多富有活力,但同时不可否认地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有论者抱怨戏剧创作在人学上的困顿,有论者指出创新话剧满台概念化的象征物,“形式上更新了,但编剧意识还极为陈旧。”呼吁该是作高层次回归的时候了。有论者认为,话剧十年,只不过是匆匆地快速浓缩了的“中体西用”。“中体西用”的实质是“旧体新用”,“戏剧理论和创作在根本的深层的总体观念层面上是旧的,在枝节的外显的技术的物质层面是新的。”[7]继《狗儿爷涅》《桑树坪纪事》之后,信守戏剧现实主义的人们再次抓住时机,借《天下第一楼》集体庆贺现实主义阵营的又一次胜利。时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于是之在一次采访中说:“现实主义虽不是文艺创作上的唯一道路,但却是一条康庄大道,何冀平创作《天下第一楼》,走的正是像老舍先生《茶馆》的路……”[8]作为80年代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年轻的编剧,何冀平在创作中的确努力吸取老舍先生刻画人物、截取场面、精到台词等写作技法。何冀平在这一年中戏同学为《天下第一楼》聚集的侃山会上说,“她想应该继承的是人艺36年来尽心致力于中国民族话剧的创造,富有诗情画意,洋溢着中国民族情调的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创造”[9]。难怪老剧人黄宗江写下如此感言:“人艺舞台上出现此剧,不少观众很自然地拿它和《茶馆》比。据说何冀平自己还总想着躲开《茶馆》,可是就没躲得开,这是由于一脉相传吧。这一脉相传是文字的也更是剧场艺术的。”[10]何冀平这个曾经赴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作为恢复高考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78级毕业生,1982年分配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6年后《天下第一楼》的成功演出使她声名雀起。相继获得了当年北京市编剧奖、1988——1989年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和1991年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大奖”。 1991年11月15日,当《天下第一楼》演出第300场之际,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做出了——《关于表彰和奖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天下第一楼〉的决定》。
《天下第一楼》借一家烤鸭店,聚集清末民初北京城里的各色人等,掌柜的、烤炉的、跑堂的、玩票的、跟包的、警察、妓女、宫里包哈局的执事、风水先生、总统府的侍卫,形象地勾勒出那个时代的一幅“清明上河图”。 1917年,前门外肉市福聚德烤鸭店老掌柜唐德源身体多病,两位少掌柜,一个迷上了梨园,一个热衷于练武,均无成就家业之心,祖传三代的产业危在旦夕。二掌柜王子西向老掌柜荐举同乡能人卢孟实,卢孟实临危受命。他眼光独到,志向远大,不忘父亲被辱气绝的遭遇,一心想摆脱“五子行”被人轻贱的处境。到任后他严明规矩,请来敬业的李小辫制衡居功自傲的罗大头,善待有一口绝活儿的跑堂常贵,请来食客“傍爷”做“高”。卢孟实苦干十年,扩大经营,借款起楼,扩大店面,增加多种经营,在他的提调下福聚德烤鸭店名噪京师,买卖兴隆。卢孟实春风得意,用多年的积蓄在老家置办房产,与胭脂巷的玉雏姑娘更是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然而,买卖兴隆的福聚德经不起两位不务正业的少掌柜无止境的挥霍、拆台,迫使卢孟实带着满腹的怨气、憋闷,一肚子未实现的抱负离开了福聚德,心高气盛的卢孟实最终也难逃一个人干、八个人拆的酸苦结局。卢孟实临走留下对联一副: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横批:没有不散的宴席。在创作的过程中,何冀平偶然间发现了这副对联,立刻被它吸引,把它用到了几易其稿的结尾上。“首先是‘楼,福聚德从没有楼到盖起楼到这座楼金碧辉煌,突出的是以楼象征的事业。‘危,有高和危的意思,正符合剧中兴败的故事。更打动我的是‘谁是主人谁是客?戏中主人公卢孟实、常贵……自以为是事业的主人,其实‘梦里不知身是客,能体现此种人生况味的,何止一个呕心沥血壮志难酬的卢孟实、一个含泪带笑一辈子终于含悲而死的常贵、一个看透世事愤世嫉俗的修鼎新?这副对联突破表意,直取人生,历经沧桑的人可为感喟,不甘于此之人可做呐喊,人生的苍凉、命运的拨弄,尽在一个问号之中。”[11]
在导演夏淳眼中,《天下第一楼》是一个有人物、有情节、有意思、耐人寻味的好本子。他一向认为观众到剧场是来看演员,是来看演员的表演、看演员创造的人物的,观众最关心的是舞台上人物的命运。编剧何冀平要为“五子行”众人立传的意图也深得他心。问题是编剧的良苦用心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控制,就会因精力分散陷入铺陈场面人物轻重着墨不均的误区。何冀平笔下的堂头常贵一辈子兢兢业业,善良宽厚,在人面前陪笑脸,但骨子里争强好胜,是个打掉牙往肚子里咽的主儿。为了养家,他早已习惯这种见人说漂亮话,低三下四被人轻贱的行当。他表面麻木,会说好听话,实质心里敏感,在善解人意的背后有一颗待人真诚容易受伤的心。常贵的扮演者表演艺术家林连昆更是为这个角色找到了贴切鲜活的行动线索,“他能说会道,有一张能把死鸭子说活的嘴,但他绝不是油嘴滑舌,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保住他赖以生存的买卖,必须委曲求全,但他又绝不是卑躬屈膝的势力小人。为保存自己生存的环境,上不能得罪东家,下不能得罪他手下的伙计;既不能亏待顾客,又不能让买卖吃亏,所以他必须上下支应,左右逢源,可他绝不是两面三刀居心叵测的刁钻之徒。”[12]明眼的夏淳导演看出作者对常贵这个人物赋予了极大的同情和钟爱,“甚至于可以说作者就是为常贵写传的,而且这个人物也确实写得很丰满,是一个跃然纸上的活的人物形象。但常贵依然担负不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他左右不了‘福聚德烤鸭店的兴衰;他也不能成为主宰局势变化的动力。而作者在剧中确实写了这样一个人物,就是卢孟实,但由于作者对常贵的偏爱,没有把精力花在卢孟实身上,这个人物的确是处在矛盾尖端的地位,可在别人嘴里介绍得多,他个人行动少,形象显单薄,不大立得起来。这个人物写不好,将会有损于全剧,影响这个戏的评价;假若这个人物写好了,全剧的脊梁骨就树立起来了,而且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13]夏淳以为,对剧本的修改是导演面临舞台呈现首先要完成的工作。其中有个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戏中谁是主要的人物?借这段导演阐述,稍加变通,从舞台主人公卢孟实的最终明确,势必引出下文要涉及的内容。
改革年代的现实思考
80年代的理论家们常常活学活用马克思经典著作。他们总是能够从中找到应和现实并指导现实的哲学基础。活跃在80年代文艺理论界的顾骧对《天下第一楼》的评论就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说:“卢孟实是戏的脊梁骨,是全戏的中心人物。他有着振兴事业的开拓精神,也有着与风尘知己遇合的儿女私情;有着对老堂倌常贵不幸的善良同情,也有着与同行竞争的狠辣与经商的奸诈。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一种20年代新兴商人文化心态的新芽。他为‘福聚德殚精竭虑,事事操劳,所为何来?是出于受老掌柜之托,士为知已者死?是为了泄生父迫凌辱身亡之仇绪?是为了自己发财政富?都是又都不全是。我们发现在这个人物身上还有潜藏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称作人的本性,追求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因子。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14]该剧另一位导演顾威在为角色确立的人物小传对卢孟实确有如下的文字描画:“有抱负,机敏,对人对事态度情绪转换极快,拿得起放得下。纵横捭阖,大开大合,收放自如。不要去演改革家、企业家,他是一个为实现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显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用足、耍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计谋手腕直至阴谋诡计者。行行出状元,他要做他这一行的状元。”看来个人奋斗和实现自我是导演首先要赋予这个人物行动的“最高任务”。第三幕最后20分钟常贵气绝倒下引出了全剧的高潮,舞台上卢孟实和唐家两兄弟的冲突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唐茂昌:卢掌柜,你打算怎么打发常贵?
卢孟实:有病治病,人死好好发送。
唐茂盛:你对伙计倒不错,可你用的都是“福聚德”的钱。
卢孟实:我当掌柜的,不在伙计们身上打主意。
唐茂盛:那你就在我们身上打主意!
卢孟实:(不示弱)这话什么意思?
唐茂盛:“福聚德”日进百金,这么多钱都到哪里去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唐茂昌:卢掌柜,你受先父之托,你可得对得起他老人家。
卢孟实:卢孟实问心无愧。
唐茂盛:你说“福聚德”是你的买卖,这大楼的事都得你做主,有这事没有?
卢孟实:(平静地)有。
唐茂盛:这儿的钱、账、买卖一概不许我们过问,这话你说过没有?
卢孟实:说过。
唐茂盛:凡事不问我们的意见,你一个人拿主意,这事你干过没有?
卢孟实:不错,全是这么干的。
唐茂盛: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哪?
卢孟实:我看你们兄弟不是经营买卖的人,我怕你们耽误了祖上留下的这份产业。
唐茂盛:说得好听,耽误不耽误,你干吗操这么大的心?
卢孟实:我愿意操心。这楼是我看着起的,“福聚德”的名声是我干出来的,店规是我定的,这些人都是我一手调理的。一个算盘珠子、一根草棍都有我的心血,我不能糟蹋了它们!
唐茂昌:卢掌柜,话是这么说,可你别忘了,这份买卖他姓唐!甭管到什么时候,掌柜的也是我们,这“福聚德”我们要收回来了。
……
当时扮演唐茂昌的青年演员杨立新(目前是复排《天下第一楼》卢孟实的扮演者)为角色准备做了扎实的功课。他写道:“1917年前后,正是中国人民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与封建皇权复辟势力及封建割据反复较量的时刻。作者把‘福聚德的起落兴衰、几易其主放在这样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实际上是写了一场封建资本经营方式与萌芽状态的新生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卢孟实和两位少爷的斗争,无疑是这个戏很重要的线索之一。”[15]这段文字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被当年众声喧哗“民族美食文化”、“民俗传奇”、“民族文化深层心理”所遮蔽的写实戏剧真实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还有一篇短文,全然背离当年众口一词的潮流。作者是活跃于新时期戏剧评论的林克欢。林文的尖锐在于他不人云亦云,他从戏的结构入手,清醒地辨识出《天下第一楼》与《茶馆》的差距和异同。下面引用林文的一段论述是想借历史的文字说明这个戏真正的脉络:“《天下第一楼》叙述的是清末民初北京一家烤鸭店兴衰聚散的故事。全部剧情紧扣在一个人物——‘福聚德掌柜卢孟实身上。从他临危受命,用空城计逼退债主,在恭顺谦卑的外表下架空东家,到踌躇满志时被辞退……全店安危系于一身。”,“《天》剧登场人物不少,有达官显贵、帮闲食客、商贾、妓女、警察、痞子、厨师、堂倌、学徒、跟包的、讨债的……但各色人等的穿插,主要是为了烘托卢孟实活动的场景气氛;掌炉与灶头派系的争斗,罗大头的撂挑子与跪地叩谢,也是为了突出卢孟实的恩威并用与江湖义气。各色人等,只是主要人物的陪衬;各种短景,只是情节主线的点缀。开放的舞台空间是为锁闭的情节结构服务的。”[16]也就是说,附加在《天下第一楼》上的赞誉诸如对美食文化的开掘,民族心态的思考等等实际上是罩在山间的云雾,拨开它,我们就能够看出山的龙骨。
在80年代,很多作家都有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这种责任承担,使有关‘历史清算和‘历史记忆的书写,几乎是八十年代作家或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这不仅是题材意义上的,而且是创作视阈、精神意向上的。”[17]这里有必要提及经历沧桑的老作家萧乾先生在看过《天下第一楼》后写的一篇感想。《天下第一楼》被萧乾誉为“警世寓言剧”,“把个烤鸭店写成了一个独立的天地。这里矛盾丛生,有奉承拍马,有使坏穿小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煞是好看。不妨说,这出戏解剖了一只麻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的缩影。”萧文说,《天下第一楼》“没有影射现实的痕迹,然而看时,尤其看后,却令人影影绰绰地联想一些现实生活的事物。”[18]看来在老人轻松随和的文字背后是有话要说的。曹禺早在萧乾之前就感言,干事业的个人命运是悲惨的。“干了一辈子却落得如此下场,这个人物在前面一定要让人同情后面才能动人,他最后的走,不是因为没办法,而是伤透了心。”[19]从当时发表出来的文字中,我们不难找到一些感受到了剧情之外深意的蛛丝马迹。邹霆说,“戏中卢孟实善于经营,这个人物具有一种善于思考的开明民主的改革意识。在今天的开放改革当中,许多立志改革的创业者们,大概也常常会遇到像卢孟实那样的阻力。”[20]顾骧说,“这出戏的作者,用改革时代的眼光,艺术地处理积淀在历史中,具有某种超越时空的稳定性与普遍性的民族文化心态(优点与惰性),引发观众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从而使作品传达出对于时代精神的积极呼应。”林涵表的文字少有艺术的花招,是一篇难得的有社会学价值的剧评。他写道:“我们今天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新时代,我们今日的改革家,回过头来去看看卢孟实在‘福聚德那段的历程际遇,难道不会深感这是‘一钵人生五味羹,从历史的镜子里寻找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吗?品味《天下第一楼》,其价值恐不仅仅在于它能以‘一丝苦味来使我们借鉴于历史,我甚至想到,唐家那两位少爷‘吃祖宗的那样的人物自然也早已作为古人,拿着鸭票子到‘福聚德耍无赖的皇室渣滓克五之流,也早应进入历史陈列馆充当小丑,然而,他们的阴魂难道全然湮灭?阻挡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的大潮的旧思想和旧恶习难道也全然退出历史舞台?我觉得作者何冀平似乎隐约地向观众点示了这些值得思考的课题。”“在今日之改革和开放中,大量涌现的改革家自不待言,但比唐家大少爷、二少爷‘吃祖宗吃得更冠冕堂皇的某些腐蚀势力,依然是祸害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蛀虫。还有比克五还克五的无耻之徒,更要我们费劲正着身子或侧着身子去应付的。”[21]
从1985年3月何冀平向剧院交出初稿开始,《天下第一楼》写了三年,作品的风格也随之明朗,何冀平说:“中国烹饪三字诀:一火、二调、三新。大师傅面前提着酸、甜、苦、辣五味佐料。他东舀一点,西配一点,凭着灵性和经验配伍烹制,做成一道道全新的菜肴。中国菜的做法,来自中国民族的美学观念,来自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古时候称宰相为鼎辅,意思就是会调和五味的厨师,唐时有诗赞相国,盐梅金鼎美调和。突然间,我感悟点什么:盘中五味原来来自人生五味,我从堂、柜、厨中走出来,从为五子行不平的义愤,升华为对人生的感叹。人物出现了新的意蕴,‘福聚德的兴衰故事里流淌出一股潜流。”[22]《天下第一楼》剧中的明眼人读书人修鼎新对于周围人物之间的关系和命运有一番生动的描述——掌柜的也是个掌勺的,你我就是他的“佐料”。你是咸的,我是苦的,罗大头是辣的,常贵是酸的。福聚德是他的炒勺。我看他到底能做出个什么菜来……作为《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何冀平说她要“按照调和五味,熔于一炉的方法,做一味酸、甜、苦、辣俱全的中国菜。”
在改革的年代,剧作家敏感于时代的冲击,时代的脉搏不可能不在其心中跳动。说《天下第一楼》的舞台从侧面反映了改革这一当时最富活力的现实,这绝不是牵强附会。下文引述的这段多年后的访谈更是从旁印证了这一结论。提问者对何冀平说,在看粤语版的《天下第一楼》时,心里突然一动,觉得她写的几个戏里隐隐约约贯穿着一个意念。比如《德龄与慈禧》,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贵族公主到最后突然冒犯龙颜,用一种几乎“文死谏”的方式,向慈禧呈上张之洞的奏折,完成了戏的高潮,而支撑她行为的内在冲动,是“改革”这两个字。还有《明月何曾是两乡》里,那个北京男孩不用说了,口口声声要‘改变,而那个香港女孩也是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用改革去提高竞争力。这样的自觉意识在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见的。联想到她在大陆时写的《天下第一楼》,虽说是说一家饭店的兴衰,实际是写人的命运。那个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卢孟实是一个“改革家”,在内部与外部的夹击下,以悲剧结尾。 何冀平对提问者的回答是:“你说的那种‘改革的意念,似乎确实在我的许多剧作里存在。”“我比较喜欢逆境中生存的人物”,所谓“改革就是从逆境中走出一条路来,我觉得这样的人物才值得称颂。”[23]有当代文学史的论者把1985年视为改革文学的拐点,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然而“对社会改革的敏感和表现已经融入了作家们一般人生观念和艺术想象之中……”[24]
卢孟实是顺应时代浮出水面的地地道道的商人,更是一个平等待人锐意改革的新人,一边标榜信义,一边敢冒风险,会笼络人,更不怕得罪人,他千方百计要自主权,不断创造买卖兴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精明能干,志向远大,要成就一世的功德,“给天下人留下一个福聚德”。这确是个有着现代意识,追求个人实现的改革家。简直就有与当代改革家相近的气质和际遇。与守规矩埋头做事的常贵不同,他是个弄潮儿,一个敢于立规矩破规矩的人物,一个新旧道德集于一身的矛盾人物。浸透着等级观念的道德准则和个人发展的物质要求在他身上发生着尖锐的冲突。常贵的所作所为都在情理之中,他不同,他的行为不能自圆其说。“义”和“利”的关系一直纠缠在这个中兴“福聚德”功臣的戏剧行动中。这一点作者捕捉到了,但写得虚与委蛇,含含糊糊。对卢孟实锐意改革的动作也处理得简单潦草,流于平庸。当时就有论者指出:“卢孟实掌柜后,十年再振雄姿。是经营有方。适应了社会潮流。不能只靠借钱盖楼、赊帐进贷摆空架子。辛亥后宅门衰落,商贾勃发。饭馆集中于前三门。正由于这里是商业繁华区,各商号送往迎来要请客,饭局频连。饭馆的主顾也变为商人为主。敏锐的卢孟实应看到,至少他特请‘高的修二爷应帮他看到,使经营对象有所转移。这是‘福聚德再起的关键。剧本未能把握住此点。卢用修,识才未能展才,反成借老怜贫;修仅谈吃经、祭烤鸭、未达‘高之效。修之苍白、使卢之形象受损。”[25]
80年代的现实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改革的幅度、深度、烈度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舞台与现实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使卢孟实这个顺应时代锐意改革的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有不可辩驳的现实意义。舞台上的人生对应着当下的现实,我们也许可以从舞台上的《天下第一楼》,洞见到超越个人命运的社会的深刻变革。站在今天的高度回头去看那段历史的舞台纪录,可以说,《天下第一楼》确实是一部改革年代的现实思考。
用作家自己的话讲,“起初是生活,再提高到文化,再从文化升华到治国,最后归结到人生的苍凉,这个戏的成功就是从最底层写起,一步一步起高楼……”[26]何冀平中戏的同班同学杨健,《桑树坪纪事》的编剧之一就曾从“楼”与“天下”的关系来看该剧的深意和问题。“《天下第一楼》写的是楼,其实也包含了天下。几个人物都有可挖掘的内涵,代表了广阔的社会背景。问题在于楼与天下的关系结合得还不够精密。两层皮还没有粘到一起。”[27]
注释
[1]王蒙:《大块文章》,王蒙自传第二部 第178页花城出版社2007。
[2]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1页。
[3]王蒙:《简谈话剧问题》,《戏剧报》1986年第10期。
[4]何西来:《惊奇与回味——话剧〈天下第一楼〉观后随想》,《光明日报》1988年7月1日。
[5]林克欢:《重复不是创造》,《人民日报》1988年8月9日。
[6]祝肇年:《死蛟龙不如活老鼠》,《新剧本》1988年第5期。
[7]马也:《中体西用话剧十年》,《剧作家》1987年第6期。
[8] 《重振雄风——北京人艺六人谈〈天下第一楼〉》,1988年8月13日《光明日报》。
[9] 《天下第一楼辩——中戏老同学侃大山记》,《戏剧报》1988年第11期。
[10]黄宗江:《危楼风月录》,《人民日报》1988年8月9日。
[11]何冀平:《〈天下第一楼〉写作札记》,《戏剧报》1988年第9期。
[12]林连昆:《站碎方砖 靠倒明柱》,《〈天下第一楼〉的舞台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3]夏淳:《〈天下第一楼〉导演总结》,《〈天下第一楼〉的舞台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4]顾骧:《舒影横斜 暗香浮动——我看话剧〈天下第一楼〉》,《文汇报》1988年7月27日。
[15]杨立新:《初识大少爷》,《〈天下第一楼〉的舞台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16]林克欢:《重复不是创造》,《人民日报》1988年8月9日。
[17]洪子诚:《八十年代文学概况》,《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8]萧乾:《京味十足的风俗画》,《人民日报》1988年8月9日。
[19]《没有不散的宴席——曹禺谈〈天下第一楼〉》,《人艺之友报》1988年5月。
[20]《一出注入当代人思维的京味戏——话剧〈天下第一楼〉座谈纪实》,《文艺界通讯》1988年第8期。
[21]林涵表:《今晚报》1990年2月6日。
[22]何冀平:《〈天下第一楼〉写作札记》,《戏剧报》1988年第9期。
[23]何冀平:《我一直带着笑脸去看》,《东方》2001年第11期。
[24]《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第2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5]胡金兆:《为〈天下第一楼〉求疵》,《戏剧报》1988年第10期。
[26]何冀平:《我一直带着笑脸去看》,《东方》2001年第11期。
[27]《天下第一楼辩——中戏老同学侃大山记》,《戏剧报》1988年第11期。
高音: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