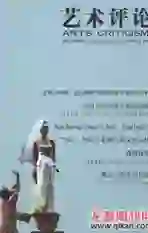数字化技术、景观与中国大片: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2009-03-19秦喜清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标志着中国商业大片时代的来临。该部影片投资数千万美元,首开中国大制作之先河,引领中国电影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此后,商业大片不断问世,从《天地英雄》(何平,2003)、《十面埋伏》(张艺谋,2004)、《无极》(陈凯歌,2005)、《夜宴》(冯小刚,2006)、《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2006)以至《集结号》(冯小刚,2007)。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导演拍摄的《七剑》(2005)、《神话》(2005)、《霍元甲》(2006)、《墨攻》(2006)、《投名状》(2007)、《赤壁》(2008)以及美中合拍片《功夫之王》(2008),推波助澜,衍生为一股华语电影的古装-武打片潮流。
我们知道,技术从来都是电影艺术的一部分。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电影对技术的依赖程度最深。默片时期的叠印、溶接、倒摄法等技术手段丰富了电影的基本语汇,胶片携载声音技术使电影进入有声片时代,特艺色(technicolor)和伊斯曼彩色胶片技术的出现,使电影转入缤纷的色彩世界,宽银幕技术(cinemascope)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推广普及,极大提高了观感的愉悦,也成为影院重新捕获观众的法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四声道光学立体声格式,给视觉愉悦增加了更加丰富的听觉享受。不过,与以往的技术革新相比,数字化技术带给电影却是一次更加绚烂的审美飞跃。为这个飞跃提供跳板的是各种数字软件的开发与使用。CG场景,VR技术,Maya, Fusion, Motor 和PF track,借助于这些电脑软件的帮助,人们在拍摄素材上进行二度创作,把素材转化为奇诡眩目的视觉景观。矫健潇洒的武打动作、宏伟浩大的战争场面、超乎想像的细节再现,都是经过特效软件的加工、润色、渲染才得以完成。电影符号学家麦兹曾把电影称作“想像的能指”,数字化技术使这个“想像的能指”更加虚拟化,这是因为,当传统电影用胶片记录现实对象时,虽然影像本身是二维的幻像,但影像的所指尚有现实基础,但数字化时代的电影,影像的所指有可能是纯粹的虚构物——漫天飞舞的矢石、武士手中的长矛、排山倒海般的人流都只是数字幻化的结果。数字化技术给想像插上了翅膀,为人类想像的表达提供了更宽广的可能性。在未来的电影里,等待我们的将是无限伸展的虚拟世界。
对制作者而言,数字化技术拓展了想像的空间,对观众而言,数字化技术则意味着视听新体验,感觉新世界。在电影的默片时期,急速行驶的火车、摩托车、汽车都曾成为重要的电影元素,提供惊险刺激的情节和场面,欧洲先锋派艺术部分地也回应的是西方声、光、电技术所带来的感官冲击。同样,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导致的也是“感觉反应范围”(米莲姆·汉森语)的扩张,观影感受的强化。
按照西方精神分析理论的说法,阉割焦虑直接导致“否认”心理机制的形成,当婴儿看到母亲的身体时,他看到了两性的差异,但为了避免这一差异给他造成的创伤感,婴儿会极力否认这一差异的存在,他会说“我知道,但是……”,依靠这种“否认”心理机制达到“否认”差异,消除内心焦虑感的目的。根据西方现代电影理论的观点,观众观影快感的基础也基于这个“否认”机制,它保证观众在观看虚假的、二维影像的同时, “否认”这种虚假性,从而进入到影像的真实性逻辑当中。“我知道(屏幕上的影像是假的), 但是(我还是承认它们是真实的)……”。经过数字化处理的大片,加重了影像的虚拟特性,从假到真之间的游走距离加大了,这意味着“否认”机制需要发挥更大的效力。当人们蜂拥进入影院,深陷在一片幽暗之中时,他们等待的是在虚拟影像中体验到真实性的魅力,虚拟程度越高,对其真实性的渴望也越强,商业大片的吸引力正在于这个从假到真的转化。因此,尽管商业大片一直受到文化批评的诟病,但虚拟影像的观影快感却一直诱惑、刺激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
同样,物恋也是消除阉割焦虑的一种途径。电影作为一种技术,其魅力正是来自人们对物的迷恋。正像麦兹所说的那样,电影的机器设备正是物恋的所在,爱电影的最好标志就是对电影设备和技术的兴趣。影迷、发烧友所痴迷正是影像本身以及创造这些影像的技术手段。
观影者受到景观的迷惑,同时更受到景观背后“电影机器”的诱惑,它所触动的是观众内心对物的深度迷恋。
有趣的是,《终结者》系列、《骇客帝国》系列以及《侏罗纪公园》之类的美国好莱坞大片经常把数字化景观表现(从人物的变形到巨大的场景描写)与未来和远古时空联系在一起,在奇幻的想像表达中展现技术蕴含的可能性,在大跨度的时空跳跃中表达西方的“科学幻想”。与此不同,中国商业大片,除少数当代题材(《集结号》)之外,几乎全部是历史、武侠、神话题材,古装、宫廷、义士、侠客、神话世界、刀光剑影、飞跃腾挪,其中所寄托的“人文幻想”(李零),成为数字技术呈现的对象。换句话说,数字化技术引发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像重写,因此,中国商业大片面临着一个双重的任务,在影像层面,它们需要通过数字化景观提供物恋满足,在文化层面,它们需要面对传统叙事,让观众在影像中重温代代相传的历史文化记忆。丈八长矛、青龙偃月刀、赤兔马、草船借箭、孔明借东风、曹营水寨,以及大大小小的各色人物,正是这些传奇般的传统文化符号,催促着人们涌入影院的脚步,累积起《赤壁》的高票房。
毋庸置疑,数字化技术与传统题材的融合改变了中国当代电影的外观,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假借现代技术不断更新与延续提供了可能性。就像上世纪20年代所发生过的情形一样,当时叠印、倒摄法等技术的引入刺激了中国第一轮古装——神怪——武侠片热,传统中国文化元素大规模融入电影这个现代娱乐形式当中,完成了现代与传统的首度融合。现在,中国商业大片再一次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力量吸纳、消化电影技术的换代升级,由此带来现代与传统的再一次牵手。不过,从中国大片目前的状况来看,数字化技术主要集中运用于宏大场面(如古代的战争场面)和技巧性的动作场面(如武打的编排)上,很少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较深层次的表达。事实上,从《英雄》到《赤壁》,中国商业大片一直在非议声中前行,其根源也正在于文化表达上的欠缺。显然,深谙“历史理性”、拥有丰富历史记忆的中国观众,不会止步于视觉景观提供的观影快感,他们在满足视觉奇观的同时,也渴望借助于丰满的人物、合理的情节和富于历史韵味的台词设计,重温自己民族的往昔。从评者的非议声中,我们不难感觉到,数字化技术与中国传统叙事的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相加,其中涉及到中西文化交融时一再出现的“体”“用”问题,体现西方技术理性的数字化景观与传统中国传统观念和价值,两者谁为“体”,谁为“用”,将决定电影创作的重心所在。显然,理想的中国商业大片,应该是以技术为“器”,文化表达为“道”,让前者臣服于后者,为后者服务,而不是让中国传统文化沦为数字化技术的展示平台或窗口。古装影片《画皮》(2008)中有狐仙撕掉面皮的场景,从制作手法上看,它直接搬用了好莱坞影片中常见的人体变形的手法,虽然产生了一定的视觉效果,但却没有围绕狐仙的特征进行构思和设计,因此,整个段落缺乏表现力,也没有足够的中国意味。因此,如何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来运用数字化虚拟技术,或者说,如何把后者吸纳、消化到中国叙事当中,这的确是中国商业大片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唯有此,中国大片才能做到绚烂与厚重并存,达到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
秦喜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
责任编辑:傅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