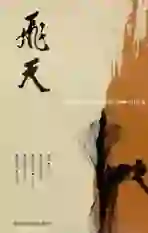电影音乐知遇《乐记》
2009-03-15廖旋
廖 旋
探究音乐的美学意义对于在当下的我们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净化我们的心灵,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美学思想家,他们的美学思想各有千秋,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在当下,经典的艺术美学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完美结合,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艺术经典。
《乐记》是我国最早的音乐美学理论专著。他所蕴含的音乐美学思想闪耀着华夏祖先的文明和智慧,其朴素辩证的音乐美学理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在构建新的音乐美学体系的同时,对音乐表演艺术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些研究以新的观念和视角,为音乐表演理论建设填充了新的内容,并为音乐美育功能的发展开拓了新的思路。而这其中,电影音乐就其独特的构成元素,表现形式,以及在对电影内容,情感和主题表达上的功能,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和电影音乐美学思想的联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电影艺术家在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向观众传播传承至今的“中和”思想。
《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是“礼乐”思想,因此,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作用归结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和”字,“乐和民性”、“乐者天地之和也”等等,从个人意志天下国家,从天下国家以至整个宇宙,音乐都能起到“和”的作用。首先从个人来看,“乐和民性”、“乐者孰和”、“君子反情以和其志”等等,都是说通过音乐能够使人陶冶性情,志气和顺。正因为这样,《乐记》主张“致乐以治心”。
音乐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当音乐和电影相结合时,观众对于音乐就不再是听之而识之,更多的时候会因导演的安排而陷于影片的情节中。观众用一颗非自由的心去欣赏影片,才能和影片创作者达到共识。《卧虎藏龙》的导演李安,是一个有很高文化造诣的艺术创作者,在李安的艺术世界中,“中和”之美无处不在,李安在其艺术作品中一直在寻找和谐之美。影片中的背景音乐也正服务于李安“和”的思想。《乐记》所说,礼乐可以提高人们内心的修养,平易、正直、慈爱、善良的心就会油然而生。在激荡起伏的背景音乐中,观众并没有感到刀光剑影的残酷,也没有感受到世态炎凉的冷酷,更多的是体会到男女主人公最求幸福的执着,美好和谐。甚至是在悲情落泪时,心中也无怒气,这也同样应验了《乐记》中所说,“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如果每一位观众在观影后,都能得以内心的平和,其音乐美育功能中最重要的“和谐”功能才算的上是功不可莫。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中而英华发外,为乐不可以为伪”,这就是说,德行修养是重要的,掌握技艺是次要的。只有“和顺积中”,才能“英华外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音乐,工作是一种关系到人的灵魂的工作,因此只有我们的灵魂高尚,才能够去打动旁人的心。弄虚作假,在音乐创作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其次,从国家社会来说,音乐的作用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是“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纳言之,《乐记》极力把音乐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是因为声音和人的感情是一致的,因此,通过音乐的声音,就可能了解到人民的感情。反之,人民的感情则是与国家的政治情况相联系的,通过音乐的声音又可以了解国家的政治情况。
在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中,人性论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中,感情不能悖逆理性的统治,个人不能超越社会的规范。《乐记》中的美学思想承认人的感情,而且认为音乐等艺术是“人情之所不能免”,音乐的本质就在于表现感情。但是儒家不仅是感性主义者,它还同时是理性主义者,它要把感情纳入理性的规范,把个人纳入社会的规范,从而把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纳入礼的规范。正因为这样,《乐记》所提倡的“礼乐”思想,就是人性论的核心观点。
《乐记》把人性看做人的自然素质和情欲,既肯定“欲”的存在,又要求“欲”的满足必须符合“礼”的规定,认为世间人的欲望是相同的,强调后天的教化对人重要性。“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礼乐表现感情,不是满足人的欲望,而是要“反人道之正”,使之符合人情天理。只有处理好情与理得关系,才能能够“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乐记》对人性的认识还体现在“审声”、“审音”、“审乐”的美育过程中,实现“乐者乐也”的美感,必须要有“欲”和“道”,“情”和“义”,即体验和领会“德育”中的内涵,达到情绪快适和理智愉悦。
在影片《英雄》中,作曲家谭盾依稀过去华丽反复的古典拉丁式音乐风格,以三段式主题音乐,配以清新的吉他和弦及提琴协奏,筑起了一个与刀光血影与世隔绝的,与大漠自然风光、永恒的爱情主题相辉映的、纯净的音乐世界,收敛起浓烈的情绪,以轻柔的音调来渲染男女主人公细腻的内心,在行云流水的乐声中,他们相遇相爱、告别、惦念、重聚、超越生死。影片是在优美的大自然中表现人物角色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既有缠绵的爱情,也有武林的快意恩仇,因此,影片的主题音乐由二胡主奏,乐队只是在主题旋律后面做背景衬垫。音乐荡气回肠、催人泪下、极具感染力,主旋律中一声声的呼唤,是超越任何人间界限的对爱人的呼唤,有力的诠释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执着。至此,《乐记》把人性看做人的自然素质和情欲,这一观点得意应证。“民有血气心之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观众在观影中,能否感受到荒凉的大漠,闷郁的竹林,其中一重要的介质便是片中撞击心灵的主题音乐。在第二段主题音乐中,谭盾用闷郁的表达,诠释了主人公爱情的无奈,这也符合了“中和”之道中“抑而合”的原则,如同《乐记》认为,人的欲望是相同的,节人欲但非排斥人的情欲。如果影片没有配以此音乐,想必观众很难体会其中爱所欲之,但非畅之的纠结感。
从古希腊的罗马大道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当我们畅游于历史长河中时,我们究竟触碰了哪些“美”,我们又是否坚定地认为“美”就在身旁,且从未离去。想必,这不是我一人对“美”的困惑。作为当代艺术创作者,我们能够也必须对前人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促使我们引导大众对“美”进行探究,丰富民众对“美”的发现与认识,从而达到以“美”净化心灵的目的,为和谐我们的社会而服务。
《乐记》提出的音乐的社会功能:“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声音与人的感情是一致的,因此,通过音乐的声音,就可能了解到人民的感情。电影中的各类音乐,无时无刻不在吐露着对生活,对美好的期盼在电影中尽显的淋漓尽致,这不得不使我联想当今我国政府高度提倡的和谐社会。电影音乐中的“治世之音”可以净化观影者的心灵,从而和谐社会这一重要原因。
儒家的“礼乐”思想,注重音乐的美育作用,其目的并不是为了音乐本身,而是把音乐当做社会的需要,是大众潜移默化接受社会改造,这就是《乐记》美誉在实践中的本质。
【参考文献】
[1]乐记批注[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6.
[2]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
[3]修海林.故乐的沉浮——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历史考察[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9.
[4]孙星群.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廖旋,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