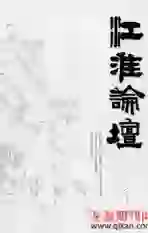在历史的追忆中追寻未来
2009-02-26周聚群
周聚群
摘要:本文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中的“历史记忆”概念分析了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的几篇(部)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高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运的反思,论文用“寻梦”概括了人物出国实现自身可能性的心理动机,说明他们在回来——出去——回来的循环中体现了作家对祖国情感的矛盾心态。
关键词:集体记忆; 历史记忆; “文革”; 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206 .7文献标志码:A
“文革”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社会、人性的悲剧已经在政治上被彻底地否定了[1]24-25,但是它的复杂性带给我们的感受和认识也是难以穷尽的。或许可以说,“文革”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集体记忆,思想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方式和途径来理解这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灾难事件。在关于“文革”历史的文学书写中,作家用自己“虚构的真实”逐渐达致“历史的真实”,不同的写作时间和空间表现出来的对同一历史的各种看法,都是由于他们不同的信仰、经历、兴趣、愿望和旨趣形塑而成的。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来自台湾的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有关“文革”题材的创作,就会发现这是和同时期大陆流行的“伤痕”、“反思”文学截然不同的作品,它们展现了多维度、多层面、别具一格的“文革”记忆。
与“文革”结束后兴起的“伤痕”文学流于揭露、宣泄、控诉甚至煽情相比,白先勇的短篇《夜曲》和《骨灰》、於梨华《寻》系列小说中的《江巧玲》和《姜士熙》以及聂华苓的长篇《千山外 水长流》少了急切的发泄,多了一份冷静客观从容与节制,远距离地审视和探究“文革”发生背后的深层原因使作品的文学性远远超过政治性,正如刘俊所说的:“这种‘距离的存在,使白先勇对文革的了解、感知和认识能够摆脱‘一己的局限和情绪的影响,而能以一种冷静理性的态度多层次、多角度地对‘文革进行一种比较全面的观照,并将它放在历史的年轮中进行高屋建瓴的俯瞰和历史的把握。”[2]401-402这个评价同样适合于於聂二位作家,只是表达的方式和介入的角度有些差异罢了。
熟悉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的人都知道,移居美国的他们没有“文革”的生活经验和切身感受,尽管他们在新时期都先后回到大陆过,可能与文革亲历者有过接触和交往。但是作品素材的主要来源或是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或是在海外听人讲述获得并在此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和想像,这种写作方式非常切合哈布瓦赫提出的“历史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历史记忆只是通过书写记录和其他类型的记录(比如照片)才能触及社会行动者……个人并不是直接去回忆事件;只有通过阅读或听人讲述,或者在纪念活动和节日的场合中,人们聚在一块儿,共同回忆长期分离的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时,这种记忆才能被间接地激发出来。”[3]42-43用这种间接的生活经验表达对“文革”的“历史记忆”是否比用亲身经历来书写的“自传记忆”更远离历史的真实呢?尽管哈布瓦赫同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更丰富、更个人化,也更有意义。”[4]51但是我认为文学创作仅有生活经验是不够的,还应该把没有经历过的经验世界主观化,融入自己的体验、见解和情感,才能创造出有别于文学功利主义和“政治文学”的“这一个”作品,李锐在一次对话中曾说过,“文学依靠的、表达的是内心的苦难体验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苦难经历”,[5]259说明用亲身经历作为写作的素材并不必然产生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让我们进入这三位作家的相关作品,分析他们的作品在反思“文革”、认识“文革”和表现“文革”有哪些相似之处。
这些集体性质的历史记忆是如何被作家们挖掘、表述出来的呢?通过文本我们知道,叙述的方式表现为讲述者与倾听者的对位,暗藏的叙述者既是倾听者又是记录者,有些作品还加上国内“文革”亲历者的书信作点到为止的间接转述;叙述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高级知识分子,二是红卫兵出身的知识青年。先看叙述方式。白先勇在《夜曲》中让吕芳在吴振铎的客厅里回忆她和高宗汉、刘伟五十年代回归大陆后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的悲惨命运,那种孤身一人、觉得“长夜漫漫,永无天明”的绝望感给读者一种寒彻骨髓的冷意。历尽人身屈辱和人世沧桑的女主人公情感徘徊在横遭厄运的悲愤和逃离文革梦魇后的心有余悸之间。纤美柔熟的萧邦《夜曲》和“胸怀大志,有远见、有胆识的”吕芳在时光与灾难的磨蚀下,更多了几分物是人非的沉重与艰难。与《夜曲》相比,《骨灰》则是言语直接讲述和书信间接讲述相结合。前者主要以“文革”回忆作为叙述重点,在反映了作者对乌托邦迷梦制造者暴虐行径的揭露与抗议,这种政治性的言说表达了白先勇对“‘人在政治下的处境的认识”[6]406:罔顾人性的政治对人的戕害和人在政治高压下的变形、异化和破碎,情感的激流在娓语式的倾述过程中渐趋平静;后者把一部中国现当代史的纵剖面展示了出来,“文革”事件是支撑整篇小说的链接点。“我”的大哥来信诉说父亲因“里通外国”被下放在崇明岛劳改农场,最后脑充血去世,信件留下了很多的空白:“文革”中父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遭遇,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本分的知识分子不得善终?在旧金山大伯家,我遇到三四十年代的“民盟”健将、“救国会”领袖表伯龙鼎立,他枯槁的神色、颓败的外表和凄凉的晚景全然失去了当年“为民请命”的激情和“民主斗士”的丰采,浓重的悲凉心态和“白忙一场”的无奈感叹是贯串作品始终的情感基调。在《千山外 水长流》这部长篇中,信件是连接主人公与母亲柳凤莲和养父金炎的纽带,母亲的倾诉让莲儿在逐渐了解上一代和中国历史的基础上,在自责中反省和忏悔了自己在“文革”中伤害父母的行为。作者并不止于超越时空的母女之间心灵的沟通和谅解,她在小说即将结束时设置了一个美国国庆日的华人聚会场面,由老李回顾了“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夺权的闹剧和中期一代人思想的初步萌醒,莲儿则追溯了反“文革”专制、纪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对人们心灵觉醒的巨大作用。这种见证式的叙事策略在文本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一方面借着对尘封往事的‘重演而迫使当事者面对不敢回想的往事;另一方面希望这种痛苦的‘口述经验能化解事件的纠葛与诅咒,使见证人在回想起伤痛的同时,‘忘却事件的恐怖。”[7]133“忘却”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埋葬往事、遗忘过去,而是在时间之流的抚慰下至少表面身心完好地在异国生存、生活和发展,在异文化的对照与反思中,产生重新认识自我、认识民族国家的渴望,萌发挣脱心锁的勇气和决心,这种为了纪念的“忘却”也表现了聂华苓难以释怀的感时忧国精神或者说根深蒂固的中国执念。於梨华的《江巧玲》和《姜士熙》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描写了曾经的知识青年江巧玲和姜士熙来到美国后的种种表现,但是无论何种处事方式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文革”的烙印和阴影。“我”——叙述者小胖——作为江巧玲的小姑,从侄女的言谈举止和对待婚姻的态度上认为她“是一个胸有成竹、算盘打得比你还精、看见过乌云、经历过狂风暴雨、对彩虹与晚霞都视而不见、见而无感的文革特产的女性。”那种勘破一切的世故和成熟、对物质的渴求超过精神需求的清醒是对“文革”神话的反讽。由于机缘,“我”和表面上玩世不恭、得过且过的姜士熙成了雇主——雇员的关系。“我”的关心照顾使他在“我”家厨房里一吐心中的积郁,对“文革”和无端诬陷迫害自己父亲的“张伯伯”的仇恨,对自己被操纵命运的讥讽和嘲弄。在诉说和倾听的来回往返中激荡着作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
这些小说都是以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作为表现的重点,不论是涉及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知青”的命运,都在印证着白先勇对“文革”的判断:“它是中国人的道德破产,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污点。……文革期间,我们民族性的阴暗面,封建传统的恐怖面,像并发症,统统爆了出来。”[8]78在“文革”期间,“他们学不能致用,才不能尽展,建国的理想,改革社会的热情,无由企达,”“遭受一种精神的凌迟,精神的死亡。”[9]38-39作为叙述对象之一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不论是留美归来的——吕芳、高宗汉、刘伟、姜父等等,还是出身“本土”的——罗任平、龙鼎立、江仿龙、姜母、金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打击、迫害等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凌辱,他们要么学会了见风使舵,身心俱疲、苟延残喘,要么灰心丧志、流落异国,不要说刚正直言者,就是逆来顺受者很多也摆脱不了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作家们就是从一个个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知识者为什么命运多舛的角度来反思“文革”这一从天而降的灾难。可以说,这种文学上的政治文化反思赓续了陈若曦“文革”小说的相关主题,但是在大陆,这股“反思”的文学潮流从缘起到夭折的时间之短说明了“对‘文革的反思势必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追问和对现实的质疑,成为对体制和权力机器的质疑。”[10]74所以白先勇们选择了超越反思“文革”的单一政治视角而从历史、文化的兴废存亡作为思考的重点,并且塑造了与自己“同气相求”的知识分子来反思他们频遭厄运的根源。其实从四十年代到“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社会地位和文化立场几经变换,但是小农意识的“反智”心态加上领袖对他们的缺席审判,无论是作为一个阶层还是单个个体,都难逃先思想改造——在监狱或“五七”干校里与工农相结合,再最后被当成一个“剥削阶级”被消灭的厄运。像血液一样无法根除的“原罪”使他们一个个成为待罪的羔羊,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巨浪中成了被撞碎的生命之舟,他们的遭遇和心境是一部用血泪书写的“失败之书”,个中的缘由与玄机颇令人深思。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於梨华的沉重喟叹:“风不吹,鸟不叫,万物都沉默了几秒钟,哀悼一个与世无争的、含冤而死的、可以对国家有贡献而被愚昧地剥夺了生命的读书人。一个、一百个、一千个、无数无数。可怜的中国人,可怜的中国,可鄙的愚昧!”(《姜士熙》)“知识青年”前身是“红卫兵”,是革命运动的“闯将”和“急先锋”,却由于红卫兵运动的分化和政治博弈的需要成了“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对象。这两个名称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两种身份,是一种思潮的两个阶段,是一种精神的两种形式,”[11]207这种“革命”身份的变化给予莲儿、老李、江巧玲和姜士熙精神上的影响非常明显,甚至左右了他们命运的浮沉。在聂华苓和於梨华眼中和笔下的红卫兵或知青,都在政治巨掌的控制和拨弄下,经历了被欺骗、被利用、被压制最终被抛弃的梦魇,无可避免地从民族、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成为被荒废、被憎恶、进退失据充满矛盾的一代,在这个令人窒息的“铁屋子”中挣扎、失望、彷徨直至产生冲破牢笼奔向“光明”所在的愿望,用悲剧都不足以概括每一个红卫兵——知青个体。与大陆知青文学相比,这三篇(部)小说没有“青春无悔”的苍白和空洞,不存在“感谢苦难”的虚饰与矫情,也绝少看见“我不忏悔”的偏狭及执拗,作家以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红卫兵造反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她们通过人物形象说明:应该接受学校教育的却被驱赶到广阔的农村去战天斗地,人为制造了一代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渴望爱情的青年却被禁锢在中世纪式的禁欲政策和封建的血统论之中,单一的阶级感情压制掩盖了神圣的爱情,用被权力玷污的信仰和理想蒙蔽尚不成熟的年轻人。两代知识分子表面不同实质则一的命运仿佛是历史老人向他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一个允诺实现而他们拼命追求的“黄金世界”被证明是一场痛苦的乌托邦梦魇和革命神话,噩梦醒后,在一片暴风骤雨肆虐过的荒原上如何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最终归宿呢?作家或叙述者的旁听姿态可以让他们从政治、思想、文化和个体命运的层面上思考“文革”的种种乖谬和背反现象。
白先勇们在作品里提供了一种寻找自我的可能性:出国留学或是移居国外。因此这些小说可以用一个“寻”字来概括“文革”后赴美寻梦者的基本动机,只是追寻的手段和目标有所不同。针对陈若曦回归大陆后又漂流北美的心路历程,白先勇在一篇序言中认为:“对一种宗教或政治信仰的幻灭,有时反而是一种解脱,一种新生的开始。”[12]30这何尝不是作家自己塑造人物形象时的潜在心理投射呢?吕芳重返美国是为了实现在大陆未曾实现的理想,只是理想已经从“用音乐去安慰中国人的心灵”转变成“用音乐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龙鼎立的目的仅仅是安度晚年,为自己及妻子寻找一个干净安宁的安息之地。姜士熙时刻想着“离开令人憎恶的家,令人沮丧的社会,令人提不起任何兴趣的周围的一切,出去闯天下;”对革命、理想的幻灭和抱着“为什么不找一个更好一点儿的地方去生活呢?”的想法,曾担任过红卫兵头头的老李泅水偷渡到香港,最后到美国当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谋生;而承载着父母希望——离开祖国,早日有个好归宿——的江巧玲以“婚姻是赌博”的心理嫁给了韩国人金约翰,寻求更安全的环境、更美好的生活和更有希望的未来是他们努力的最终方向;莲儿在母亲的鼓励和寻访生父故乡的渴望下踏上了石头城,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生活、学习和情感的新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很多人物身后都拖着长长的“文革”暗影,也许逃避过去的灾难和负累与寻找一方别样的天空是他们共同的选择。他/她们以回忆的方式向海外中国人倾述自己和亲人们在动乱年代所遭受的身心创痛和理想信仰崩溃轰毁后精神上的茫然无着,因此,“历史记忆”的书写也应该包括国家、民族、个体的苦难以及对苦难的隐忍和抗争,而不仅仅是“群体成员的事迹和成就”,这样的历史记忆才是完整的。而且追寻者的心态也因年龄阅历的不同有所差异,年长者如吕芳和龙鼎立对家国往事充满着无奈、不堪回首和一切皆空的透彻与领悟,而年轻一代尽管经受了不亚于自己父辈的磨难,也因为轻信受到“文革”主流舆论和极左政治的蒙骗,曾经得过且过、怨天尤人、灰心失望、憎恨一切,但是他们大多仍然努力渴望着有遭一日能返回故乡(像姜士熙、莲儿、老李),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政治清明的祖国,用爱来抚慰伤痕累累的亲人,以表明自己的忠诚与不曾泯灭的爱心。小说中的人物(不论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逃离“文革”阴影、追寻民主自由的新生活和感时忧国、回归文化母体的向心力是他们对祖国爱恨交织情感的真实体现,对民族国家苦难或是兴盛繁荣置身局外的道德重负使他们在归家或去国的选择中时有悖论和犹豫的反应,也间接表露出作家们矛盾彷徨的心理倾向。
作为“原乡神话的追寻者”,在“历史记忆”的叙述过程中白先勇、聂华苓和於梨华选用的叙事抒情模式不仅仅是“或缅怀故里风物的纯朴固陋、或感叹现代文明的功利世俗、或追忆童年往事的灿烂多姿、或凸显村俚人事的奇情异趣,”还应该包括对灾难深重的故国由于“文革”暴政引致的政治恐怖、文化失范、人性贫乏的反思和审视,它们也是“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因为国家是范围更大、内涵更深的“原乡”。[13]225在睽违大陆三十余年后,他们对“家国”的想像以动乱年代的政治运动为人物活动的大背景,在历史幽微的角落和缝隙里“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14]2这种想像通过追忆单个的、具体的人在政治的雨骤风狂摧折下的创伤性记忆与体验,用个人的“小”历史隐喻放大了曾被遮掩的国家的部分“大”历史。作者/叙述者与“文革”及其亲历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感藏匿不住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家国忧患意识,“何处是我家园”的困惑使作家们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去反顾苦难血腥的历史,并对他们的寻梦之路抱以同情的理解和回归奉献的期待。或许可以说,白先勇们是以“文革”书写这个媒介承载着他们难以释怀的道德负疚感?
注释:
[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4-25.
[2] 刘俊著,悲悯情怀[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401-402.
[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2-43.
[4]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1.
[5] 王尧著.“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5:259.
[6] 刘俊著,悲悯情怀[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406.
[7] 费修珊、劳德瑞著,刘裘蒂译.见证的危机[M].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转引自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0:133.
[8] 白先勇著.明星咖啡馆[M].台北:尔雅出版社,1987:78.
[9] 白先勇著.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见陈若曦.尹县长.序二[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5:38-39.
[10] 戴锦华著.隐形书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74.
[11] 许子东著.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0:207.
[12] 白先勇著.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见陈若曦.尹县长.序二[M].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5:30.
[13] 王德威著.想像中国的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25.
[14] 王德威著.想像中国的方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