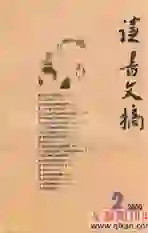罗伯昭和钱币收藏群体
2009-02-10郑重
郑 重
中国泉币学社第74次例会与会者在罗伯昭先生家中合影。前排左起:张伯、诸葛韵笙、丁福保、张翼成、郑家相;后排左起:杨成麟、戴葆庭、王荫嘉、张季量、陈亮声、罗伯昭、马定祥。
在收藏界,钱币的收藏是最具有普及性、民间性和群体性的了。1926年张叔驯、程文龙等人创办了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性质的钱币组织,还创办了《古泉》杂志,也是同仁性的刊物,仅出版了一期。古泉学社和《古泉》杂志虽然影响不大,但上述的“三性”已经表现出来。1936年由丁福保、叶恭绰、张叔驯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古泉学会,并创刊《古泉学》季刊,其寿命比《古泉》杂志要长了许多,出了五期才告中断,和前者相比,总算有了一些发展,并有了较好的结果。罗伯昭等人在1940年创办的中国泉币学社是第三个泉界收藏组织。
古泉学社的创办,大家公认罗伯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并把他的寓所作为学社举行例会的活动场地,学社的刊物《泉币》也主要靠他出力支持。然而出于对泉界前辈的尊重,罗氏率大家公推丁福保为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郑家相为总编辑,王荫嘉担任校对,戴葆庭为会计员。这个组织早期成员为13人,个个都是实业界和钱币界有影响的人物,由于抗战时局的动荡,他们是从四面八方汇集上海滩的。
为了寻找罗伯昭的行踪,我来到安福路7号中国泉币学会诞生地,一幢三层楼的小花园洋房,斑驳的门上已经钉了许多人家的信箱,说明这地方已经是“七十二家房客”了。唯有那合抱的绿树,和久经风雨的小洋房相映衬,还能记忆起小楼的主人和钱币收藏群体在这里聚亦乐、散亦乐的生活。
在小楼前,我伫立良久,心想这个地方真的应该成为纪念馆的。
寻找罗伯昭,巧遇宣古愚
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行的收藏家迎春宴上,我遇到多年不见的宣森,他原在上海参事室任秘书,专门为老参事们服务,后又到友谊商店负责古玩字画工作。我知道宣森和我同年,以年龄而论还不能成为收藏家,更不可能是对上海博物馆有特殊贡献的收藏家。
“你什么时候成为收藏家?对博物馆有何贡献?”我脱口而问。
“我不是收藏家,我捐献的是我祖父的收藏。”宣森说。
“你祖父是宣古愚?”我又一次脱口而出。在写《杭人唐云》时,我接触过宣古愚的材料,收藏甚丰,宣森所捐献的是他祖父的收藏,他的祖父就只能是宣古愚,不会再是别的宣姓。
“你写唐云8把曼生壶,有一把是从我祖父那里得到的,我祖父是有曼生壶,但唐云的那把绝不是我祖父的,……”宣森的眼睛瞪着,似乎要和我辩论的样子。
“好,改日我去你那细细地说。”我说。
再次见到宣森听他细说的时候,才知道宣古愚———罗伯昭———宣森,原来是连锁式的忘年交。
宣古愚[1866(同治五年)-1942]江苏高邮人,清朝监察大员,辛亥革命后移居上海,以清朝遗老的身份做了寓公,居住在当时属于法租界的淮海路。宣古愚的祖父是有名的盐商,父亲单传,到他这一代兄弟3人,只有他为官。袁克文曾拜他为师,跟他学诗词。抗战期间,地下党员徐平羽以为宣氏抄书保管古董的身份常住宣家,他们都是高邮人,为乡情所系。
张宗儒作《宣愚公先生传》
愚公先生,名人哲,字古愚,高邮宣氏,晚号愚公,而名亦删首一字,貌奇伟,腹大腰圆,望之不似南人也。以清生,援例试吏为主事,分陆军部,清光绪丁未,京师筹备各级审判检察厅,奏调法部,任京师地方检察官。都城五方杂处,地检厅为刑事总汇,先生博闻多识,尽知民间情伪,侦察重案,每为老吏所惊服。辛亥事起,挂冠南下,思天下将大乱,乡居似非乐土,乃斥售旧业,移寓上海霞飞路,邻多园林,遂署曰花园里,读书养志,不复问人间事。家藏书画古董甚富。先生精鉴别,遇有佳品,不惜兼金易之,所聚益多。无何忽摒除众好,而专以其志于古泉币,上自周秦,下逮光宣,旁及海外诸国,收藏美备,近代圆钱,颇重辽金元,集元代小钱尤富,为海内之冠。
宣古愚业余善画,好收藏,以藏古钱为主,曾为某一枚铜钱,三次去张家口,把古钱买到方才甘心。他所藏的元朝“供养钱”最为有特色,这种钱又叫“”,用风磨铜为原料制造,据说可以驱邪避灾。但这种钱在市场上不流通,只在建房架梁上用,再有女儿出嫁作压箱钱,讨个吉利。元朝已经使用纸币,铸钱逐渐减少,这就给元钱的收藏带来困难。宣古愚对元钱颇有研究,曾著有《元钱秘录》。宣古愚到了上海,基本上靠自己的积蓄生活,仍然继续收藏钱币,对罗伯昭等他视之为小辈,但对泉社他也给予很多的关心。到了他儿子这一代,过的是坐吃山空的生活,靠变卖父辈的收藏过日子;到了孙子宣森这一代,家藏文物所剩不多,但他收藏的元朝供养钱还有一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徐平羽到北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就动员宣森将其祖父的收藏整理捐献。这样,宣古愚所藏的元代供养钱140枚精品,经其孙子宣森之手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宣古愚著作除了《元钱秘录》外,还有《论钱绝句二百首》和《古玺之源》。他认为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平民用的印都叫玺,秦始皇当了皇帝之后,只有皇帝用的印才能称作玺,其他人用的玺就只能称之为印了。宣古愚还藏有三代古鉥字千余,经他研究认为,玺的文字不管有其千万变化,深入分析皆从“敬、事、信、诗、封、行、玺”七个字变化而来,自成一家之言。张宗儒在《宣愚公先生传》中写道:“终岁衣一大布袍,手污面垢,不事盥洗,而肴馔必丰,食兼数人量,海上学者凡治金石、训古式,又词章书画或精鉴赏,无不竞趋先生之门,每月必治具小集,谈论古今,时出所藏珍异,相互观摩,往往日昃而不知倦。”
宣古愚的山水自成风格。解放之后,在陈叔通的倡议下,他在荣宝斋办了一个小型画展,郭沫若、康生看了他的画也颇为赞赏,并同意出版。古典艺术出版社为他出了六开画页,后又出版余绍宋、黄宾虹、宣古愚《三家书画合册》,并由徐森玉写了序言。
古钱收藏三分天下:南张北方巴蜀罗
中国古钱的收藏在上个世纪的二十、三十及四十年代达到了高潮,藏钱家殆数以千计,藏品最富的则首推张叔驯、方若、罗伯昭。张叔驯是浙江南浔人,方若是天津人,罗伯昭是重庆人,故有“南张北方巴蜀罗”之称。
张叔驯名乃骥,字齐斋,南浔张石铭第七子。战前其父去世,他分得了二百万家产,成为房地产巨商,收集古钱有了充足财源。张叔驯不但是古钱收藏家,也是著名藏书家。钱币收藏家一般都是集中收藏自己喜欢的冷门。张叔驯也是这样,他所藏的宋靖康钱为民国期间的集藏之冠。古钱收藏家马定祥曾言,“余见齐斋藏靖康钱独富,举凡靖康之小平、折二、折三、元宝通宝、篆、隶、楷(真)书,铜铁钱,以及钱母,几乎赅备。”靖康钱之所以珍贵,因为此钱为北宋最后一年即靖康元年所铸的钱,古钱界称之为“靖康钱”。这种钱仅造一年,铸量极少而成了珍贵品种,版式却又非常繁杂,有元宝与通宝两种,元宝以篆、隶两体书写钱文;通宝以篆、真两体书写钱文,其中通宝小平又有真、隶两体合书一钱者。除了铜、铁钱外,还有银质通宝钱,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等三种。这种铸钱变化的频繁,很能反映北宋末年“乱世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的窘况。抗战期间,张叔驯把所藏古钱精品带往美国,但罗伯昭创办的《泉币》杂志上,每期都把他所藏精品介绍二三品,如“西夏大德通宝”,评介者认为此钱“具西夏钱气息,无元代钱风韵”,“今据实物,足证史氏之疏矣。此大德钱为前谱所无,今亦未见二品,洵属瑰宝。”其他如“阴晋—金化”、“虞—金化”、“半”、“天成元宝”等都有较高的价值。难怪罗伯昭说:“民国十七年及二十五年,吾先后方之于上海,观其珍藏,孤品异品,层见叠出,令人望洋兴叹,宜其有大王之称也!”
方若原名方成,字楚卿、药雨。抗战期间,在日本领事馆的卵翼下成为巨富,娶旅日华侨汤某之女为妻,先后创办了利津、益津、新津三大公司,经营房地产。方若发家后,曾大量收集古物,以古钱和石经为最多,兼及书画、印玺、端砚。他是天津“大罗天”古玩市场的最大主顾,古玩商为他四处寻找货源,因此能在短时间内积成巨观。他收藏的古钱精品及研究心得,汇编成了《言钱录》、《言钱别录》、《言钱补录》、《古钱杂咏》等,皆自费印刷或油印出版。他所藏古钱曾存入法租界盐业银行保险库,后经同乡张伯介绍,整批卖给了上海银楼少东家陈长庚,售价15万元。
对方药雨及张叔驯两位藏泉大家,张伯评论说:“自光绪中叶至今约四五十年,为古泉集大成时期,当以方药雨、张叔驯为中心人物。方氏好泉之始,在戊戌庚子之交,时老辈凋谢,鲍李云亡,乘泉界中衰之余,居北方冲要之地,嗜好既笃,经济又裕,大力搜求,嘉道以来数十钱币精英,萃于一箧,益出土之品,洋洋大观,蔚成当代巨宝,……足以与匹敌者,张叔驯耳,时有北方南张之称。张氏平最幼,好泉最晚,然嗜深力强,近自浙江,远及蛮荒,东南旧藏,西北新出,匪不罗而致之。若百川汇海,万流朝宗,不及二十年,竞与方氏分庭抗礼,同辈敛手叹服。”
罗伯昭(1899-1976)曾名罗文炯,号沐园。罗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经营桐油生意,曾任美商生利洋渝万分行总经理,1956年公司合营后,任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上海市第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黄浦区政协副主席、副区长。自二十年代初,罗氏就对古钱发生兴趣。在四川期间,他得到毛厚青(四川画家、收藏家)协助,收购了成都藏泉家杨介人的全部收藏,其中有真篆两体书淳熙背利钱、铁靖康元宝、咸丰宝云当五十、阔缘厚大的永通万国钱、顺治背宝川钱等,都是泉中名品,可望而不可得。后来,罗氏又从樊树材处得其所藏全部泥范,铁梁五铢及一品方背货泉,此泉亦是藏泉所景仰的名泉,因贝字长而方形得名,原为翁友三旧藏,樊氏以一部宋版书换得,后归罗氏。
1935年后,罗伯昭到了汉口,兼任汉出口部经理,在经营实业之余,与泉界朋友成立了“泉友会”,时常邀请武汉三镇的同好聚会,品评藏品,后来定于每周日共聚其府上,讨论泉学、交换藏品,成为泉界朋友活动的中心。这期间与之交往最密切者为汉口广东银行行长陈仲壁,罗曾从其中购得六铁(无大货二字)和战国秦权钱“第十八”天圣铁母等珍贵藏品。由于罗氏广交四方,以泉会友,名声随之大振,各地朋友携泉求教,求售,求交换者日踵其门,使他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西部地区的藏泉首富,与南张,北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罗伯昭曾返回重庆。1939年又迁居上海。此时的上海收藏家云集,商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很多都生活在上海租界里,过着城市隐居生活。罗氏到了上海,仍然继续钱币的收藏及会友活动,收藏中又有新品:通行泉货、楷书元符铁母、景和小泉、明仁宗洪熙通宝小平、保大元宝、元重宝背四端雀、大宋通宝当十大钱、大字宋元铁范、铁端平背利折寸、折二绍兴铁范等等。张伯曾评价罗氏收藏云:“伯昭同好中年较幼,好泉较晚而癖嗜之深,搜罗之勤,余叹不如。其所藏虽不逮叔驯、仁涛,然箧中不乏新颖可喜之品,两宋铁范尤为可观。”杭州人张晏孙则评之曰:“罗君深于泉学,且富收藏,久为同好所推崇,比来搜集日益勤,所得尤多珍美,在昔称雄巴蜀,今且争长中原,为南张北方之劲敌矣。”(《沐园四十泉拓》)
泉币学社和《泉币》的创立
1939年,罗伯昭到了上海,仍保持在巴蜀期间广交游、谈藏品泉的风度,与海上藏家数人,登高一呼,于1940年创办了泉币学社和《泉币》杂志。《泉币》杂志从1940年7月开始,到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停刊,共出32期。
《泉币》的内容分门别类,自有不少可取之处。《考据门》和《撰述门》有许多卓有创见的专著,如第一期上就刊有张伯的《货币释名》、鲍鼎的《鱼币之我见》、罗伯昭的《所谓灭监五铢之疑问》、郑家相的《明刀之研究》、《上古货币推究》等,都有很大的学术参考价值。在鉴别上,《泉币》则以严肃的态度分列《出品门》和《鉴别门》,前者列入确认为真品的货币,如张叔驯的“虞—金化”、“济阴传形”几十种名品在《出品门》中作了介绍。而尚待考证的则列入《鉴别门》,真赝严格区分,不使混同。《什著门》多属序、跋、史、传和年谱,摘抄之类,如丁福保的《历代钱谱序言》、王荫嘉的《寿泉集拓自序》、罗休园的《刘嘉灵传》等都刊载于此栏目。该栏目为读者提供了不少知识和史料。《通讯门》涉及范围较广,读之引人入胜。
泉币社活动及讨论《泉币》杂志事宜,多在罗伯昭家进行。如《泉币》第三期(1940年11月出版)《通讯门》发表了郑家相写的一条《泉友谈话会消息》云:“本社同人发起之泉友谈话会,自8月31日起,每星期六午后开会于副会长罗君住宅,已历14周,每次到会者10人。会式为自由谈话,或传观出品,或讨论刊物,或研究泉学,或交易泉币。每次由罗君躬自招待,茶点精洁,谈笑风生,同人兴致之浓,无以复加。”
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共出版杂志32期,共召开170次例会,都在罗伯昭家举行。罗伯昭在《胜利号献辞》中说:“此后基础已定,而人生聚散无常,发扬而光大之,是所望于诸贤者也。”文后编者附言:“比年物价高涨,本刊经费筹措,最为难事。如31期本预计为10万元,殊不料人文赖账,竟达39万元。罗沐园君有鉴于此,特商葆庭共垫60万元(罗40万,戴20万)预付人文,胜利号得以出版,皆二君之力也。”抗日胜利后物价飞涨,《泉币》的经费难以为继,就应验罗伯昭的伤感之言“人生聚散无常”,它也就寿终正寝了。
《大齐通宝考》和《临安府贰百文省释疑》
罗伯昭是钱币界“研究型”的收藏家。仅在1940年至1945年出版《泉币》杂志32期中,他先后撰写或提供藏品的文章就101篇,平均每期有三四篇之多。他治学严谨,言必有据,言简意赅,不绕圈子,虽寥寥百言,也能发前人之所未发。罗伯昭的文章分两类,一类是考证,另一类是鉴赏。在考证文章中如《大齐通宝考》、《临安府贰百文省释疑》、《建国通宝考》都是广征博引、阐幽发微、掷地有声之作。
钱谱著录大齐通宝,最早出现在戴熙的《古泉丛话》,据云:“酒人贻其先君古泉百许,中有齐泉二,破大齐其一也。”因为戴熙所藏的那枚残缺左角,所以叫“破大齐”,或“缺角大齐”。这品钱一出,轰动京城,藏泉家及学人定之为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铸。后戴熙与太平军作战,“殉难于杭州,遗泉不知何所矣。”李竹朋的《古泉汇》、唐与毗的《泉币汇考》、方药雨的《言钱别录》、丁福保的《古泉大辞典》等著作中虽有记载,但大家看到的都是拓片,谁也没有看到真品“大齐”。此后,古泉学勃兴,搜求奇泉,不遗余力,张叔驯获得“大齐”一枚,因自号“齐斋”。罗伯昭在《大齐通宝考》(刊于《古泉学》一卷第二期)中描述:“厥泉完整,阔缘薄口,背似夷而有四小孔,文字则与戴文节公藏者同范,通宝二字隶书。”关于此“大齐”的来历,是戴葆庭得之于江西某村。戴葆庭搜集奇钱,常走村串巷,足迹遍南北。一次他来到江西某村,村童踢毽子为戏,毽子恰好落在戴葆庭的头上,他捡起一看,毽子上有小钱一枚,视之赫然大齐也,遂购下,后辗转到张叔驯手中。后来,张氏将此带往美国去了。这个故事使罗伯昭大为感动,他不无感慨地说:“噫,物之显晦固有时耶?亦视乎人之好求,张君自幼癖泉,闻名中外,得享此泉,宜哉。”对前人把此钱定为“黄巢所铸”,罗氏在该文中提出质疑:“考大齐制作,酷似十国时物。南唐有大唐,蜀有大蜀,岭南友人拓其大越通宝,据云,是南汉刘龚初铸。五代时以国名钱者,有汉元、周元;宋太祖,以宋元名钱,固一时之风气使然,无足怪也。”罗氏引用了《资治通鉴》:“正月,吴徐知诰建齐国于金陵。”此事,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均有记载。徐知诰乃吴丞相温之养子,温事吴王杨行密有功,温死,知诰继其位为中书令,后封齐王。后三年,知诰乃篡吴位,立国称帝,国号大齐,改元昪元,罗氏断定“大齐通宝,必铸于此时”。
罗氏又云:“五代十国,群雄纷起,王纲未振,各自铸钱,或仍因唐制,铸开元乾元,或自以国号年号铸钱,如后蜀先铸大蜀,后铸广政;南汉先铸大越,后铸乾亨;齐初立国,先铸大齐,殆无疑义也。徐知诰以后唐沦亡,窃窥唐室,乃复姓李氏,更名昪,改国号大唐,号召人心,事见《十国春秋》,其铸大唐通宝,当在大齐之后,改国大唐时也。”
罗伯昭为“大齐”断代论文一出,引起各方面注意。1941年,流居香港的叶恭绰读了罗氏之文,由于记忆不当,错为丁福保所作,于是就给丁氏写了一封信,该信在1931年《泉币》第五期刊出,叶氏信中云:“尊论以此钱为徐知昪所铸,确当不易,戴(熙)论疏矣。”此时,叶恭绰在香港也得到一枚“大齐”,并有感而发,作绝句二首:
梦冷人间造孽钱,奇珍突降画从天。
贫儿压岁堪夸富,尤物摩挲九百年。
浙戴空传破大齐,黄巢制作语无稽。
天成广政应相拟,他日相逢试品题。
郑家相在该信后加了一段“编者按”,按语中有言:“若完整之大齐,未见真品。方劬园于五年前得一品,虽完整而不真,予所藏亦完整而不惬心,盖近年好事者伪作甚多,大都出自北平厂肆,或翻铸,或改刻,流入各地者累累。今以叶先生之鉴别,其所新得之大齐,当不属此类。如果完整而真确,诚为绝无仅有之品。”
叶恭绰读了郑家相的“编者按”,心中甚为不快,遂又致信丁福保,《泉币》又将此信发表,其中有句云:“至大齐一品,某君言外似有不信之意,弟不愿出以示众,致邻争辩。弟昔年早得一品,乃翻铸品(亦非近作,乃出自端午桥家),从不示人,平生最恶标榜,且藏泉有限,亦绝无与任何人争胜之心,殊不愿人人轻于忖度也。”叶恭绰所得“大齐”是不是真品,当时不了了之,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三枚“大齐”出现。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马定祥还重提“大齐”的断代问题,认为不是黄巢所制。其实这个问题在几十年已被罗伯昭研究解决,马氏重提此泉学之公案,已无新意矣。
“临安府牌贰伯文省”是临安府行用铜牌,牌为长方形,一端有洞眼,一面的文字为“临安府行用”,一面文字为“准伯文省”,常见的有三种,伯文、叁伯文、伍伯文,罗氏认为“所见壹伯文或一百文者,均伪作,不可信。”而牌文贰字,从弌从贝,遂起近代泉家贰之争。《古泉会考》作者翁树培(宣泉),是古泉鉴赏权威,他认为“实从弌”,疑是弌字,非“贰”字,方若《古钱杂咏》定“为一”。罗氏为此撰《临安府伯文省释疑》、《再说临安府伯文省》及《字余音》三篇文章,经过大量考证,认为“”字应释读“贰”而非“一”。
他写道:“考古文弌可作一,弍可作二,若从贝则遍觅字书无此字也。字不见经传,而强释之为一,于义终未安也。且钱牌之用,期以流通市里,出入凡夫俗子之手,果如翁氏所云,从一作一百,其字贤士大夫犹识之,而盼凡夫俗子能知之可乎?其不起市井之纷争也几希。故余曰即贰,从俗书。”
《建国通宝钱考》一文,更见罗氏考据与推理的功力之深。考据首要是言之有据,但无大胆想像,则考据必走进死胡同。“建国通宝”钱谱上未见,历史上也没有“建国”年号,对于鉴别建国通宝的真伪来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如果一旦发现这枚钱是真品,那将是一个大的发现,用现在的时髦语言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此钱本为绰号叫小江北的房良收自外埠,固为太离奇,竟被疑为建炎改刻者。如此,钱又流入天津。罗氏看到拓片,“文字精神,叹为未有”。此时杨成麒北行,将此钱追回归罗伯昭。罗伯昭“审视再三,果非赝作。铜色金黄,膛底松花绿锈,面带黑斑,销色坚美,权之得三公分六厘。版式狭穿大字,宝含圆贝,四字平整,一气呵成。遍查建炎各种图式,建通宝三字,决无此书体,焉能以炎改国。此钱轮廓风气,酷肖政和宣和,亦逼近敕制大字圣宋,其为北宋官铸钱无疑。试比南宋之制,固大相径庭也。”文章写到这里,笔锋一转,把罗氏的水平、才气及鉴别中的悟性表现出来,他写道:“然而北宋却无建国纪元,寻悟建国之义,岂取建中靖国首尾二字,以铭钱耶。”学问光有大胆推理和想像还不行,必须言之有据,罗氏又分析:“宋初,太平兴国年间,以首二字铭钱,曰太平通宝,兴国二字弃之。迨至大中祥符年间,则取尾二字铭钱,曰祥符元宝,大中二字弃之。徽宗嗣位,改元建中靖国,照例应以建中或靖国二字铭钱,然而唐有建中在前。意者,徽宗巧技成性,或以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义,爰取首尾二字,一度铸钱,理或然欤。”
罗的文中引用《宋史食货志》一段文字:“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轻重稍均,即听兼铸。”“余以为此钱,即陕西炉铜铁兼铸之时所出。”罗氏以元祐背陕钱较之,同为狭穿大字,轮廓大小及铜色,亦相近,其文字风度,近乎圣宋宣和,这样就判定了建国通宝铸造的地点和时代。“徽宗既铸圣宋,何遑铸建国乎?”经过这样一番研究,罗氏结论曰:“建国钱乃建中靖国改元试铸品,旋以其制不合,而改圣宋欤。”最后设想:“余按北宋钱自天圣以降,率真篆成对,今篆书建国已发现,其书建国抑或有之。”
罗氏文章一出,郑家相在此文按语中即说:“真书建国,予昔有之。民七八年间,陈信高为予收于江北者。制作精好,文字平正,却无伪作痕迹,唯因其过于离奇,漠然置之。二十七年,南京失陷,予所藏大半散失,此钱亦在其中。”
负责《泉币》校对的王荫嘉,曾经撰文,不同意罗伯昭的看法,罗氏三篇文章刊出后,王氏撰有《沐园创获即贰之铁证》一文,其中叙述他和罗伯昭讨论的过程,最后写道:“越数日,伯昭果欣然相告曰,得左证矣。出一书以视,则庆元本史记晋世家后记曰,史壹万伯拾壹字。一行之中壹之分,昭然若日月之揭。同好传观,相与画节。余亟请其书以制版,表余往日之过。”“于是元明人所置若罔睹者,乾嘉以来名儒硕彦所渴求莫得者,天下同志之所彷徨歧路研究无从者,一旦乃大白于世,夙积疑团,涣焉冰释,不亦快哉。”
君子之交 十步芳草
以罗伯昭为核心的海上钱币收藏者群,是中国钱币学社的基本会员,彼此相处都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风度,相互尊重,每有新品,大家同乐;每有创见,也共同研讨,也都言有固然,争之成理。这从戴葆庭的《珍泉集拓》中可见一斑。
戴葆庭(1895-1976)字足斋,浙江绍兴人。毕生致力于钱币的收藏与研究,曾协助丁福保编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泉图说》等。他所收藏的珍贵钱币,解放后捐入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博物馆,其中太平天国“平靖胜宝当千”等199枚,极为珍贵,这一举动受到中央文化部的嘉奖。编有《寿泉集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和《珍泉集拓》。
《珍泉集拓》计搜泉拓148帧,是他历时半个世纪以来新发现的古钱名品。其中有的至今仍是孤品,有的则已流落异国,海内仅存一纸拓本。这些钱多数由他亲自发现和集藏,部分则是程云岑、方药雨、张叔驯、罗伯昭等收藏家的名品拓本。
《珍泉集拓》珍贵之处不只是名钱拓本,更为有意义的是集有藏泉界诸多的题跋。其中有:张伯、秦子伟、宣古愚、缪继珊、张果园、方雨楼、鲍鼎、沈子槎、王贵忱、郭若愚、戴葆庭、罗伯昭、宋寄、蒋伯壎、郑家相、赵权之、马定祥、李荫轩、孙鼎、彭信威、王建训、丁福保、骆泽民。题记所及,或注明出典、或断其年代、或记流传之序,论其真伪,墨笔朱印,是前辈学者论钱议泉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最早的是题大齐通宝、题大泉五十,均成于1936年。最晚的是题应运应感钱,成于1966年,先后历时三十年之久。
从这些题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泉学的孜孜以求,坦诚相见,严肃认真的学术风尚。张伯在1941年的两篇题记中写道:“人情大抵好谀而恶毁,鉴泉不得尚义气,亦不可尚客气,孔子益者三友,吾主直。”“葆庭嘱题此册,余与之约,评判真赝,直言无讳,幸勿见怪,葆庭点首称善。”于此,书中有几处引人入胜的记录。如张伯初读此册,对圜钱“渝阳”有疑,当即直书:“上列圜钱,文似河阳二字,篆文恶劣,望而知为赝造,徒为本册之累,宜在删除之列。”时过五载,张伯在张叔驯处目验此品,毅然更改旧见,并于1947年2月5日补记,曰:是钱“家相释为洮阳,颇惬心意,而泉亦无可訾议,次页之评甚妄,自应更正。”如此还不作罢,又在原题上加注眉批:“洮阳钱有眼不识泰山,惭愧,惭愧。”反之,对阜昌通宝大钱,张伯指出为仿造,戴葆庭信服,在1963年春的补记中写道:“此品阜昌,张君所说,有先见之明,近年予再行审视,是泉实为后人仿大泰和之戏作。”
张伯(1885-1969)名晋,浙江宁波人。1927年到上海,曾任明华银行总行经理兼青岛分行经理,业余致力于古钱的收藏与研究。著作有《何谓泉货学》、《货币释名》、《新莽货币志》、《后素楼清钱谈》、《两铢泉考》、《小五铢泉考》。解放后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张伯亦是政治活动家,1946年国共和谈时,他是第三方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当时的《文汇报》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
在题记中,郑家相还介绍了篆书崇庆元宝和真书至宁元宝的鉴定:“篆书崇庆元宝钱,昔为王朴全君得诸辽东,旋抵于大方(时称方地山为大方)。民七大方尝携至沪,而沪上诸家皆疑为伪,未加注意。民九余客居津门时与大方过从,尝见此钱,肉间细翠,精美绝伦,叹为瑰宝,即问之曰老方(时称方药雨氏为老方),岂未之见耶。大方愀然曰彼亦疑之耳。余曰有是藏,愿以三百金易一可疑之品如何?大方慨然可。但押期未满,子其待之,至伯得至宁元宝钱而归,老方乃想及大方之崇庆,遂以三百金及异书大观钱易焉。噫,昔李鲍诸氏之疑至宁,犹近南北诸家之疑崇庆也。今日至宁证崇庆之不伪,亦由崇庆而证至宁之不伪,二钱因证方显,后世亦幸矣哉。”
郑家相(1888-1962)浙江鄞县人,自幼受其父影响,对泉币颇有兴趣。1916年在宁波中学任教时结识了张伯,从此兴趣更浓,逐渐成为钱币专家。1924年,他在南京得到古遗址出土的大量的南朝梁的钱币泥范,并撰写了《梁五铢土范考》,并自号“梁范馆主”。他编选的《泉拓》6册16卷,包括周秦至清代及外国的钱范,影响很大。他的泉币类著作还有《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瘗钱考》、《中国古代货币冶铸考》、《历代冶炼法考》、《明刀之研究》、《古代的贝币》、《古钱的伪造及鉴别》。他生前,将所藏的古钱及其他藏品陆续捐给有关博物馆。1962年,郑家相去世后,其夫人吴秀卿秉承先夫遗愿,将其生前收藏文物六千四百余件,全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当今,世界上藏泉家蜂拥而起,但罗伯昭及钱币收藏者群的收藏精神及交友古风已不复存在了,笔者不能不在此一呼:魂兮归来!
(选自《收藏十三家》/郑重 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