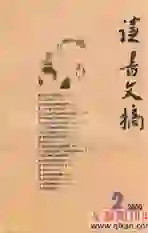“新三届”的青春记忆
2009-02-10王昕朋
“下乡镀金”是当时摆在新三届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虽然艰苦,但他们确实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一枚珍贵的毛主席像章
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新三届当时都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对于那场运动,不要说理解,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若干年后,只能从几件记忆深刻的事情中,找回一些感觉。
“文革”刚开始那阵子,谁能搞到一枚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那可是本事。红卫兵大串连时,我正在读中学的舅舅,跟着学校的红卫兵去北京串连,路过我们那里时,把我带去了肥东(位于合肥东郊)姥姥家。
那时姨妈的一位女同学经常来姥姥家玩,她经常说点笑话逗我开心。有一次,她来时,胸前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我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她看出了我的心思,假装和姨妈谈笑风生,但左手却不时朝上抬一下,好像在防范我。
过了几个月,父母亲来信让我回去上课。临走前一晚,姨妈的那位同学来了。她听说我要回去了,嘱咐我好好读书。我看着她胸前那枚毛主席像章,心里很不是滋味。
第二天早上,那位阿姨又来了。奇怪的是她胸前毛主席像章没有了,代之是一枚语录牌“为人民服务”。她和姨妈在屋子里说了一会儿话,走时眼睛红红的。那位阿姨走后,姨妈把我叫到跟前,打开一个小红布包,里边正是那枚毛主席像章。姨妈告诉我,那位阿姨早看出我喜欢那枚毛主席像章,但是她也特别喜欢。现在见我要走了,她才决定送给我。
姨妈把那枚像章放在我包里,嘱咐我一定保管好。因为街上抢像章的特别多。一路上,我都小心翼翼地抱着包。回到家,我才把像章佩戴在胸前。到了1970年,我已经读初中了,家乡一位在部队当兵的朋友,给我寄来了一枚铜质的毛主席像章,我才把那枚像章送给了一位对它向往已久的同学。
真正想上山下乡的没几个
那是1975年4月10日,一个天色亮丽的日子。下午,我们在铜山礼堂参加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欢送大会。会后,每个人披红挂花,乘坐各地接知青的车到知青点去。
实事求是地说,别看新三届上山下乡前要自己写申请书报名,但真正想上山下乡的没有几个人。那时,大学从工农兵中招生,从中推荐表现好的,应届毕业生望尘莫及;参军也是难上加难,就业就更没有门路。加上政策规定,家中只要有了上班的子女,其他孩子就要上山下乡。
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一些,就可能有让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参军或者招工机会,“老三届”中有些人已做出了榜样。那时,社会上称这叫做“下乡镀金”,是被批判的思想。但这又是新三届大多数人心中的目标,也是当时摆在新三届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
我认识几个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在农村的艰难困苦甚至让人无法想像,有些在贫困村插队的知青,常年连饭也吃不饱。知青们为了早日摆脱艰苦的环境,用尽心思。招工、招生、招兵名额有限,竞争十分激烈,有的男知青不惜“自残”,有的女知青不惜委身于当地村队领导……
尽管那时天天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是,人人心里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竞争。
从我们下乡那天起,新的生活开始了,竞争也开始了。我们那个知青点先后来了八十多个知青,主要来自徐州市和铜山县,家庭背景、成长环境不同,学历也不同,因此观念、性格、处世方法也不同。我们插队的果园,活儿有轻有重,有干净有脏。所以,分配岗位时竞争就已经开始了。有的父母想方设法儿托人找关系,给子女分配个好点的岗位。
我们知青点,也可以说我们新三届一代人,之所以没有进入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是因为时代有了转折。就在我们到了可以招工的年限,也就是插队满两年时,国家恢复了高考;1978年,一大批知青获准回城接班;接下来,政策也有了变化,知青全部招工返城,只是时间早晚、岗位不同。那段日子里,每天都有和知青点告别的人。
一只红木箱搭起知青“图书室”
我到徐州东的邓楼果园“插队”时,行李很简单,就是一包衣服和一只装满了书的红木箱子。那只红木箱是我下乡前,父亲专门给我做的。
那时,我家住在一所学校里。院子里有几棵榕树。清晨的阳光温情地照下来,榕树下就有了一片晃动着光斑的树荫。父亲就带着一身的光影,在那忙个不停。箱子钉好后,父亲又细心地涂上鲜亮的红油漆。
我把当时自以为珍贵的几十本书装了进去。那些书一部分是父亲保存的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家乡小镇上的那个废品收购站。父亲是个爱书、惜书之人,“破四旧”之前家里就有许多书,随后的“破四旧”也并没有让这些书遭到“灭顶之灾”。父亲把一些书悄悄地藏起来了,让我在文化贫瘠的年代还有书可读。
我的家乡安徽肖县官桥是个集镇,有一段时间,官桥供销社的废品回收站里旧书堆积如山。一开始,我装作若无其事,到书堆里随便挑了本薄书,揣在怀里就赶快朝家走。回到家,我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几个星期过后,废品回收站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我“偷”书的行为。但他们并没有责备我,更没有“处理”我,而是给我大开方便之门,让我到那些旧书堆里挑拣书。在那,我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文学梦。
那只红木箱装着一整箱书跟随我到了黄河故道上的邓楼果园。在枯燥的乡下生活中,红木箱里的书,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不久,我有一只装满书的红木箱的事,就在知青里传开了,于是,大凡爱看书的,都到我那里借书,一群年轻人久被禁锢的心灵终于找到了另一片天地。这只红木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果园知青的“图书室”,成了这些生活枯燥的青年人的精神家园。
红木箱子里装的那些书,大部分是那个年代禁锢的书,在书店里绝对买不到。如《红楼梦》、《青春之歌》、《普希金小说诗歌选》……
如今,红木箱已不再光鲜,斑驳的表面仿佛在诉说着它见证的岁月。
手抄周总理遗言
1976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几个月后,正当“四人帮”大肆防民于口,人们对总理的哀思无处可寄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了周总理的遗言,据说是写给毛主席的。
那天,我刚从果园劳动回来。果园医务室的大夫老潘找我,他跟我挺谈得来的。
“走,到我家去,给你看一样东西。”看他神神秘秘的,我满腹狐疑。到了老潘家里,他谨慎地关好门,然后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他先是哗啦啦地翻了一阵书页,接着从里面抽出了一张稿纸,低声说:“这是我从城里的一个朋友那里抄来的,是周总理的临终遗言。”
我大吃一惊,忙问他:“为什么没有公布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因为上边有人对外界封锁周总理的情况,所以这份遗言是他老人家身边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
我迫不及待地抓起稿纸———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永别了,同志们!共产主义万岁!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看完遗言,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室友们听我讲完后,也很激动,纷纷表示要牢记总理的嘱托、继承总理的遗志,让我无论如何要抄一份。当晚,我又去了一趟老潘家。在我的再三请求下,老潘只好让我抄了一份,只是再三地叮嘱我,一定要十二万分地小心。
几天后,老潘遇到我,偷偷地把我拉到了一边说:“现在上面查得很紧,你还是赶快把总理遗言烧掉吧。”我回到宿舍,越想越担心,就把那份总理遗言又偷着抄了几份,小心翼翼地藏在了被子底下。
不久后的一天,县公安部门真的来人了,我也被叫了去谈话。他们问我:“有没有见过周总理遗言?”我说:“没有见过,只是听人传过。”人家又问:“听谁传的?”我就说:“因为传得太多了,走在路上都有可能飘进耳朵里几句,谁知道是怎么传来传去的。”当然,县公安局的同志也是奉命行事,也不是要整人,就说以后别再传了。我一颗吊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虽然我们那时都不清楚,那段感人肺腑的话究竟是不是周总理的遗言,但我们却是把那份遗言当作真的来保护的。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早已不仅仅是一份遗言,而是代表了我们那一代人爱护战友、爱戴周总理、热爱祖国的一份神圣的情感。
改变命运的1977
1977年,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高考。在那个招工招生机会少得可怜的年代,这无疑是一次命运改变的机遇。
带着兴奋与对未来的憧憬,我和果园里的其他几个准备参加考试的人一样,开始了高考复习,回到了母校,重新坐在了阔别已久的教室里。这真是一间特殊的教室啊,本应在过去的十年里参加高考的人们被集中到了一起。年龄不一,身份不同,有农民,有像我一样的知青,也有工人、复员军人……有些老三届的知青当年已经结婚生子,为了照顾孩子,还带着孩子一起复习,常常是左手抱孩子,右手记笔记,还要时不时地喝住孩子的乱抓乱动。这样的场景实在是让人感动。
老三届的加入,对于我们这些新三届来说,无疑大大增加了竞争力度。因此,新三届的人复习起来就更艰难了。同老三届相比,新三届存在不少劣势,这些劣势最终在高考成绩上也有所体现。首先是各自的精神状态。那些成家了的老三届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而新三届,决心和意志就差一些了,因为那时已有消息说知青要全部返城参加工作。其次,尽管老三届想重新拾起十年前荒废的知识不容易,但毕竟很多知识他们从前学习过。而对于新三届,许多东西还是陌生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大量新知识,相当的困难了。
那一年,我们知青点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他们不但为我们知青点争了光,也为新三届争了光。尽管当时我没能考上大学,但我仍深深感受到了那扑面而来的新气象,更加珍惜每个点滴的时间,下定决心要在新的时代里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1983年,我成为江苏省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不久,又从事了专业创作,先后出版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1992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小时候的理想实现了。我感谢挫折,也感谢1977年那次难忘经历。
苹果飘香的季节,爱情也自然成熟
我们下乡插队时,十七八岁,也有一部分二十岁出头。正是“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的时节。但是,那时有规定,知青在下乡两年内不能谈恋爱。大概过了两年以后,情况才好了一些。那被压抑了许久的情感,终于得到了宣泄,知青点傍晚的活动从打牌、喝酒,变成了柳梢下、花丛间的窃窃密语,变成了互相督促、互相帮助的充实生活。就是这样一种简简单单的爱情,给知青点平淡乏味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滋润。
于是,一些胆大的,开始公开在一起吃饭,光明正大地交往起来。也有一些胆小的,还不太敢公开在一起。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虽然让大伙儿吓了一跳,但虚惊过后,这一群知青们却深深地感受到果园领导对我们的理解与关爱,不安的心也找到了一个平静的避风港。
那是苹果熟了的一个晚上。为了防止有人偷苹果,身强力壮的男知青会被分配晚上看果园。那天刚好轮到小A值班。远远的传来了脚步声,小A从床上坐起来,大声问:“是谁?”一个清脆的声音传过来:“是我。”看见女朋友来了,小A喜出望外,两人在蚊帐里讲起了悄悄话……
刚好那天夜里,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巡逻到了这个果区。几人发现守夜人不查不问的,便来到蚊帐前,只见小A和女友相拥着睡着了。几个同去的男知青面面相觑。那个领导没有言声,用床单把两人盖上,走了。当天夜里,那几个陪领导去巡逻的知青回来,吓得不得了,都在议论小A他们俩一定会受到严肃处理。
第二天早上,小A得知此事,当场就愣在了那里,他的女朋友更是惊慌失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小A顿时也没了主意,急得满地转圈。最后,他决定主动去找领导承认错误,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后果。
那天上午,小A不安地敲开了领导的门,红着脸,犹豫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说到昨晚的事。领导没听他说完,就打断了他,说昨晚一切正常,果园没发现任何情况。小A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办公室回来,他把结果告诉了女朋友,两个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其他知青听说了后,也不由地对那位领导十分敬佩,深深地感受到那位领导对知青的理解和爱护。后来,听说那位领导对别人说:苹果到了季节自然要成熟,何况是人,而且是活力四射的年轻人。
(选自《我们新三届》/王昕朋 著/作家出版社/200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