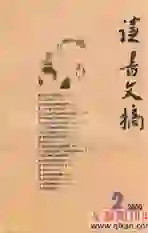一个孩子的文革成长史
2009-02-10叶兆言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敷衍。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运动中,最大最漫长的一个。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像,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地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最后得出了共同结论,这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化大革命在我最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最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化大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最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着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
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歪七扭八,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的反党言论,有一句无论如何也忘不了,那就是“共产党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这句话实在太形象了,很引人注目。一起看大字报的小伙伴转过身来,指着我的鼻子申斥:
“这话太反动了,你母亲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也觉得反动,太反动了。
小伙伴气鼓鼓地说:“你母亲竟然要把共产党扔到茅坑里!”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这么说,怎么能这么说。它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秘密,直到“文革”结束,有一次聊天,偶然问起母亲,她大喊冤枉。母亲说我是共产党员,你父亲也是,我干吗要这么说呢。但是她又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的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
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
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里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伶伶的一个人。
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天很快黑了下来,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一个人待在宽宽大大的厨房里,真有些害怕,于是便跑到大街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流浪了一夜。或许也可以称作是一种出走吧,自记事以来,还从未一个人离家这么远过,更没有深夜不归的经历。我为自己生长在这样的反动家庭感到羞愧,决定离开,决定跟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彻底决裂。夜色降临,我不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身无分文,茫然地在街上走着,哪儿人多就往哪儿去,哪儿好玩便往哪儿钻。这一夜,遇到的稀奇古怪,要一笔一笔说清楚,还真不容易。大街上灯火通明,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轮番演出活报剧,给我留下最最深刻记忆的,是一段轻松活泼的天津快板书。在当时,再也没有什么比快板书更适合街头宣传,说书者戴着个大鼻子扮演刘少奇,动不动就来这么一句,“提起了刘少奇,他不是个好东西”。这词非要原汁原味的天津话说起来才有趣,快板噼噼啪啪地响着,听众一边听,一边乐。
不远处,造反派正慷慨激昂辩论,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斗嘴吵架。那时候,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辩论者唇枪舌剑,不时地听见有人在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文斗就是讲道理,可是讲着讲着,就都不讲道理了,袖子捋了起来,拳头举了起来。眼看着要打起来,不知怎么的,又突然不打了,双方握手言和,然后又接着与第三方大吵,吵得不可开交。一方说什么好得很,一方就大喊好个屁。广场上“好得很”和“好个屁”此起彼伏,谁都不肯示弱。我一直没弄明白“好得很”和“好个屁”的争论焦点是什么,“好得很”这一派后来被称之为“好”派,它的对立面就成了“屁”派,“好”派“屁”派是南京两大造反组织,都出了一些了不得的大人物。
那漫长的一夜可以分成两部分,上半夜都和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下半夜与革命就有些距离。随着夜越来越深,耍猴的,卖狗皮膏药的,要饭的,都形迹可疑地冒了出来。耍猴的一个劲数落一只老实巴交的猴子,就像教训自己的孩子一样,好几个大人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看着,边看边笑。卖狗皮膏药的开始推销自制的肥皂,吹得天花乱坠,把机油和泥土往一块白布上揉,然后现场清洗给观众看,引得看的人赞叹不已。要饭的在数自己挣的钱,把硬币一枚枚摊在空旷的台阶上,数了一遍又一遍。在树荫深处,竟然还有一个男人在手淫。我当时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奇怪他尿个尿,干吗要那么复杂。
重新回忆这一夜,总有一种荒诞之感,连我自己都觉得它不真实,然而又确确实实都是亲眼所见。一群小流浪汉合起伙来,不费吹灰之力,就骗走了我脚上的新塑料凉鞋。他们是我新结识的伙伴,我们一起在广场上玩,从东窜到西,又从南玩到北,很快变成无话不说的小战友。夜深人静,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喧嚣的热闹劲过去了,我仿佛找到了组织,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伙小流浪汉郑重其事接纳了我,开始对我天花乱坠,哄得我这个九岁的孩子心荡神怡,对未来产生了太多美好想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在空中飞舞,我很轻易地就相信了他们的许诺,相信他们真能带我去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家伙是个瘸子,是个能说会道的语言天才,他自称是老红军的后代,曾经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还跟他老人家握过手。我对这家伙的故事深信不疑,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我,说什么我都敬若神明。最后他对我下达命令,让我像其他的小流浪汉一样,在银行门前的大平台上躺下来睡觉,他让我把凉鞋脱下来,当作枕头垫在脑袋底下,理由是这样不容易被偷走。
我困意朦胧地当真把塑料凉鞋脱了下来,搁在脑袋下面,美美地进入了梦乡。在蜜一样的梦中,我梦到自己和成年的红卫兵一样,爬山涉水,终于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见到了人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人山人海,一片欢呼声,我的鞋子被挤掉了,大家都赤着脚向前拥去,一直冲到了最前面,街面上到处躺着被挤掉下来的各式各样的鞋子。
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一时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躺在大街上。我已从平台的这一头滚到了另一头。我的鞋没有了,我的那些新结识的流浪汉小战友也无影无踪。
最后,我是光着脚走回家的。我被那些新结识的小流浪汉给耍了,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情谊,转眼间被糟蹋得干干净净。他们偷了我的凉鞋,兴高采烈逃之夭夭,像沙滩上的水一样蒸发了。我的失踪惊动了当地派出所,也让造反派感到不安,他们对我的失踪负有责任。我的父母还关在牛棚里,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有了,造反派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正分头在找。他们担心我被人贩子带走,落入坏人之手。我的出现让大家喜出望外,尤其是那些女弟子,虽然已经与我母亲决裂了,毕竟还有些残存的师徒情谊。她们像对待英雄回归一样地欢迎我,让我先饱餐了一顿,然后围着我七嘴八舌,一个劲地追问我把鞋子丢到哪去了。我结结巴巴说着自己的遭遇,多多少少有些添油加醋,她们听得一惊一乍。对于她们来说,这只是有惊无险,只是弄丢了一双鞋子,鞋子丢了,孩子还在,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吃饱喝足,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演员英姿飒爽地走过来,把我从母亲的女弟子手中接走了。她是造反派的小头目,是兵团的什么司令,穿一套草绿色军服,系一条地道的军用皮带。那时候,造反派全是这身打扮,真能穿上货真价实军服的人并不多。她身上是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仅仅凭这套行头,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在当时,有各式各样的军服,大多是仿制的,有的甚至是用土布自己染的,绿得莫名其妙,水洗以后,因为褪色,像迷彩服一样肮脏不堪。一套真正的军人制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代表着一种地位。
造反派小头目正和一位现役军人在谈恋爱,她身上的军服就是那个男人的,穿在身上大了一些,可是仍然很好看。我觉得最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最能引起人们回想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场景,莫过于绿军装与红袖标的配合。民间有“红配绿,丑得哭”的说法,南京方言里“绿”和“哭”搁在一起,不但押韵,而且朗朗上口。红和绿在颜色对比上,既尖锐冲突,又十分和谐。在一片绿色的海洋中,红袖标像鲜花一样灿烂。身穿军装,戴着红袖标的小头目神情严肃,径直走到我们面前,神气十足地宣布:
“好吧,你们现在可以把这小家伙交给我了,我有话要对他说。”
女弟子们立刻都不说话,似乎已经明白她要对我说什么,看看我,又看看她。
我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只是预感到会有些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依依不舍地看了女弟子们一眼,乖乖地跟她走了。接下来的谈话,对于一个九岁孩子产生的强烈冲击,丝毫也不亚于抄家。她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看了看四周,既兴奋又神秘地向我宣布,说你并不是现在的父母生的。她说,你只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你和现在的父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看着我吃惊的神情,她有些幸灾乐祸,和颜悦色地安慰我,说这其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是坏人的孩子。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她接着说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秘密,她说你知道,事实上,你是一位革命烈士的后代,你的父亲是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为了人民英勇牺牲,已经长眠于地下。
我不相信造反派说的话,又没办法不相信。突然,她的眼睛饱含着泪水,仿佛被什么事情感动了一样。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二十多年以后,在美丽的西湖附近,在革命烈士陵园,我看到了亲生父亲的墓碑,这个困惑了自己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解开了答案。我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是痛苦,还是麻木。对于一个九岁孩子来说,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极端,极端得不可思议。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突然之间,你美好幸福的家庭遭遇了抄家,父母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成了反动分子,成了反革命。然后又是突然之间,原本你生命中最亲近的人,他们竟然又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记不清楚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造反派小头目从头到尾,都没有拿我当作外人。她挑唆着我与养父母之间的仇恨,不停地安慰我,鼓励我,要我挺起腰杆做人,要像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要对得起那位为革命捐躯的亲生父亲。她说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你撑腰,党和人民站在你的一边,做你的坚强后盾,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她说你要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要撒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后还会开出鲜艳的花朵来。
几天以后,下课的时候,一名同学当着众人的面,模仿我父母游街示众的情形。他曾是我最好的伙伴,爬到了课桌上,拿腔拿调地发挥着,一会扮演我父亲,一会扮演我母亲。他说我们原来都觉得你们家了不得,谁都是人物,想不到你们一家都是坏蛋,你爸是个坏蛋,你妈是个更坏的坏蛋。你父亲是个大右派,你母亲不是江姐,她是甫志高。我听见了女孩子吃吃的笑声,那个在我心目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小女孩,那个代表着美好理想的小女孩,也幸灾乐祸地混在人群中。我的母亲曾是她心目中的偶像,现在,这个虚拟的偶像倒坍了,英雄人物已经不复存在,革命先烈江姐已经被叛徒甫志高取代了。孩子们的游戏很快进入了高潮,小女孩举起了拳头,大家突然高呼起打倒我父母的口号,异口同声慷慨激昂。
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就好像被心爱的人背叛一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笼罩在心头。真想把那个女孩子拉到一边,把自己的身世秘密告诉她。我要告诉她,我依然还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亲生父亲仍然是英雄人物。可是我没有勇气这么做,就算我说了,她能相信我吗?我不相信她会相信,因为我自己都不太相信。那是一个激烈的年代,革命是头等大事,革命就是一切,换了任何孩子,处在我的地位上,都应该被讥笑,都应该被诅咒。
革命是天堂,反革命应该下地狱。
(选自《亲历历史———张贤亮、冰心等作家名流的文革回忆》/叶兆言等 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