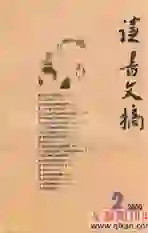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1955
2009-02-10姜异新
姜异新
“平淡而近自然”
1955年的大年初二(1月25日),纽约曼哈顿区八十街一座普通的公寓内,六十岁的胡适在这个全球最富庶的城市读着一本关于饥饿的故事。这已经是第二遍在看了,他看得非常仔细,不时为之动容。
故事描绘的是1951年上海附近的某个乡村农民金根一家在新年前的一二个月的生活:金根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刚刚分到了土地,不久前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在上海做女佣已经三年的妻子月香为此回到了家乡,却发现丰收的粮食都交了公粮,农村家家户户都吃不饱。年底到了,上级要求农民每家每户都要“自动”献猪肉和年糕。自家都没有吃的金根不满这种强派,与干部王同志争论起来,结果饥饿的农民在粮仓前与上级发生冲突。绝望的月香放火烧掉了粮仓,自己也死于大火。新年到了,饥肠辘辘的农民被组织起来,唱着秧歌给军属送粮。“呛呛砌呛砌!呛呛砌呛砌!”秧歌声声,“在那庞大的天空下,那锣声就像是用布蒙着似的,声音发不出来,听上去异常微弱”……
1955年,正是大陆大规模开展批判胡适思想运动的高潮期。胡适那些在香港和曼谷的朋友们零零碎碎地为他剪寄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刊登的清算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的资料。他的脑海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这连台三幕的洗脑戏,小说《秧歌》里的某种政治倾向似乎很符合彼时胡适对大陆的想像。
小说作者的文笔是那样的细腻,人情烘托竟每每使人泪盈于睫。当写那忍不得饿的顾先生,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又怕给别人看见时,作者如此描绘他的心理:“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这真是让苦涩的人也忍不住地笑出声来。在此之前,胡适好像还没有读到过这样无微不至的小说。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真诚地写道:“我读了这本小说,觉得很好。后来又读了一遍,更觉得作者确已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这本小说名叫《秧歌》,作者就是张爱玲。
对于张爱玲,胡适还很陌生。但是,《秧歌》里面的社会形势,却让他感到熟悉。他很想知道《秧歌》出版后,得到些什么评论,很想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尤其是读了张爱玲去年10月25日写给他的首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胡适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秧歌》,非常欣慰而高兴。他给张爱玲回信写道:“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他为此非常想知道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爱玲在2月20日回了信。遵照胡适的意思,寄上了五本《秧歌》,小说集《传奇》(1945年写成,1954年在香港再版),香港盗印版的《流言》,还有一本《赤地之恋》的英文本。
这年深秋,胡适就在纽约自家公寓的客厅里见到了这个不凡的女子,她与一位名叫炎樱的女友同来。胡适没有料到张爱玲的寡言多思,她天然地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贵气质,反倒那个锡兰女孩子,甚是活泼,胡适与江冬秀都很喜欢她,竟至于聊得很开心。
很明显,《秧歌》给胡适的印象比作者本人给他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他的日记里根本无暇出现张爱玲的这次初访。
出于礼貌,胡适在11月10日回访了张爱玲。这次他竟有一个意外地发现,于是,有了下面的日记:
1955年11月10日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拜访张爱玲女士\]。张爱玲,“author of”《秧歌》\[《秧歌》的作者\]。
始知她是丰润张幼樵的孙女。
张幼樵(佩纶)在光绪七年(1881)作书介绍先父(胡传,字铁花)去见吴愙斋(大)。此是先父后来事功的开始。
幼樵贬谪时,日记中曾记先父远道寄函并寄银二百两。幼樵似甚感动,故日记特书此事。(《涧于日记》有石印本)。
幼樵遗集中竟收此介绍一个老秀才的信———我曾见之———可见他在当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
《涧于全集》刻在一九二四,二十卷。
胡适想不出,作为晚辈的张爱玲来拜访他有何用意,她好像没有明确的目的,丝毫不擅社交辞令,甚至连这段完全可以将之与胡家列为世交的家庭背景,她压根儿就没想到要提起。她似乎并不需要一个漂泊中的倚靠。实际上,那时主要靠演讲、稿费和积蓄维持生计的胡适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当张爱玲第二次来到胡适家,端坐在他的书房中,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胡适的思维触角尝试性地探向这颗不可捉摸的心灵,他打算热心地由大陆谈起。
然而,张爱玲明显地对大陆的政治话题不感兴趣。她独自坐在那儿,本身就是那么的“平淡而近自然”。她并不随声附和,哪怕是一个晚辈出于对景仰者的礼节性的心境迎合也没有,这让胡适稍感尴尬。他猛然想起,她在信中似曾说过,国内对《秧歌》的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却并不怎样注意。
被“清算胡适幽灵”运动刺激着的胡适,似乎失去了“五四”时期品评文艺作品那种超然的眼光。他无奈地意识到这一点,自谦自己对《秧歌》的批评“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关怀这个柔弱的女子。11月24日,感恩节到了,他怕张爱玲一个人寂寞,主动打电话邀请她出来吃中餐,哪知对方跟炎樱刚从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回来,说是“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回来的路上,二人许是很高兴纽约的夜景像极了晶莹可爱的上海,在新寒之中说说笑笑,不曾想吹了风,刚回到家里,张爱玲就吐了。
胡适一听,知道张爱玲对美国的基督教文化还是不甚了了,美国人在感恩节是一定要吃火鸡的,怎会吃烤鸭这种中餐。既然如此,也就作罢。
饭局如果赴成,胡适大概会极力在自己的友人圈子中,引荐这位对于美国文化界还很陌生的大陆才女作家吧。但上帝安排了这段颇有意味的空白,使张爱玲对胡适始终保持仰望的视角,使胡适对张爱玲始终保持初见的陌生。
后来,胡适听说张爱玲住进了八十七街救世军办的职业女子宿舍,便前去探望。救世军是以军队形式组织管理的慈善公益组织,宣传基督教信仰。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里面收容了一些打算终老的胖太太、醉鬼流浪汉、病恹恹的老人,还有初来乍到只认识胡适的张爱玲。
胡适在张爱玲的引导下,走进黑洞洞的客厅,这是个足有学校礼堂那么大的客厅,因为没什么人而显得十分空旷。前方有个讲台,讲台上有架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
胡适一路四面看着,竟然满口说好,很真诚的样子,不像是敷衍,因为毫无虚荣心的张爱玲并不需要客套话。
救世军标榜“以爱心代替枪炮的军队”,这非常契合胡适演讲中的博爱主题。抗日战争初期,他为不战日本而斡旋,倡导和平主义;做驻美大使期间,他宣扬“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外交理念,无不与此观念相关。为此,胡适根本没有注意到张爱玲住处那简陋的陈设和物质的寒酸,他止不住地连连叹好,直到起身告辞,仍沉浸在这种渺远的博爱氛围中。
大门开启,胡适在台阶上站了会儿。隆冬的纽约,天寒地冻,呼啸的北风,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强劲地吹过来。胡适望着街口显露出的灰蒙蒙的河面,忽然想起了少年时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也是这么孤独地望着赫贞江,写下了白话尝试诗《蝴蝶》。他不由得看怔住了。那个时候尽管寂寞,但是与同窗好友互相切磋文学革命的热情是多么高涨啊,而今暮年已至,为之捍卫一生的某些东西,却是如此的脆弱,这灰蒙蒙的赫贞江多么像他此刻苍凉的心情,他并没有留意,这种苍凉恰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常见的底色。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捕捉到了胡适此时的心境变化。十三年后,她对二人在纽约,也是在世间的最后一面曾有一段著名的描写:
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
胡适无从知晓,十个月后,张爱玲第二次来纽约,是与和他同庚也就是大张爱玲三十岁的赖雅(Ferdinand Reyher)结婚。这位社会主义的崇尚者会对所谓的“反共”小说《秧歌》极为欣赏,大概是张爱玲爱上赖雅的一个原因———透过表面的政治看进她内心的凉薄,看透卑微的人在这荒诞的人世间又多了一种生不如死的形态。
但是胡适更不知晓,他之于张爱玲,是写作活动中一种必然的目光投射———“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这天是空白的,所以不会影响她的任意涂抹,这天是窗外的,所以可以随时收回目光;这天是不能不依傍的,否则又往哪里去凝神呢?
张爱玲的美国想像,很多来自于胡适。当炎樱说“你的胡博士……”时,当她自己说面对胡适“确是如对神明”时,谁能否认张也曾是个胡迷?
1932年,十三岁的张爱玲还是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初中生。她经常光顾父亲窗下的书桌,把胡适的《歇浦潮》、《人心大变》、《海外缤纷录》一本本地拖出去看。后来又发现了一本《胡适文存》,便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桌前一页一页地翻看。
此前,父亲曾为她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朱老师,教她念古书。当时,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买回来一本《海上花列传》,被张爱玲看到后,硬缠着朱老师用苏州土话(吴语)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老师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张爱玲和弟弟边听边大笑不止。从此,就无法自拔地痴迷上了《海上花列传》。
有一次,张爱玲破例要了四块钱买来了也是胡适考证过的《醒世姻缘传》,结果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做姐姐的大致已经知道了些眉目,便慷慨地给弟弟先看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好几年后,张爱玲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爱玲的姑姑有个时期跟张爱玲的父亲借书看,后来因为张爱玲的原因,兄妹二人闹翻了不来往。张爱玲的父亲有一次忸怩地笑着咕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张爱玲的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她的。”
张爱玲的母亲和张爱玲的姑姑早年跟胡适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国的照片,笑容满面,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爱玲的姑姑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这真是毫不含糊的一家子胡迷。很多年后,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饶有兴味地铺陈了这段家传。
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下午,三十五岁的张爱玲终于在纽约一座白色港式公寓房子内,见到了身着长袍子的胡适之先生。那杯中的绿茶,室内的中式陈设,太太江冬秀特有的安徽口音,无不使张爱玲的初访笼罩在一种浓厚的时空交叠感之中。
回来不久,机灵的炎樱就跑出去打听,然后冲张爱玲嚷到:“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尽管张爱玲梦想能和林语堂一样红遍美国。尽管寓居纽约的胡适早已从大使的位置上卸任下来,赋闲在家,正艰难地渡过他一生最潦倒的时期,张爱玲来美国最想见的人还是胡适。
就在这年冬天,胡适开始为《自由中国》写下《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一文,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大陆特别提出来做几次大规模清算批判的目标,“是因为在这个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近四十年的过程中,有好几位急先锋或是早死了,或是半途改道了,或是虽然没有改道而早已颓废了,……只剩下我这一个老兵总算继续不断的努力工作了四十年(从民国四年开始讨论中国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算起),没有半途改道,没有停止工作,又没有死……”
读到这里,一下子恍悟到张爱玲那么执着地来纽约拜见胡适的真意。
实际上,张爱玲已然表白了她对胡适身上“五四”遗风的崇敬之至。在来纽约前收到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她就注意到了胡适那加圈加杠的阅文习惯,完全是“五四”式的。“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零、三零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她明确地评价大陆“批胡运动”是对“五四”传统的遗弃———“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
1956年3月,张爱玲离开纽约,搬到纽英伦的“麦克道威尔艺文作场”。后来她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为其申请写作基金做担保人:一次是1956年9月申请哥根哈姆及尤杰伍•萨克斯顿基金会基金;一次是1958年二三月间,申请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胡适均欣然同意,第二次做保时顺便把当年收到的《秧歌》寄还给张爱玲。
当“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的《秧歌》辗转回到张爱玲手上时,胡适正离开寓居八年零八个月的纽约,经旧金山飞回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张爱玲看到这本经胡适反复翻读过的《秧歌》,站在原地,“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的欢迎酒会上发言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说着说着他出人意料地倒了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四年以后,张爱玲有机会翻译《海上花列传》。这时,她才猛然警觉自己实际上是把胡适当作一种传统来倚靠的。然而,难抑悲凉的是,如今这个传统真的不在了。“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这是怎样的一种失去传统的惶与恐,乃至于使她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了。
1955年,胡适张爱玲相逢于纽约,这应该不是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滥调。两个旁人眼中的人间偶像,此时此地,羁留其间,最简单的见面,却也是最真挚的温情。张爱玲写作巅峰的华丽转身,只是她美国梦的起头,而“黯淡中苦行”的胡适,的确是在希望中等待机会。尽管对张爱玲来说,纽约仍然是她企图向全世界宣告才华的世俗目标,而对胡适来讲,它却未尝不是一座精神上的孤岛。当上帝刚刚放手,他们就都那么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这座既充满自由又充满欲望的城市。在离开纽约港的一瞬,不知是否会会心地想起那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欢迎你,/那些疲乏了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那熙熙攘攘的被遗弃了的,/可怜的人们。”无论如何,历史还是别有深意地为我们留下了他们那同时望向雾中赫贞江的苍凉剪影。
(选自《书屋》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