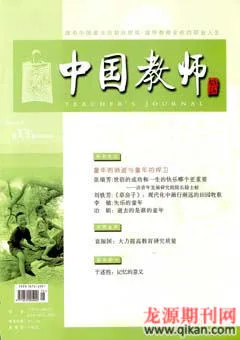记忆的意义
2008-12-29于述胜
中国教师 2008年13期
两种风格的历史记忆
去年暑期,读了两本个性鲜明的日记。一本是丰子恺的《教师日记》,记录着他抗战初期的流浪教学;一本是《吴宓日记》,记录了作者学习于清华学校开始直至晚年的生活。
抗战时期,是中国知识人最痛苦的岁月之一。当时的大学中人,因不甘心在沦陷区仰侵略者之鼻息,卷起行囊,背井离乡,跟随不断退却和迁移的大学,奔波流浪。丰子恺就是这流动大军中的一员。空袭、废墟、穷困、生离死别……也是其日记所展现的历史场景。写日记的丰子恺,却恰似一尊巨幅雕像,屹立在废墟之上:那来势汹汹、狂轰滥炸的敌机,在他眼里,不过是群蝇乱舞;简陋而异常艰苦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人生的历练。他会驻足农人院外,透过门缝,仔细倾听,去欣赏那夫唱妇随的恬淡生活;他把广西农村那些他从未见过、又相当机巧的器具,如出自匠人之手的门栓、窗棂、食篮,画下来,并仔细品评一番。当然,他也绘制了很多战争题材的图画,奋发激扬。他的绘画作品,观察细致入微,刻画入木三分,笔法粗犷朴拙、简洁明快,真有大智若愚、大辩若讷之象。难怪,他教学生绘画会强调境界高于技巧,文化重于技能;难怪,他能成为大画家——不,是艺术大师。
读吴宓日记,憋闷、痛苦的情绪,会弥漫在你的周围。吴宓很内向。你看他那时与家人的一幅照片(大概在他30岁左右),妻儿被置于身后,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从眼镜后面发出的视线指向水平线以下——不是向内的沉思,而是忧郁并带着拒绝地向外尖视。他希望自己能像“寅恪兄”那样,“闲他人之所忙,忙他人之所闲”,专心学问,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却又总受“参与”意识的驱使,一会儿当主任,一会儿办报办刊。一旦投入那些事务,就得同各种愿意、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周旋,可他偏偏不长于此道。于是,在他的日记中,你常常会看到,他会因为一件小事、别人的一句话,抑郁终日甚且数日。对于那些“不可忍”之人、之事,他竭力忍让,然后在日记中拼命发泄。他拳拳服膺“寅恪兄”,甚且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他也真该拜陈寅恪为师:不仅是学问,更是那种毅然决然的处世态度。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有学会。
我猜想,吴宓写日记,记得那么仔细,持续时间那么长,对他自己来说,主要是一种情感宣泻,平衡心理的手段。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位多愁善感者的日记,还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历史素材。有些东西相当生动有趣——毕竟,它反映了吴先生的真性情,尽管充满了痛苦和伤感。
记忆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动物:他在记忆中形成自我意识,获得生命的意义。记忆有选择性。人总会竭力强化那些想记住的东西,回避甚至淡忘那些不想记住的东西。但事情不会总遂人愿。一些东西之是否被记住,还与经验的强度有关。那些强烈的经验,会在潜意识中一再呈现,想忘也忘不了。
经验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有些人会有意无意间记住那些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总是笑咪咪的,充满快乐。他在接纳自己过去的同时,也接纳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从他身边走过,他微笑的目光与你不期而遇。你自然会以为,他是在向你微笑。那笑,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你的距离,让你与他亲近。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痛苦的经历,但他的态度,使他能超然面对过去,不会把过去的痛苦不断放大,更不会把它无有休止地传输给别人。他安慰痛苦中人,会说:“瞧!雨过天晴,有一片彩虹。快点看哪,别让它溜走。”
有的人,会倾向于记住消极的经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会不断地揭开未愈的伤疤,带着痛,去吮吸自己的伤口。日子久了,那痛,就堆积成皱纹,深深的,一道道,纵横交错,成就了一副苦不堪言的脸。他猛然看见你,会立即换一副笑脸。但那笑,也苦苦的,让你退避三舍。他不是没有快乐的经历,只是那快乐,更多的是成就了他人生的无常感。他想抓住,想让它留住,却留不住。于是,他对幸福的感觉倒超然起来,好像无所谓了。他只有时刻准备着,受苦受难。好像只有痛苦,才是永恒的。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总在寻求“本体”,寻求一种超越此生此世的“本然”的东西。表面上,这种寻求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调。其实,那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悲观主义,厌世主义。他安慰痛苦中人,会略带不屑:“嘿!那算什么?我经历的那些龌龊事儿,比你要严重得多。”
上个世纪,有两个“疯子”,尼采和福柯,也曾让这个世界上那些所谓“有思想”的人疯狂。他们颠覆了人们的整个历史记忆、文化想象。尼采从反权贵开始,走向反庸常,最后通向“超人”。福柯循着“考古学”的方法,把一切都还原为“权力关系”。但我面对那“考古学”,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由遍地骷髅和草木灰组成的层层废墟上,除了蠕动的“考古者”,还有生命的气息吗?一想到那考古者也会变成骷髅和灰烬的时候,我不禁毛骨悚然。
所以,记忆这个东西,可能充满快乐,也可能充满痛苦。尽管有时快乐会使人浅薄,而痛苦则可能使人深刻,要让我选择,我宁愿成为一个浅薄的快乐者。深刻的痛苦毕竟还是痛苦,我不太愿意像鲁迅那样去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
当然,有些记忆也可能是以“客观”形式呈现出来的流水账。碎片一样,没有感觉,记忆者本身先已成了“考古学家”的工作对象。我觉得,对于生命的记忆,还是要由生命来承担。那里,有色彩,有线条,有波浪,有花纹,更有气息。那气息会让生命充盈,抚平我们满脸的沟壑。
不灭的记忆
在过去,四十岁上下的读书人,就开始写回忆录了。学中国教育史,读过陈鹤琴先生的书。他就在不惑之年,写了《我的前半生》,借着回忆过去,畅想未来。那未来自然没有明白写出,但看得出来,它潜藏在作者对过去的回忆中。到了这个岁数,未来似乎已经很确定,却又不那么确定;态度似乎很坚决,却又带着一丝犹豫。
我如今四十有四,已过了不惑之年。不知为何,最近总想起一些过去的事,特别是中小学时代,点点滴滴,绵延不绝。有时候想得出神,自己会哑然失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代的我,光着身子,一个人置身无边的海洋,随波逐流,与天地为一。于是就借着悠闲的春光,从头写来,带着微笑,带着眷恋,也带着憧憬。既然都是些无法忘却的往事,索性就叫《不灭的记忆》吧。一边想,一边写,再一边自我欣赏。让记忆温馨自己,让过去照亮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