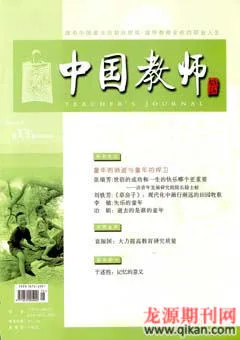《草房子》:现代化中渐行渐远的田园牧歌
2008-12-29刘铁芳
中国教师 2008年13期
孔子曾这样说到人性之质与文的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要么是文胜质,要么是质胜文。在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纲常礼教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在的渗透,实际上,在社会的主导教化体系中早已是文胜过了质。太多的文饰,导致生命因缺少激情与创造而变得平庸,更倾向于内敛。中国文化中阳刚的成分太少,过多地强调整体,过多地强调礼教、教育伦理化,直接导致文对质的过度教化。过度教化的结果是,生命因为失去了自然、丰盈的阳光本色,而缺少一种创造的激情与活力。现实中生活得比较阳光的人,恰恰是没有被过度教化的人,或者说是文与质相和谐的人。生命的成长需要尝试错误的空间,教化之于生命成长当然是重要的,但不能过度。问题在于,“度”怎么来衡量?只能以儿童自身的生命状态、儿童生命的自由与惬意来衡量。如果一种教育不是在成熟儿童生命的自由自主,反而遮蔽了生命本身的自由与惬意,这种教育就是过度的。
生命需要沉醉,就好像醒需要梦的呵护,清醒的人生需要不时的沉醉来呵护,这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代表一种理性,代表着秩序、清晰,按照社会即定的常理出牌。但个人在特定的空间忘记秩序,或者叫超越秩序,这就是尼采所讲的善恶的彼岸。人的生存有时候是需要超越善恶的,这就是游戏与沉醉,一种生命自在的生成与显现。正如席勒所言,只有人能游戏,人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成为人。的确,对于成长中的少年而言,不是简单地以外在秩序,以成人世界的生存秩序来规划、设计儿童世界,取代儿童生命世界中的自然秩序,而是在激发、诱导儿童天性的自然绽放中去促进儿童世界向成人世界的认同,从而促成儿童生命世界的丰盈与饱满,促进儿童生命的内在生长,无疑是现代教育渐渐被遮蔽的重要话题。
生命的“质”,这个“质”就是质地、原初、原始,需要我们更多地正视它们,“质”的显现在个体生命成长中很重要的。生命之质需要被提升,但是却不能被简单地抑制。过度的教化,往往会截断个体人生发展与生命自然善好的丰富而生动的联系,实际上大大缩减了个体生命发展的空间。当生命被过度地文饰,个体生命成长就触摸不到自然善好的踪迹,一个人的成长就可能是内在地无根的。失去了生命内在自然善好的引导,个人固然可以获得世俗意义中的成功,但终究少了点自然生命烂漫天真的本色,生命的颜色难免是暗淡的,缺少了郁郁葱葱的痕迹。
以曹文轩小说《草房子》改编的同名电影,就是这样一部探询生命自然善好与个体生命成长之间彼此交错的叙事。
儿童生命世界的展开与个体尊严的生长
《草房子》的叙事线索是多重的,贯穿首尾的是桑桑和他的父亲,其中关键的线索就是桑桑的生命成长历程。在桑桑的视界里,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以桑桑为中心展开的叙事,就是儿童世界中的桑桑怎么一步步走进大人的世界。大人的世界也就是社会化的世界,桑桑向大人世界的靠拢,也就是儿童自然生命世界向社会化的生命形态的靠近。桑桑向大人世界靠近的过程也就是他精神成人的过程,就是他生命成长的过程,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
1962年,一个叫油麻地小学的地方,在大大小小的一圈草房子边上,一位叫桑桑的小孩子怎样在远离社会中心的、遥远而美丽的草房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以这个主题作为基本线索,我们可以看到,影片率先展开的是优美的自然,还有儿童伙伴之间自由的玩耍,这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孩子所看到的生命世界的美好。搞笑、大量的民谣、各种各样的游戏、儿童的狂欢,还有恶作剧,看露天电影,等等,都是充满着自然野趣、同时又不乏某种人性的良善的一种表达,正是这些因素滋润了桑桑们个人生命的根底。
当儿童生命自然在无遮拦地释放之时,儿童世界的尊严也渐渐地绽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个体尊严的显现。桑桑和他的伙伴们在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在想方设法祈求着“被”这个世界“看”,“看”与“被看”实际上就是他们生命尊严生长的起点。其中最有意义的片段就是桑桑在大热天里撑着棍子、穿着棉袄、大摇大摆地行走在众人的注视之中,以及随后瘦高的光头陆鹤戴着白色的帽子在众人的拥戴般的关注中走进教室,以至于把得意的桑桑冷落一边。这其中不乏恶作剧的尊严的凸显与彼此之间有意无意的比拼,实际上都跟外在的规训无关,而更多地是儿童世界之人性自然的显现,非关教化的善恶。
影片中的陆鹤,可以视为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靠近的一个典型。陆鹤之为典型的意义首先表现在他的秃头,一种自然的野趣,这代表儿童世界中的一个极端,一种游离于成人世界规训体系之外的基于其生命自然的个性。他又要进入学校,融入周遭社会主流之中。进入学校本身就意味着向成人世界靠近,接受来自成人世界的规训,但他天性顽强的是,总是与体制化的学校教育保持微妙的张力,以强规训为特征的学校教育自觉不自觉地把他排斥在外,这导致他的尊严的被贬抑。显然,正是因为天性中与成人规训逻辑的差异遭至以教化自居的成人世界的贬视或打击,致使他无法正常地进入到学校教育的规训场域之中,典型的场景就是学校广播体操比赛对他的排斥以及他的反抗。反抗的结果不仅是进一步加剧了他和学校教育之间的裂缝,更重要的是他和周围同伴的关系都由于成人世界的介入而被瓦解,使他处于孤立无援之中,他不得不以让步的方式向成人世界靠近。陆鹤向成人世界靠近的一个机缘是学校的演出,因为演出紧缺的角色正适合于他的原本不光彩的秃头,也适合他的张扬、夸张的天性。在这里,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接纳与提升,并不是简单地排斥他们的天性,而是发掘、引导他们的天性,把他们引导进到合适的境遇之中,显现他们,并且成全他们。这里传达出来的乃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讲和,或者说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讲和。一种互赢的方式,使陆鹤进入了成人世界之中,演出成为儿童世界整体被规训的一个尝试,从此,使得陆鹤这样一个学校教育中的边缘人变成一个拥有正当位置的人,进而赢得他在成长过程中的尊严。
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尊严,有的是基于自然的人性来追求自己的尊严,有的是基于社会的认同,实际上这也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这也就是卢梭所说的由纯粹的自然进入社会的自然。陆鹤作为典型代表,提示我们,教育过程中怎么看待自然野性的问题。个人天性中的乖戾不合于当时的教育路径,常常遭遇教育的排斥;想和普通伙伴一样拥有同样的尊严,却又处处遭遇歧视。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当他对尊严的期盼得不到回应时,就会用越轨的形式,甚至是公然挑战整个成人世界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尊严。在那样的场景之中,甚至可以说在那样的时代之中,他可以是敢于表达自我、追求尊严的一个人。这里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对比,在我们之中,大多数人,特别是成人化的个人,都习惯于顺从命运,顺从世俗的力量,缺少抗争的勇气,比如白雀和蒋老师他们是羞答答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他们和陆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恰恰是基于自然人性的力量,而不是教化的力量,把个体在世的生命源初性的尊严充分地显现出来。
不难看出,在这样一种跟自然贴近的生命历程之中,儿童成长的一个最基本依据就是自然的善好。这里实际上触及到了教育学要追问的一个关键主题:个体的教育究竟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一个人究竟怎么样教化成人?如果说最初的教化就是把他生命中所浸润的自然底色都排开,让个体纯然进于体制化的教育形式之中,那么,这样长出来的生命形态就只能是白面书生,一种被过多的文饰、从而失去了生命自然底色的生命样式。我们的教化形式是文对质的遮蔽,我国几千年来以皇权为支持、以儒家伦常为主要内容的对于个体生命而言过于强大的教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国人生命之中的自然底色,遮蔽了个体教化之自然善好的基础,我们是以成人化、社会化的整体设定来取代儿童生命世界,儿童生命自然善好的踪迹在我们的教化体系中实际上一直处于遮蔽状态。《草房子》可以说是充分地正视、并展现了儿童的生命自然善好踪迹。
生命自然善好的无力与成长的代价
如果说影片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示了桑桑生命世界中美好的画卷,那么,构成桑桑他们生命世界的美好的源泉是什么?一个基本的来源乃是草房子所代表的自然世界!正是自然世界中的美好,游离在体制和中心之外、游走在社会边缘的自然,才成为小孩子生命美好的一个基本的参照,或者说生命美好的基本感受。这里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们引向美好,那么,美好的生活,或者美好的教化究竟从何开始?这实际上是教育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最初所显现的美好来源于哪里,第一个是纯粹的自然,包括周围的自然环境;第二个是人性的自然。在这两者之间的综合体,也就是说纯粹的自然和人性的自然的结合就是草房子。草房子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边缘姿态的草房子之所以成为桑桑们精神的家园,根本的原因正是基于其作为原初自然和人文自然的结合,而呈现出来的对儿童生命世界的贴身且贴心的呵护。
作为具有某种唯美主义倾向的电影,影片中尽量传达一种基本人性自然的善好,与此同时,也传达出这种人性自然善好的踪迹在现实中诸种因素的挤压,这种挤压既有成长的必然,也有现实本身的挤迫和社会偏见。杜小康家道的败落造成他的失学流浪,学校中学生的分等,使得放养鸭子的杜小康被排斥在高唱“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之外,这都是社会对个人成长的挤压。美好的破碎还有一层原由,来自于白雀父亲因偏见而对白雀与蒋老师恋爱的不赞成,这些都属于现实的挤压。白雀和蒋老师爱情的破灭还有命运的偶然性,而且还跟桑桑自己相关。桑桑原本是一个忠实的信使,并且因为对白雀和蒋老师的亲近而产生了对他们之间爱意的美好期盼,但这个忠实的信使因为一次很偶然的失误导致信的丢失,使他们的误会加深。这属于误会,一种生命存在中的偶然性,误会引发生命的断裂,但生命的断裂并不是误会造成的,而是生命内在的断裂。换言之,即使没有这个误会,断裂依然会以别的方式发生,断裂的根源在于自然的美好与现实的不美好之间的冲突。不管怎样,白雀以及她和蒋老师之间略带朦胧和羞涩的爱恋,乃是初长之中的桑桑生命世界里美好爱恋的象征;而他们之间恋爱的失败,则不仅仅是成人世界美好的破碎,更重要的是桑桑的基于自然善好之上的生命世界本身的破碎。
桑桑的父亲桑乔,同时又是校长,属于两者的集合体。一方面他的身上有很多自然的美好因素,包括他面对纸月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父亲、长者的天性,这种身份是去社会化痕迹的身份,他关怀纸月,并不是出于校长的名义。影片中,我们又不断地看到校长摇响手中的铃,这是一种社会身份的表达,一种权力的实践。桑乔就是这样不断地在两者之间不停地游走。他对桑桑的态度也是一样,既有作为校长的威严,也有作为父亲的慈爱。他发现桑桑损坏了他珍爱有加的荣誉本用来抄写课本,他把桑桑的行为视为对自己尊严的极度贬损,而这种尊严的基础正是基于外在的社会认同,这些荣誉都是作为自身体制化中的个人合法身份的一种象征。他发疯地追打桑桑,因为作为儿子的桑桑触犯了他作为校长的生命中最敏感的神经。那一刻,作为浸润在自然善好之中的桑桑的无力与作为成人世界代表的桑乔的强硬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当桑乔知道真实情况之后,他又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父亲的宽容和爱,桑乔卸下成人世界身份的重负,回复到蕴涵着自然善好本色的父亲身份。作为体制的代表,面对儿子的冒犯而施予一顿暴打,但并不能改变父亲对儿子的爱。这里反过来说明,作为校长的桑乔其实是紧紧地围裹着作为父亲的桑乔,自然善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现实的冲击,首当其冲就是作为父亲的桑乔。
桑桑走近落魄的杜小康,为他抄课本,稚幼的桑桑是基于儿童天性的友爱,基于个人自然人性的美好,来尽力挽救他困境中的同伴杜小康。为什么别人没有办法实现,而要小孩来承担?因为小孩的承担完全是基于个人对善好人性的一种自然流露或表达,而不是一种体制化的力量。而恰恰失学的事实本身,却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裂痕:基于个人之人性自然善好的力量在现实中于事无补,不足以改变既成的事实。桑桑试图尽力扩展自己个人基于自然人性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渺小。甚至包括桑桑充当信使,也是基于一种自然人性的善好,但人性的力量并不足以促成善与美的现实化。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人性的自然善好与现实中不好的冲突,这就是桑桑所进入的真实的世界,在这里,自然人性与历史和命运纠结在一起,演绎出生命成长中的纷繁际遇。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生命联系之中,桑桑秉持的自然善好心性,也一点点在现实周遭之中表现出美好而无力的一面。
如果说影片的前半部分,是桑桑为代表的儿童世界的开启,与以自然善好为基础的生命世界的呈现,随后,影片就逐渐把自然善好在现实中的遭遇一点点展示出来。伴随现实的诸多冲击,人性的美好开始在桑桑的视界中一点一点地失落。白雀和蒋老师爱情的昙花一现,杜小康的失学与流浪,纸月的忽远忽近与最终离去。还有在玩火过程中的失火,在偷看蒋老师信件过程中导致信件的丢失,实际上也是对自然人性的一种提醒,人性自然之质并不都是善好的,而且,自然善好的人性也并不总是可靠的。一个成熟的个人走进社会,是不能单纯靠自然人性的美好的,这意味着教化的必要性。
正是桑桑基于自然善好的人性与周遭生命世界的复杂纠葛,以及在现实中的诸种遭遇,才导致了桑桑的得病。在这里,桑桑的病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是精神的病,是一种生命根底的病,是一种阻遏之中的善好人性的病,是他的基于自然善好的人性想象寓居其中的肉身被败坏了。初始人性的自然美好原本具有某种完整性,但是这种完整性会在现实周遭的人与物的不完满性中失落,个人周遭世界的不完满意味着个人生命世界本身的不完满。一个人的心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周遭的世界就是一个人的心。桑桑的得病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更是因为他所遭遇的世界,所以病的根源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生命对美好的这种期盼,与进入现实所遭遇的自然善好人性的破碎感和无力感。
儿童世界的新生与生命自然善好的留驻
纸月在桑桑的生命世界里具有某种特别的象征意义。纸月来到桑桑的生命世界里,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神秘感,在不断地唤起桑桑心中某种美好的想象的同时,又始终与桑桑保持着若远若近的距离。从开始往纸月的被子上洒水的恶作剧,到夏日穿着棉袄的夸张表演,到纸月遭遇欺侮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桑桑都是在传达一种努力想赢得纸月的好感、走近纸月的生命世界之中的冲动。但纸月只是他年幼生命世界中一个飘忽的影子,最终黯然地离去。原作者曹文轩显然是借纸月有意无意传达这样一个意念:首先她是“月”。对于乡村成长起来的桑桑而言,月亮无疑是自然善好的典型代表,纸月带给桑桑的显然就是一种自然善好的敞开,是桑桑生命中的一种美好的期待。如果说白雀与蒋老师带给他的是成人世界美好爱恋的晨曦微露,那么纸月则是贴近他自己的生命世界的神秘爱意的朦胧开启。其次这个“月”是“纸”的,“纸”的“月”当然是不真实的,是易碎的。纸月带给桑桑的无疑是儿童世界美好爱意的开启与迅即凋零。这意味着就桑桑而言,纸月的离去是必然的,怎样把美好的回忆留在心中才是成长的应有之义。换言之,儿童生命世界中开启的人性之自然善好总是会随着自我的成长而逐渐消解、变色,对于成长中的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是怎样把这种美好留在成长的记忆中,成为人生发展永远的基础,留住童年世界所开启的基于人性自然善好的爱与美好,乃是成长永恒的主题。
我们每个人都期盼生命与美好为邻,亲近美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美好的事物大家都是很乐意去靠近,但是基于自然善好的人性在现实中又往往是无力的和易碎的,正是这两者的差异,成了他生病的根源。桑桑的病乃是一种成长之病,或者说成长的阵痛。每一个人的成长必然要置身于复杂社会关系之中,复杂社会关系的纠葛与沉重,使自然人性的美好变得不能承受,米兰•昆德拉说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里说的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为,人首先遭遇的是重的危机,而不是轻的危机。轻的危机是反抗,是放弃,而重的危机则意味着过度的承负。当自然善好人性的阻遏成为必然,人性的得病就不可避免,关键在于病的轻重与否。敏感的人更容易得病,人是泥土做的,不是钢做的,这就是生命的脆弱性。自然之质虽然有一种初始性的美好,但初始性的纯洁与美好毕竟要融入不纯洁也并不美好的现实之中,这意味着得病的不可避免。
所谓“对症下药”,桑桑的病其实并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精神性的、生命性的。正因为如此,桑桑的病的治疗非同一般,所以一味地求医问药乃无济于事。桑桑得病之后,校长回复到父亲的角色,在这一刻,他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救治自己的孩子。救治自己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成人化的世界中留住自然人性的美好,就是在当下之中留住未来。作为校长的桑乔,其父亲身份的回归,代表着成人世界对儿童世界的真诚接纳,蕴涵着成人世界本身被过度教化的人性向着自然善好的人性的复归。由于民间的非预期的力量,得病的小孩子在偶遇的情景之中获救,影片以一泡健康的尿结尾,象征着桑桑对自然善好的回复。父亲永不放弃的决心与民间并不可靠的奇迹,使小孩的病得到救治,疗治人性之疾病最好的良药就是——也只能是——优良的人性本身。人性的病还需人性来治,生命整体性的病乃需要生命自身向着自然善好的回复。
在这里,治病的过程充满一种隐喻。救治的过程,他要找医生,寻找医院,求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碰壁的过程。医院作为现代化、体制化的组成部分,医院问诊的失败意味着疗治人性的力量并不来自于现代化与体制化的力量,现代化与体制化并不足以救治人性的病弱,恰恰现代化与体制化本身就可能是人性之病源。拯救孩子,拯救自然善好的人性的希望在民间,是偶然性,是偶遇。既然是偶遇,那就意味着是非预期的,是不可靠的。救治方式的非预期性,非常规性,传达了对现代化与体制化的犹疑,不信任。现代化与体制化不可信,而民间救治又存在着偶然性,这意味着人性之病在当代社会中救治的无力。
如果说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去发现美好,获得美好,那么,在现实中,这种基于人性自然的美好恰恰无时无刻不受到来自现实的冲击。影片一方面试图充分地展现这种自然人性的美好,同时又更深沉地显现这种自然人性在现实中的虚幻与无力,从而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份流逝,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怅惘。由于影片中传达的这种美好的破碎,以及后面救治过程中非预期的不可靠,使整个电影具有一种植根于现代性中的、深切的、生命的悲剧意识。
自由的重建:从自然的自由到教化的自由
《草房子》由一种个人命运的叙述,变成一曲逝去的时代的挽歌。历史的进步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和舒适,带给我们开阔的、坚硬的空间和居住之所,但是历史的进步也逐渐淹没了我们心中的小房子。代表着乡村淳朴生活时代的草房子就只能作为一种反观当下生活的镜像,而留存在置身现代化之中的你我的想象世界之中。既然现代化和体制化都不足以呵护我们生命的完整性发展,我们又不可避免地要承负现代性的命运,那么,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当下的境遇中重建生命的自由与完整?我们固然是凭靠后天的教化生活在社会之中,但教化的自由如果缺少了自然的自由作为内在的补充,就会缺少真实的生命内涵而流于外在的适应与模仿。对于我们而言,思考当前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教育的起点在哪里?当我们被越来越眩目的现代化所围绕,我们还能找到教育的起点吗?更确切地说,我们还能找到教育所由起始的、所赖以发生的自然善好人性的起点吗?
以应试为中心的体制化的教育,越来越多地遮蔽了儿童生命自然善好的踪迹,世俗化的力量过早地设定了儿童在教育中的方向,小孩子从幼儿园里开始就被期待着要去考大学、考名牌大学,出国,挣钱,当明星……世俗化力量的冲击实际上大大地缩小了儿童在教育中陶冶的空间,实际上是缩小了儿童成长的空间,缩小了儿童生命成长的可能性,同时也遮蔽了儿童发展的内在生命起点。这就为我们教育提供了一个思考的主题,那就是:怎样重新拾回基于人性自然的善好,从而给个体人生找到一个可以永恒回返的起点。人成长的过程当然是不断向前发展,但同时又是一个不断回溯的过程,这两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向后走是一种意向,不是时间性的,而是空间性的,是把基于人性的自然善好带入到个体当前的心灵空间、精神结构之中。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从自我人性最初的踪迹中找到自我生命发展的可能的方向,而不至于被当下的某种特殊的目标、设计所遮蔽。对自我生命之自然善好的回溯,乃是个体成长恒久的参照,正是对生命本源的回溯,是个体生命的自然善好对当前生命状态的介入,调整着生命健全的方向。这不仅仅是个体的,同时也是人类的,人类的健全发展,同样有赖于对古典时代基于自然善好的健全人性的不断回溯。
曹文轩在小说的后记中曾这样说:
“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情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
由此推论下来,孩子——这些未长大成人的人,首先一点依旧:他们是能够被感动的。其次: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总而言之,自有文学以来,无论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还是写实的现实主义,它们所用来做‘感动’文章的那些东西,依然有效——我们大概也很难再有新的感动招数。”(曹文轩:《草房子》,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第277页。)
作者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对于初始人性自然善好之质的信赖与依恋。儿童生命中的成长与感动,正是来自对儿童生命世界的自然善好的激活,留驻童年的美好,实质就是留驻生命本身的自然善好之质,留驻生命的初始本色。
生命发展基于自然的自由、并从自然的自由逐步走向教化的自由的过程,自然的自由给人生发展以鲜活的质料,教化的自由则赋予自然的自由以美善的形式,一种类化的生命存在样式,而自然的自由之中则内含着生命的原初的美好。守护生命自然善好的踪迹,不仅给个体生命发展提供内在的生动的生命基础,而且给教育提供可以恒久回溯的家园,一切教育都从这里开始。
草房子:现代化中渐行渐远的田园牧歌
电影(小说)的题名是“草房子”,影片中也大量出现草房子的镜头。房子是我们的安居之所,房子同时也是人心安居的地方,但是这个“房子”却是“草”的。草房子有两层隐喻,第一层是草所代表的自然、感性、柔软,第二层是“房子”则代表着温暖、美好,合而言之,“草房子”代表着自然的美,贴近儿童生命世界的温暖。不仅如此,草就是代表着自然的天性,而房子是人为的,作为整体的草房子作为空间,意味着自然与人为的优雅结合,代表着自然向着人事的延伸和人事向着自然的贴近。理想的生命空间正是自然与人为的结合,草房子就是这样一种妥帖地呵护人性的、自然而温暖的生命空间,草房子本身就代表着自然的人性与社会性的有机结合,从而给儿童生命世界的发展提供一种自然、和谐、温暖的空间。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是两个小孩在草堆里打滚,草软软的,有着土地的香气,传递着一种贴近生命的温暖,睡在草上是很舒服的。这是草房子的第一层意蕴,作为一种温暖而自然的生命体贴。另一层意思是,草房子终究是易碎的,经不住风吹雨打,特别地,在现代化、体制化的进程之中,草房子不可避免地是边缘的,无力的。草房子提供的一种意象就是感性的,柔美的,易碎的。草房子也就是象征自然人性的力量,放大一点说,就是一种古典的、乡村的、贴近自然的心灵生活的力量。当现代化与体制化裹挟着权力的、物质的、利益的力量弥漫而来的时候,草房子终将灰飞烟灭,成为我们心中日渐远去的遥远的记忆。
无疑,草房子就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空间的表达,一种切近自然的、妥帖地呵护人性的、温暖的教育空间的期待。遗憾的是,童年的草房子终将随着年龄的长大、岁月的变迁,一点点逝去,取而代之是现代化、体制化的教育空间,是人为对自然的一点点的僭越,逐渐替代,草房子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无可奈何花落去”。这种远离,既有现代化的必然性,又有我们对现代化的单面追求而出现的人为与偶然性;既有以现代化来提升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合理性,又有着诸多难以言传的隐忧,那就是我们对自然、乡村社会的人文意蕴的否弃与遗忘。我们是否还需要留驻已经远逝的草房子?历史的进步是否必须以淹没我们曾经拥有的草房子为代价?如何留驻,并积极纳入到当代教育结构之中?当我们的社会在追逐着高楼大厦、追求着一种逼迫性的现代化之时,那些纯朴的、贴近自然的、贴近自然人性的生命空间到哪里去了?我们还能留得住,是否还需要频频回顾?
整个影片传达着自然与教化、乡村与现代、民间和体制之间一种微妙的紧张,草房子就是这种紧张之中的乌托邦,既是人性的乌托邦,也是一个教育的乌托邦。教育要回到这样一种最基本的生命状态,以这个作为起点来引导人性的优良。所以整个社会中的文明与虚华,包括教育中的文明与虚华实际上很有可能会遮蔽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是多媒体展现的世界,是世俗化的、外在的一些东西,实际上遮蔽了教育回望自然的视角。
沈从文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战士不是战死他乡,就是回到故乡。”这句话实际上从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来讲,就是生命永远要回到自己的家,这个家就是草房子,就是对人性自然善好的妥帖呵护。这种自然的善好并不是孟子说的道德意义上的人性善,而是原初的,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理想的人性,它只可以被想象,但它确实存在,但不能被具体化为某种实存,只能在想象中重现。我们不可能寓居在人性自然善好之中,回家是一种意向,不可能永远都在家里,家只是暂时,人总是要上路。真正的教育是要引导人担当人生的艰难,成熟的个体乃是能够从容地担当自我的人。在这个意义而言,尽管出发的命运不可抗拒,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心性,留驻善好的人性,从容地面对成长的阵痛,面对我们置身现代化之中的个人命运。在此意义上,草房子乃是我们置身现代化的路途之中可以恒久回望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张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