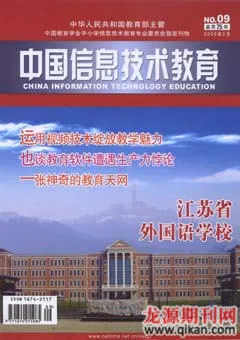图灵测试能证实人工智能的存在吗
2008-12-29魏宁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2008年9期
图灵测试是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最早被英国科学家、人工智能主要奠基人图灵(1912~1954)提出。在信息技术必修教材中的人工智能部分不但被提及,而且给出了一些可以对话的机器人,让学生通过与计算机的对话并寻找其中的破绽来感受人工智能的存在,例如机器人ELIZA等(http://www-ai.ijs.si/eliza.html)。人工智能是20世纪的新兴学科,也是当今的前沿学科,关于“机器能否思维”以及“机器能否具有智能”这样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作为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重要标准——图灵测试自然承载了人们更多的期望与质疑。下面,就让我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重温人们对图灵测试以及人工智能探寻的经典历程。
■ 图灵测试的提出:机器能思维
1950年,图灵在《思维》杂志发表了奠定了人工智能理论基础的著名论文《计算机与智能》,文章中提出了“图灵测试”,认为判断一台计算机是否具有智能可以通过图灵测试来检验。所谓图灵测试,简单说来,就是让一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分别与一个人和一台计算机进行问答,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如5分钟内),他无法分辨与他交流的对象是人还是计算机,那么这台计算机就可以被认为是能思维的,即具有智能的。图灵并且预言,在20世纪末,将会有30%以上的计算机通过图灵测试,人与计算机可以自由交谈。
■ 维特根斯坦:机器不能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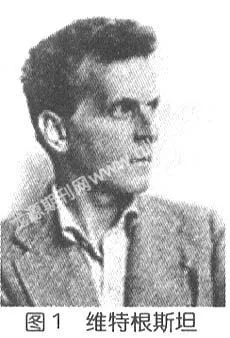
最早对“机器能思维”这一观点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是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的维特根斯坦(1889~1951)。虽然他的大部分生命历程是在计算机问世之前,但维特根斯坦对机器思维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深刻的思考。在他用自己生命最后16年时间完成的空前杰作《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就明确指出:机器不能思维。他的理由是:思维是生命现象,说“机器在思维”是无意义的,虽然计算机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它无法理解这些行为的意义,这不属于思维的范畴,他举例说,当机器停机时,可以说它在思考或者沉思吗?
■ 塞尔:中文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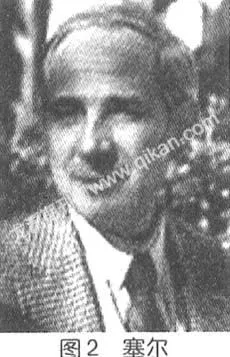
1980年,当代美国哲学家塞尔提出了著名的中文屋子假想实验,以回应图灵测试。他假定了如下情节:一个名叫丹玛的人被关在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屋子里,她只懂英文,不懂中文,而看守她的人则只懂中文,不懂英文。丹玛面前有一张桌子和各式各样的纸条,以及一本英文写的规则书,规则书告诉她如何为中文字符配对。如看守递进的纸条上写有“甲”时,她应当送出“乙”。对于丹玛来说,“甲”和“乙”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图形,而对于看守,“甲”与“乙”都有其自身的含义,并且对于从窗口递进的问题,丹玛都已经将答案递出。因此,看守认为屋子里的丹玛是懂中文的,而丹玛则对中文一无所知,她所做的只不过是按照规则书进行图形匹配而已。
塞尔的中文屋子比喻了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丹玛相当于计算机中的CPU,那本英文写的规则书则相当于程序,纸条是存储器,窗口则是输入输出装置。丹玛虽然给出了正确答案(通过了图灵测试),但是她对那些问题却毫无理解。中文屋子假想实验表明,用图灵测试来定义人工智能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
■ 彭罗斯:皇帝新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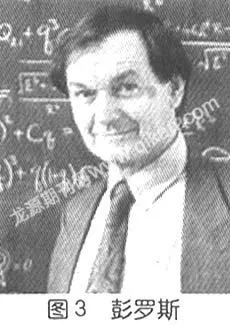
罗杰·彭罗斯,这位被誉为当代“最博学、最有创见”的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于1989年推出了《皇帝新脑》一书。该书立刻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上榜并达数周之久,并获得了1991年科学书籍奖,作为一部经典的科普著作给人们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在书中,彭罗斯借用童话故事“皇帝新衣”来隐喻计算机,正如皇帝没有穿衣服一样,电脑并没有头脑。他认为,要制造出能满意地通过图灵测试的计算机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即使真有计算机通过了图灵测试,我们还是不能断定它真的具备了智能。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彭罗斯以一个故事的形式不失幽默地攻击了图灵测试与人工智能。
大会堂里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标志着新的“超子”电脑的诞生。总统波罗刚刚结束了他的开幕词。现在,总设计师正在进行他的发言:“有1017以上的逻辑单元,这比组成我们国家中任何人的大脑神经的数目还要多!它的智慧将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马上就有幸亲眼看到这种智慧。让我们的超子电脑开动运行!”
总统夫人向前走去,有点紧张,也有点笨拙,不过她还是转动了开关。“嘘”的一声,这1017逻辑单元进入运转时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暗淡的光,每个人都在等待。“现在有没有观众想提出第一个问题来让我们的超子电脑开始工作?”总设计师问道。每个人都感到羞怯,生怕在众人面前出丑——尤其是在这个新的上帝面前。一片寂静。“可是必须得有一个人来提问呀?”总设计师请求大家。可是大家都害怕了,似乎感到了一个新的权威的威慑。
这时,坐在第三排的一个孩子举起了手,总设计师说道:“这位小朋友,你要向我们的新朋友提个问题,是吗?”孩子战战兢兢走到超子电脑面前,“是的,我想问的是,超子先生,您现在感觉如何?”“嗯,一个最有趣的问题,我的小朋友,我自己也想知道答案。”这位总设计师说道,“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朋友对这问题怎么说……真奇怪……呃……超子电脑说它不知道……它甚至不能理解你想问的是什么!”压抑的会堂里终于爆发出大笑……
■ 对诘难的反驳
正如《剑桥五重奏》的作者、美国著名科普作家约翰·卡斯蒂所说,塞尔和彭罗斯在20世纪80年代对人工智能的两轮“讨伐”引发的争论至今未息,他们的诘难也激起了人工智能界的反驳,同时促使人工智能学术界严肃地反思构成他们研究基础的一些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术语的提出者、1971年图灵奖得主、有“人工智能之父”之称的约翰·麦卡锡回应塞尔“中文屋子”假想实验时说:“虽然屋子里的人不理解中文,但屋子这个系统已经具备了理解能力,这就够了。我们就可以说这间屋子具有智能。”也就是说,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得到了理解,依据的并不是我们是否能够洞察这个问题在人脑或计算机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而是看人或计算机在其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在“中文屋子”中,我们所依据的只能是屋子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实际结果,而这个实际结果就是看守判定里面的丹玛是懂中文的。对于看守而言,屋子内部完全是一个“黑箱”,他无法直接和屋子中的丹玛沟通,就像我们不可能观察到在他人头脑中发生的思维过程一样。
正如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不停追问,“图灵测试能否证实人工智能存在”这个问题竟然涉及了人类与计算机的思维、语言、情感等诸多方面的争论。而针对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已经使其由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一个哲学问题,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尚未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或许我们应该重温图灵在《计算机与智力》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能向前看到很短的距离,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试问,假如图灵活到今天,他对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感到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