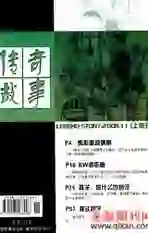剪影里的美丽
2008-11-21陈孝荣
陈孝荣
1980年冬季征兵,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逆转。当然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出现,我和我爹我妈还对我的未来充满期待。因为我们白云荒峡谷实在是太偏僻了,农村青年要想跳龙门,当兵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们村里已经有了不少这样的先例。其中最老的就是胡仙大爷,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他当了首长。年轻一辈的就更多了。混得最好的是严波,他当了几年兵,转业到地方后就在县人武部当了副部长,部长。即使是混得最差的也没有回农村,而是吃上了皇粮,混上了科长、股长什么的。所以从家出发前,我爹我妈就对我充满了希望。我爹说,建新这个身体考个兵绝对没问题。我妈说,考取兵,你就给我在部队里好好混,今后就不回这个穷山沟了。尽管我爹我妈说这些话时,我没有做声,但我的心里也是充满了期待。因为除了身体好之外,我还是我们村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之一。如果真顺利地考上了部队,我想我一定会混得很好的。
出发的时候是一天清早。宁西站在我对面的山包上喊的我。他说,建新,我们走呀。我说,噢。等我跑到对面,发现与宁西站在一起的还有熊钊。这样,我们三人便结伴朝石头坳镇医院赶去。因为初检的地方设在镇医院。我们在那儿过了初检后才能到夷城县医院进行复查。只有复查过了,政审过了才算考上兵。考兵的通知是我们白云荒村的民兵连长颜德龙来通知的。他说今年的兵种不错,是航空兵,要求很高。因而无论是我,还是宁西和熊钊,都希望这次能考上。
镇医院离我们家有四十多里山路。不通公路,我们全靠步行。好在我们年轻,我们一路奔跑,到镇医院时间也不算晚。医院的过道里、巷子里、楼梯里围的都是应征青年。好不容易轮到我,我是一路过关斩将,项项都OK。可是到最后一关,我却出事了。起初我不知道这最后的一关叫什么检查。后来才知道那是检查我是不是气卵,说是有气卵的人跑不快,不能干重活。这样的人自然是不能当兵的。检查室放在医院的三楼。楼上的人并不多,因为前来参加体检的应征青年到这一关的极少。绝大多数在前几关就被打发回去了。来到楼上,我就站在最后。站了一会儿,就听里面叫王建新。我就推门进去了。进屋后,我发现这间屋子很空荡。里面既没有必要的仪器,也没有供人躺下的床。只有两张简易的桌子。桌子上面好像放着注射器、针头、记录册、钢笔什么的。两把椅子散乱地放着:另有两个像木偶一样的医生站在里面。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男医生大概四十多岁,身子显得有些修长。那张还算过得去的脸上挂着冷漠的表情,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根冰棒。另一个女医生却非常年轻。后来我才知道,她并不是医生而是护士。今年刚刚从卫校毕业分到石头坳镇卫生院当护士。因为医院体检缺医生,她被临时抽来当了那个男医生的助手。后来当我对她的情况有了彻底了解后,才知道她与我同龄,也是18岁,只是出生的月份小了我_三个月零五天。从她那单薄的身子看,她还像个中学生,发育好像晚了一些,这显然与营养不良有关。不过她非常漂亮,她的漂亮主要是她有一张饱满的脸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张饱满的脸与她瘦弱的身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饱满、匀称、白皙、细嫩,红白极到好处,那双明净的大眼睛则像一片湖,纯净、天真、善良、自然。我一进入检查室,那个漂亮女孩子就将门栓死了。门被栓死的同时,那个像冰棒一样的男医生就毫无表情地对我说,把裤子脱掉。医生说过这话之后我犹豫了一下,因为这个屋子里有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我怎么能把裤子脱掉呢?但我的犹豫只有片刻。因为我是来检查的,我的目的是考兵,医生叫我怎么做我就必须怎么做。这样,我就脱掉了外面的长裤,只留下一条短裤。就在我把长裤往前面的椅子上放时,那个冰棒医生义说,把短裤也脱了。这一下我就真的紧张了。因为我知道脱掉短裤意味着什么。我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能在漂亮姑娘面前脱得一丝不挂呢?但冰棒医生的话却说得斩钉截铁,如果我想考兵我就不能违抗。这样在脱掉短裤之前,我还是犹犹豫豫地看了一眼男医生和女护士。男医生依旧显得那样冷漠,甚至有些不耐烦。女护士则栓死门后来到了我的面前,显然是在等待我脱掉短裤了。但看她的神色,她也同样是面无表情,见怪不怪。这样,我就毫不犹豫地把短裤脱了下来。脱下短裤我更加紧张了,所以将短裤扔到前面的椅子上后,我就像一根木棒一样站在屋子中央,眼睛望着窗外,一副任凭你们摆弄的模样。因为我知道。不管他们怎么检查,我的身体都没有问题。包括隐秘的地方也没问题。窗外自然没有什么,远处是房屋的屋顶。更远处则是对面的大山。没想这样站直后,那女护士又用冷冰冰的口气说,往前走两步。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我站到更加光明的地方,靠近那两张简易办公桌,让她能看得清楚些。听到女护士的命令后,我按照她的要求往前走了两步,站到了更加光明的地方。为了使自己保持镇静。我还将自己的身体靠到了桌子边沿。我站好时,女护士在我面前蹲下来,伸出她那柔软的小手给我检查了起来。她先是把我的那个物件扒到一旁,然后就捏住了下面那个肉袋。问题就出在这里。就在她的手接触到我身体的那一刹那,我的身体出现了剧烈反应。身子就像触电般颤抖了一下。所以这时我怎么也不能保持镇静了,而是收回眼光望了那个女护士一眼。女护士依旧是那般见怪不怪,公事公办的模样。而我在这一刻却是紧张到了极点,心里就像打鼓一般咚咚跳了起来。接着,就见她扒开了我那个物件,捏住我那个肉袋捏了几下。这时,我那个物件硬挺了起来。几乎是刹那间,那个女护士顺手拿起简易桌上的那只注射器,照着我那个硬挺的物件就砸了下来。砸下来的同时,她还气愤地说了一句:“流氓!”
我的命运就是在这一刹那急转直下,朝另一个方向滑去的。因为女护士用力很大,我的物件被砸伤了。女护士砸下来后,我痛苦地大叫了一声,接着我本能地用双手护住我那受伤的物件,整个人则像一堵墙似的倒了下去。倒下去后,因为疼痛太剧烈,我就像一根木头一样。在地上滚过来又滚过去。同时,我痛苦地大喊大叫,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我反复滚动的地上,留下了一摊血迹。
就在我疼得满地滚的同时,那个像冰棒一样的男医生就埋怨女护士说,你怎么能打他呢?女护士没有说话,而是呆了傻了,像木头一样站在那里没任何反应。男医生说过这话后。赶紧跑到我身边问我,怎么样?伤得重不重?我没有回他的话。因为我疼得实在没力气回答。我依旧在大声叫喊,哎呀,我的妈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那个男医生一时也变得手足无措。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猛烈的拍门声,并有个声音大声询问,怎么回事?开门!呆在那里的女护士终于醒了。她赶紧打开门,门外的人一下子拥了进来。拥进来的人有院里的医生,有考兵的青年。同时屋外也传来了喳喳哇哇的嘈杂声和人在楼道里跑动的声音。有个医生问怎么回事?那个像冰棒一样的男医生说,她把他打了。其中有个人问那
个女护士,你把他打了?女护士没有回话。就有几个医生说,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送到住院部。说过,他们就按住滚动的我,问我,你能不能把裤子穿上?我说哎呀我的妈呀,我现在疼得要命。有个医生反应快,顺手拿了椅子上的裤子往我裆里一包,就对另几个人说,快,帮忙抬一下。那几个人就立刻把我抬到了住院部101号病房。抬进病房后,接着门就关了。屋里只留下三个男医生为我检查。检查后,其中一个医生说,伤得很重,可能不能生育了,另两个医生没有回话。接着他们就给我清洗了伤口,上了药,挂上了液体,并给我裆里缠上了许多绷带。处理完这一切,我的疼痛就没先前那么剧烈了,房门也随即打开了。
房门打开后,镇里的书记杨锐、镇长胡丹、人武部长张显峰等干部和医院里的院长周琼冬,到我病房里来看我了。他们问过了情况后就安慰我说,你不要伤心,安心地养伤。所有的医疗费由我们负责。他们这样一安慰,我又哭了起来。当然这一次哭不是疼痛,而是恐惧,现在清醒后,我对我的未来充满恐惧。我知道我的一切都被那个女护士一注射器给打碎了。书记杨锐说,那个什么?院长周琼冬说,李玲。书记杨锐说,李玲又不是故意的。院长周琼冬说,我们一定会严肃认真地处理这次事故,给李玲严重的惩罚。人武部长张显峰说,你放心,我们已经给你们村里打了电话,你父母很快就会赶来。这样劝说一遍,我终于安静了下来。我一安静,那些干部们也就走了。干部们走后不久,宁西和熊钊就进来对我说,我们要回去了,你有没有什么信带?我说,我爹我妈可能在路上来了。若是你们碰上他们,就叫他们快点。宁西和熊钊点点头,就走了。他们一走,病房里彻底安静了下来。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其他闲人均没一个人再围在我的病房前。
傍晚时分,我爹我妈匆匆忙忙进来了。一进来看了我的情况,他们伤心地哭了起来。尤其是我妈,哭得眼睛鼻子都连在一处,说,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今后我们该怎么搞呀?我爹则气得暴跳如雷,他说,妈的,她把我家的根断了,老子去把他们一家杀了!说过就要往外闯。我妈一见要出事,就赶紧拉住我爹说,你冷静点好不好?我也说,爹,你就别再多事了。我爹软下来,说,唉!我们都知道,我爹是个鲁莽的人。他头脑简单。做事不计后果。如果凭一时的冲动真把那个叫李玲的护士怎么了,事情就更不好办了。再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无论是李玲还是我,我们都没有错。李玲打我那么一注射器,是出于一种本能;我呢,那物件受到刺激要硬挺起来也属于正常现象。我有七情六欲,并非我在她面前耍什么流氓。当然我爹我妈的愤怒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只有我这么一棵独苗,如果我真残废了,不能给他们传香火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我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和他们活着的唯一理由。我爹叹息了一声后,我说,不能蛮干,一切等我的伤好了再说。我爹便在男一张病床上坐了下来。这样坐了一会儿后,我妈就问我还疼不疼?我说不疼了。我爹说,饿不饿?我说不饿。我妈对我爹说,你赶紧出去给他买点吃的来。我爹没做声,站起来出去了。爹一出去,我妈就为我擦去了泪,我也为她擦去泪。我妈说,现在什么也别想了,安心养伤,等伤好了我们再找他们。我说,如果不残废就算了。我妈说,嗯。过了一会儿,我爹回来了。他手里抱了两筒麻饼和一斤白糖。见到这些东西,我妈说,你就不能给他买点罐头或是麦乳精什么的?我爹说,供销社也没什么卖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说,这些就行,我不饿。我妈便从我爹手里接过麻饼,拿出一个给我递了过来。我爹则赶紧给我冲糖水。吃麻饼喝糖水的时候,我问我爹我妈,屋里请谁照护?我妈说,屋里的事你就别管了。我便不再多话。这样,吃过麻饼,我妈为我放好枕头,说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我说,那你们呢?我妈说,我们困了就在这个床上眯一会儿。我没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也许是见到我爹我妈心情放松了的缘故,我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我就被一阵吵声惊醒了。睁开眼。发现是我爹我妈和镇里的书记杨锐、人武部长张显峰和院长周琼冬在争吵。我一睁开眼,他们的争吵就停了。所以我并不知道他们争吵什么。人武部长张显峰对我爹我妈说,一切都放到明天再说吧,事情总归会有个结果。镇委书记杨锐说,明天你们吃过早饭后到镇政府去,我们在那里商量。我爹说那也行,他们站起来走了。他们走后,我爹说,反正一条,建新不能残废,残废了我不会就此罢手。我妈说,残废了,我们就把我们两个老家伙和建新交给政府。我爹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妈的这种说法。听他们这么说话,我的心里也沉重起来。现在看来,李玲的那一注射器后果相当严重。影响的除了我们王氏家族之外。还包括医院和政府。她伤害了我,我的爹妈和我们王氏家族的人。医院除了蒙受经济损失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荣誉受到了损害。政府则要承担责任。因为征兵是政府行为,出了事,当地政府不能一推了之。正因为问题如此严重,镇委书记杨锐、人武部长张显峰和医院的院长周琼冬才在我爹妈来之后,赶到医院看望他们。这时我说,你们没和他们吵吵?我的问话终于使他们清醒了过来。我妈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想。你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我说,你们不能和他们吵呢。我爹说,一切事情我们会处理好的,你不要操心。我妈说,你闭上眼睛再睡吧。刚才是我们把你吵醒了。我没再说什么,闭上眼睛又睡了过去。
夜里我醒过二次。每次醒来,我都发现我爹我妈还坐在床前说话。第一次醒来,我对爹妈说,你们怎么还没睡呢?都半夜了。我妈说你睡吧,我们不困。我因为太困也就没说什么,又睡了过去。第二次醒来天就快亮了。我听我爹说,镇里找不好,我们就找县里去,县里找不好我们就找省里去。很显然,我爹我妈一夜都没合眼,他们正在合计如何与镇政府和医院交涉。所以我也不睡了,从床上坐起来与我爹我妈说话。我说明天你们就到政府去谈?我爹说,嗯。我说现在怎么谈呢?我妈说,我和你爹商量了一夜。现在关键是看你会不会残废。不残废事情好谈,如果残废了就不好谈。我说如果我真残废了,怎么谈呢?我妈说,你真要残废了,我们就得让政府负责你一生,包括我们两个的养老。我说,我残废又不是不能劳动,怎么能要政府负责你们两个的养老呢?我爹说我和你妈不要政府养老也行,但反正我要孙子。我说,如果我真残废了,政府哪里去给你弄孙子?我爹说。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谈。反正他们弄钱打发不行,我不要钱。由此看来这是一个死结了。如果我真不能生育了,这件事情将会变得十分棘手,不好处理,甚至无法处理。所以想了想我说,反正你们要冷静,不能和他们吵。我妈说,我们不会吵。我说,爹这副牛脾气说不清楚。我爹说,你放心,我保证不和他们吵。我和他们讲道理。
天亮后,我爹去卫生院厨房里打来早餐,我们吃过,我爹我妈就到镇政府去了。去之前他们又安慰我说,你就躺在床上不要动,也不要乱想,事情我们会处理好的。我说,嗯。我爹我妈就
走了。房间里空下来之后,我心里异常难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会不会残废,给我治疗时,医生就说过我将会残废的话。如果真残废了,我的一生将会怎样呢?我将讨不到老婆,我将孤苦一生。大约十一点多钟,我爹我妈就进来了,进来时。我发现他们的神色还算不错。从他们的神色上,我猜想交涉的结果肯定令人满意。就在我这么想时,我爹对我说,你妈留下来照护你,我下午赶回去。我说商量的结果怎么样?我爹说,一切医疗费用由医院和政府共同承担,你妈和你的误工损失也由政府负责。他们将和生产队协商,不扣我们的工分。所以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你妈留下来照顾你,我回去。我说残废了怎么办?我爹说,残不残废要到出院的时候再说,现在说为时尚早。我妈说,不管你残不残废。那个护士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听他们这样一说,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因为目前也只能这样处理。
给我治疗的就是那个冰棒医生。冰棒医生姓张。他很积极,几乎是天天来病房给我检查伤势,为我治疗。同时我还发现,那个张医生其实很和善,很热情。自从他当了我的主治医生之后,就换成了一张笑脸。不再是过去那副冷漠的面孔。治疗期间,镇里的杨书记、胡镇长、张部长和院里的周院长也很关心。他们多次到医院看望我;叫我和我妈不要愁,医院会尽全力治疗。让我们感到愤怒的,是那个李玲和她的家人一直没露过脸。这让我和我爹我妈极为不满,我妈甚至火喷喷地说,如果你真残废了,到时我们一定不会轻饶她。
三个月后,我就可以出院了。为我拆去绷带的那天很热闹。我爹、我妈,我叔、我伯,我的叔伯兄弟都来了。院里的几个主要医生,包括院长、副院长等也都来了。拆去绷带后,我们一下子全傻了。因为我那个物件残废了,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得到这个情况,怎么说我们都接受不了。我爹火喷喷地说,走,跟我到政府找干部去。这样,我们一行人就火冲冲地冲进了镇政府。
接待我们的是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给我们泡了茶后,就找来了书记杨锐、镇长胡丹和人武部长张显峰,坐下后,杨书记对张部长说,你打电话叫周院长来一下。不一会儿,周院长就来了。重新坐下后,我们王氏家族的人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当然中心意思只一个。那就是现在怎么办?政府得给一个说法。书记杨锐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好处理,责任在医院。周院长说,责任怎么在医院?李玲我们已经处理了,给了停薪一年的处罚,还留院察看二年。如果表现不好,我们就把她调到乡下的卫生所去。胡镇长说,这只能算是医疗事故。周院长说,这怎么算医疗事故?杨书记说,问题出在你们派护士做这样的检查。周院长说,我们派护士做这样的检查没错。医院的人手不够,为征兵,我们所有科室的人全抽出来了。杨书记说。不管怎么说,李玲动手打了人。周院长说,李玲动手打人那是她个人行为,要负责也只能她个人负责。我们医院怎么负责?听他们这么踢来踢去。我们忍受不了,也与镇里的干部和周院长吵了起来。我们说。你们现在踢皮球不行。我们要结果。吵到最后,周院长站起来就走,说这事我不管了。政府怎么处理,我怎么服从。说过就火冲冲地出了办公室。周院长一走,事情就僵了下来。吵了一阵后。杨书记、胡镇长和张部长只好给我们做工作。叫我们先回去。让他们慢慢来协调。杨书记说,现在的事情明摆在这里,政府只能起协调作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先回了白云荒峡谷。
可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协调就没个止境了。我们先后到政府跑了数十趟,时间过去了将近半年,政府也没给出一个结果。他们依旧踢皮球,政府把责任推给院方,院方把责任推给李玲。这样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就将院方和李玲推上了法庭,向镇法庭提交了诉状,要求他们赔我一生的损失,并要求法庭追究李玲的刑事责任。
接受我们案子的法官叫高建来。可是提交了诉状,高法官也依旧拖了半年。我们每次去问,高法官说你们再等等,我们正在调查。其实事后我们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法庭也相当为难。就在我们找了第二十一回后,法庭终于在这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把我、我爹我妈、周院长和李玲、李玲的父母召到一起进行了调解。李玲的父母我们是第一次见到,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对他们的家有所了解。他们住在峰山村。离我家三十里。李玲的父亲叫李锡东,与我爹同龄;李玲的母亲叫周文秀,与我妈同龄,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李玲有三姐妹,李玲是家中老大;她的二妹叫李娟娟,十五岁半,初中毕业后下学在家;三妹叫李姗姗,十三岁,正在念初中。家境十分贫寒,坐到一起后,高法官说,你们这件案子相当棘手。如果原告王建新继续追究的话,当事人李玲就得被判伤害罪,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判。问题是这样判也同样不能结案,原告王建新提出的是一辈子的损失赔偿,不管他们提出的数额是多大,都是合理的,法庭应该支持。问题是李玲一判刑,你们的损失赔偿就成问题了。尽管在这起事件中,医院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医院不是主要责任,绝大多数赔偿还得李玲拿出来。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法庭都很为难,这也是我们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判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希望采取庭下调解的办法把这个案子结了。我们先提个调解方案,你们商量一下,如果同意调解,这案子就结了;如果不同意。我们就只好判了。我们提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就是,原告王建新把诉状撤了,让被告李玲嫁给原告王建新。高法官一提出这个方案,我们全都傻了。高法官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能同李玲结婚?再说这样的调解方案对李玲也太残酷了吧?当然这个调解方案。医院是再高兴不过了。高法官一说完,周院长就说,这个方案好,我同意,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应该这么做,只是这个话不应该由我们说出来。但我们和李玲、李玲的父母却高兴不起来了。站在我的角度,如果不是因为这场事故,我可能无法娶到李玲这样好的老婆;毕竟她吃着国家的粮食,而我只是一个农民。问题是一旦我同意与李玲结婚,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我们更加痛苦;李玲也是。如果不出现这样的事情,说什么她也不会同意我这样的男人,因此接下来就冷场了。这样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法官问我们,你们呢?我爹说,事情太突然了,我们得商量一下。高法官说,那你们找个地方商量一下吧。这样,我和我爹我妈就走出屋子,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在走廊里,我爹问我和我妈,你们说怎么办?听我爹的口气,他显然乱了方寸,也没主意了。我妈说,你说我们那个家供得了她那么个大菩萨吗?我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我怎么能和她结婚?结了婚不仅是问题不能解决,而且我们也搞不到一起去。我爹说,那你说不结婚怎么办?不结婚你就一头也抓不住了。我爹这样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事情明摆在这里,判的结果是李玲会毁掉一生,我也将得不到什么。停了停,我妈说,那就只有同意了。我爹说,只有这样了。如果不出这个事,还找不到这样的媳妇哩。我妈说,只是这样太亏那个李玲
了。我爹又对我说,那你表个态,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我想了想说,那就同意吧。商量好走进屋子,我们就发现李玲脸上挂满了泪水。她瘦弱的身子看上去更加瘦小,显得可怜兮兮的。她的父亲母亲坐在那里像木头人一般,很显然,我们出去的这段时间里,高法官和周院长加紧做了他们的工作。重新坐下后,高法官问我爹,商量的结果怎么样?我爹说,那就同意吧。法官问李玲,你呢?李玲说,同意。这是李玲自始至终唯一说的一句话,就这么简短的两个字。法官又问李玲的父母,你们呢?李玲的爹说,同意,声音极小。就在这时,李玲却哭着跑出去了。李玲一跑出去,李玲的父母就叫了一声李玲,也跟着追了出去。他们一出去,我们一家人就傻了,尽管他们一家人都同意了,但现在看来,他们是被迫的,被迫同意的婚事,婚后的生活可想而知。卫生院的周院长倒是欢天喜地的。他们一出去,他就站起来对高法官说,没我的事了,我可以走了?高法官冲着他点点头。周院长就走了。周院长刚一走出屋子,高法官又对我们一家人说,你们也走吧。我爹说,人都跑了,我们怎么能走呢?高法官说,你们都听见了,他们一家都同意。但这件事对他们来讲太突然,总得给人家一个过程嘛。我们再没说什么,站起来走了。
只是从离开法庭的那一刻起,我们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都认为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完了,只能自认倒霉了。我妈说,先晓得是这个情况,该不同意的,如果李玲不同意这场婚事,我们就是鸡飞蛋打了。我爹说。那你说怎么办?事情是我们一起定的,现在倒怨起我来了。我妈说,我没怨你,我说的是实话嘛。我爹说,不会鸡飞蛋打,是他们亲口答应的。他们要不同意,我就找他们去。我说,不同意你有什么找头。我爹说,那你什么意思?难道就这么算了?我说,反正我们不能逼人家。我妈说,建新说的对,我们就等吧。
没想等了一个月后,李玲竟然提着礼品独自找上我们家来了,她来的这天,我们一家人正好在家里。因为到了腊月,队里放假让我们在家里忙年。李玲在我们家门口出现时,我们一家人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她却显得落落大方,冲着我爹叫了一声大伯,冲着我妈叫了声大妈。又冲着我叫了声建新,然后才说,我来看你们了。这个时候,我妈先反应过来,她说快屋里坐,说着就接过了她手里的礼品。今天的李玲上身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下身穿了一条黑色的长裤,这样的打扮使她显得更加漂亮。她一进来。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屋子也亮堂了不少。只是她的到来,除了让我们感到意外之外,还让我们心里感到忐忑不安。把她迎进火垅,给她找了椅子。倒了茶之后,李玲说,我今天是专门来认门的。从此以后这儿就是我的家了。每次放假我就回这儿来。她的嗓音甜甜的,语气坚定有力,丝毫没有勉强的意思。同时从她的语气看,她俨然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我妈说,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一定要想好。我们丝毫没有勉强你的意思。我爹说,虽然建新残废了,但我们的本意也并不是要你嫁给她,这对你不公平。李玲说,我想好了,我爹我妈也同意,再说这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我妈说,你是吃国家饭的,建新是农民。你们怎么说也不般配。李玲说,农民怎么啦?我爹我妈也是农民。正说到这里,屋外拥进一大群人,就把我们的话打断了。因为李玲的出现就像一颗新星在村里升起一样,村里的七姑八嫂都潮水般地涌到我们家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把李玲看了又看,评了又评,说了许多羡慕的话。而乡亲们一到来,我爹我妈也踏实了下来,忙得屁颠屁颠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倒是我还一直忐忑不安的。因为我知道,刚才我爹我妈的那些话都不是真心话,如果时间拖长了李玲还不上家来,他们也会去找她。若是李玲反悔不同意了,他们还会继续告她。当然我爹我妈这样做,这样想也没有错,可是这样做了,我觉得对李玲来讲太残酷了,她跟着我将会毁掉她一生的幸福。我一个农民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幸福,可是我也矛盾,如果我不同意,不仅我爹我妈那里通不过,而且我的一生也就全完了。所以出来抱柴的时候,我望着对面的山想,走一步看一步吧。
李玲这次上家来玩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我一直把她送到了镇卫生院。尽管路上,李玲一直不要我送,说了好多次叫我回去,但我还是一直把她送到了家。路上,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话也说得很少。一般是她问一句,我答一句。她问我,你怎么没有考上大学呢?我说,我们那一届的考生多,录取的比例小,我差三分。李玲说,你为什么不复读呢?我说,当农民也一样,坐轿子要人,抬轿子也要人。李玲说,你就打算在你们村里搞一辈子?我说,嗯。本来我想说,我原来是打算通过考兵这条路出去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送到能看见集镇了,我说,你慢些走,我回去了。李玲说,送到这里了怎么回去?我说,我回去还有事。李玲说,哎呀。都走了半天要吃中饭了。到我那里吃了中饭再回去。说过她上来拉了我一把,我就只好跟着她去了她的宿舍。进了她的宿舍,我才发现她的屋子很小,只有一个单间,屋里的摆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床和简单的一些家具,不过屋子收拾得很整洁。坐下后,她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下楼到厨房里看看,看过回来,说厨房的饭早过了,便用煤油炉给我煮饭。其实所谓的煮饭,只是煮了一碗面条,吃过,我就走了,走的时候,她把我送到了门口,说,慢些走。我说嗯。相互间冷静得不像恋人。
回来的路上,我想了许许多多:我觉得我不能同意这门亲事。这对李玲太不公平了;她有属于她的幸福。我不能毁了她的幸福。所以回家之后,我与我爹我妈发生了很大的争执。我说,这门亲事我们不能同意。我妈说,为什么?我说,这不明摆着吗?我同意这门亲事,就毁了她一生。我爹说,你说个屁!你说为这事掏了多大的力?我说,掏了再大的力也不能同意。我妈说,事情到了这一步,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说我这样想是应该的。我爹说,那你就没替自己想想,没替我们想想?你以为你长这么大是白长大的?我说,反正我不同意。我爹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我妈说,你不同意我们同意。因为你一生的幸福是她毁掉的。由此看来。我爹我妈是想好了,意见统一了,这门亲事他们是打定主意同意的。因为我作为男人只是一个摆设了。我不能让李玲生育。我爹我妈也就没有盼孙子的指望,所以他们现在把指望放在多一个媳妇身上。
过年的时候,李玲又来了一次。走的时候,我爹我妈让我去送她。我妈说,你把她送到家,去见见她的父母。我说,我才懒得送呢。说过,我就提前躲到别人家打牌去了。第二天开年就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完山林和土地的那天。李玲又来了。这一次来,她一进门就改了口,管我爹叫爹,不再叫大伯;管我妈叫妈,不再叫大妈。而且从这次起,她就改变了角色,以一个媳妇的身份操持起了家务。李玲这样做,我爹我妈自然高兴。尤其是我妈,高兴得热泪盈眶。就好像她是她的女儿似的,在一
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是她们越这样。我心里就越受刺激。这次送李玲时,我把她送出二里多地,走到一个叫大岩湾的地方时,我对李玲说,李玲你坐下来,我想和你认真谈谈。李玲说,谈什么?我说,你坐下来。李玲和我在一个石包上坐下后,我说,今后你别来了。李玲说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我不同意这门亲事。李玲说,你不同意这门亲事?你嫌我?我说不是。我不能毁了你的一生。李玲没有说话,我站起来就往回走了。
但是谈过这话只过了两个多月,李玲又来了,而且这次来,她给我们一家人都买了新衣服。见到她我就有些火了,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李玲没有回话,倒是我妈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说,我给她说了,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听我这么一说,我妈说不出话。我爹则狠狠地剜我一眼,就去外面忙他的事去了。我爹一走,我妈也显得极不好意思。她说,我到灶屋里弄饭,你们俩说说话,说过她就走了。我妈一走,火垅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我们便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可以看出,李玲没有生气。沉默了一会儿,李玲说,你能这样想,我很感激你。我说,既然这样,你还来干什么呢?李玲说,回家之后我也认真想过,人不能没有良心,你的一生幸福是我毁掉的,我即使是嫁给你也不可能让你幸福。所以你不让我嫁给你,我就偏要嫁给你。我没想到李玲会这么说,这么想。我想让她得到幸福,她却想让我得到幸福。所以想了想我又说,你不要这么想,我们之间没有爱,你得找一个爱你的人。李玲说,我是不爱你,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李玲说,我就这样了。说过,她就到那边灶屋里帮我妈做饭去了,这样,我们的谈话又僵持了下来。
吃饭的时候,我爹说,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我们就把话亮开了说。我和建新他妈的观点是统一的,我们只有他这么一个孩子。李玲打断我爹的话说,爹你不用说了,我都改口了,是下了决心的。我妈说,其实我们心里很矛盾。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人道。李玲说,妈你也别说了,吃饭。这样,事情就拖了下来。
没想这样拖了几年,我对李玲产生感情了。李玲不来的日子里,我吃不香,睡不着,只得找个借口去镇上看看李玲。去了李玲的单位。李玲也显得很热情,若是手头有事。她就立刻放下把我迎进屋。而且我一去,她就不再去食堂吃饭。而是用煤油炉烧出简单的饭菜。李玲说,建新,我们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去见见我的爹妈呢?我说,你说我怎么有脸去见他们呢?李玲说什么有脸没脸的?你不去他们有老大的意见了。我说,那好吧,我们选择个时间去见见。李玲说,什么选择时间?要去现在就去。我说。你单位能脱身?李玲说,我请个假。这样,我就去街上买了一些礼品,跟着她去了峰山村她的家。
李玲的父母很热情。看得出来,李玲在这之前做过她父母的工作。他们是接受我这个女婿的。李玲的母亲还说,你怎么不早点来。拖这么长时间呢?我说,穷忙。李玲的父亲说,今后就常来。我说,那是。也不管他们这种接受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但他们能接受也让我心里很踏实。李玲的两个妹妹也很喜欢我。起初她们见到我时还显得有些害羞,但熟悉之后,她们则成了人来疯。尤其是小妹,熟悉之后,她竟然爬到我身上来了。她坐在我腿上说,哥,你要是欺负我姐,我就不饶你。我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我哪敢欺负你姐呀。李玲的父亲出屋时正好看见她坐在我腿上,就吵她,说你爬到哥身上做甚事?小妹吐了一下舌头,从我身上下来。这一次,我在李玲家玩了两天,帮他们干了一天活。走的时候,我对她的两个妹妹说,放假了就到我那儿玩去。她妹妹说,那是肯定的。这样出屋走了一程,李玲就说,你怎么不改口?李玲的意思我明白,她不满意我管她的爹叫大叔,管她的妈叫大婶。我说,第一次见面不好改口,下次一定改。
假期里,李玲的两个妹妹也开始到我家走动了。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两家之间就成了最亲的亲人。这个期间,李玲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她的个子长高了,身子丰满了,该凸的地方凸了出来,该瘦的地方瘦了下去,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而且她也越来越大胆。有一次,她竟然一下子抱住我,吻了我。可是李玲越这样,我的心里就越疼,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也越来越恐慌。冷静下来一想,我真能同她结婚吗?不说良不良心的问题,损不损失的问题,幸不幸福的问题,一些最现实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呀。至少我们不能睡在一起,至少我们婚后不会有孩子。如果没有孩子,我们即使是结了婚,这婚姻又能维持多久呢?可是在这个期间提出不结婚,我又怎么面对这一群人呢?至少我爹我妈都幸福得要死了,李玲的父母也是很乐意,她的两个妹妹也是那样认可我,如果我提出不同意,他们会善罢甘休?但经过彻夜的思考,在即将要办理结婚登记之前,我还是痛下决心,不与李玲结婚。想通之后,我就找李玲谈了一次,我说李玲,我想好了,我们这婚不能结。李玲说,你说什么?我说,我们不能结婚。李玲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们都处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说,但愿我没有耽误你。李玲说,你耽误我了。我说,耽误了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说对不起。李玲上来揍了我几下说,不行,你不能说不结就不结,我现在爱上你了。我说,我也爱你,非常非常爱你,可是爱也不能结婚。李玲说,为什么爱也不能结婚?我说,我这样,即使结了婚,婚姻也不会长久。李玲说,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说过,她气跑了。
但不管怎么说,我的主意现在不能改了。气跑李玲后。我要做的就是我爹我妈的工作。并让他们也去做通李玲父母的工作,希望他们也同意。我们两家之间可以像亲人一样往来。但我就是不能同李玲结婚。在做我爹我妈的工作时遇到了麻烦,我妈一听就哭了起来,说你这个孩子太让我们操心了。你现在怎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爹则更火,他火喷喷地说,你这个逆子!老子今天打死你!说着他就去找木棒。我说,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同她结婚。我妈一见要出事。赶紧拦住我爹叫我跑。我当然没有跑,我说,你们要不同意。我就去死!我爹满脸涨红地说,你去死吧!我爹这样一说,我就真去死了。我在阶沿上拿了一条钩绳,到屋旁的板栗树上系好。就准备上吊。我妈一见吓坏了,哭喊着向我跑来,说,建新,我的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呀?说过又喊我爹,说,快,你赶紧把他弄下来啊!我的孩子!我爹终于软了,把我从树上取了下来。而我爹我妈这一哭喊,周围的乡亲也都拥了来。我爹流着泪说,建新,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说,爹,我们不能害人家,你们得同意。我爹说,我们同意,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你怎么决定怎么好。我说,你和妈得去做做李玲爹妈的工作,叫他们要理解。我妈说,我们去,我们去。这样,我爹我妈的工作终于做通了。
第二天,我爹我妈就去做李玲父母的工作。他们天一麻麻亮就出发,很晚的时候才回家。回家后,我问他们,做得怎么样?我爹说,不怎么样,自始至终就你妈和她妈抱在一起痛哭
了一场。我妈说,他们的意思和我们一样,你们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我们当大人的不掺和了。听了这话,我“扑哧”笑出声,说,这不就结了。从此之后,我心里就放心了,我当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么些年过去,我们村通了公路,通了电灯,通了电话,安上了自来水;我也包了一大片果园。我想我一辈子婚姻是没指望了,那我就在事业上努点力吧。
可是一个月之后,李玲来了。李玲这次来我没有理她,她刚一露脸,我就跑到我的果园里躲起来了。躲起来之后,李玲也没有来找我。我干到天黑后回到家,李玲也就走了。进屋后我问我妈,李玲来说了些什么?她是不是同意了?我妈说,同意什么?她是来取证件的。一听这话我就急了,取证件的?取什么证件?我妈说。你的身份证,结婚证明。我说,我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明?你们给她了?我妈说,身份证是我给她的,结婚证明是你爹去村里办的。我说哎呀,你们这不是糊涂吗?你们怎么能给她办呢?不行,我得去追回来,说过我就要走。我妈却一下子扯住我说,你不能去。我说不去不行。我妈见扯不住我。就大声喊我爹。我爹从外面进来弄清了事情真相后,就把门关上了。关上后,他们又把我推进我的卧室,我爹一边推一边说,你去我们不拦你,但今天去不行。今天天黑了,要去明天去。然后。他们就在我门口守了下来,守了整整一夜。因为出了那事后,他们就怕我寻死觅活的,所以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不敢再硬了。我呢,坐到半夜的时候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我就去找了李玲,李玲正好在她的宿舍。一见面我就没好气地说,李玲,你怎么能这样做?李玲不说话,直笑。我说,你把证件给我。李玲说,行,给你。说过,她就从箱子里取出了证件。可是把证件递上来后,我就傻眼了,因为递上来的并不是我的身份证和结婚证明,而是结婚证书,我气得把结婚证往地上一扔,说,你……然后我就气冲冲地走了。
回到家,我爹我妈很快就围了上来。我妈问,怎么样?证件拿回来了?我说拿个屁,她把结婚证都办了。一听这话,我爹我妈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们是同意这门亲事的,现在结婚证都办妥了,显然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之后,我在家里气了两天也就不再气了,因为现在生米做成熟饭,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李玲嫁给我,说什么也不能太亏了人家。所以气醒过后,我就同我爹我妈商量了如何操办这场婚事。我爹说,我和你妈商量过了。还是热热闹闹地办几桌酒席。我说办什么酒席。给她买几套新衣。另外把新房布置一下就算了。我妈说,这样做是不是亏了李玲?我说,她要觉得太亏,那也是她自己找的。因为在我心里,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到底能维持多久,如果结婚太张扬,到时婚姻不能维持下去,我就觉得这人丢大了。我爹说,那也行。然后,我们一家请了泥瓦匠把大瓦房重新粉刷了一遍,把我们的新房装修一新;衣服给李玲买了好几套。一切忙妥当,我爹说,你和人家闹意见,现在得你去把人家请回来呀。我说我不请。我爹说,不请也行。那就去村里给她打个电话。我说,电话我也不打。我妈说,我去请。然后,她就赶车去了镇上。
当天下午,我妈就把李玲接了回来。李玲见到我时,调皮地笑了一下。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而我妈一进屋就开始忙碌起来。她让爹去请我们王氏家族的亲戚,说不整酒席可以,但几个亲戚还是要请来坐一坐,我的大伯小叔、叔伯兄弟姐妹是晚上到的。而他们一来就放鞭放炮。这样又惊动了其他乡亲。大家都拥来,流水席坐了一桌又一桌。准备的大米、蔬菜不够,又现到商店里去买,这样一直闹到深夜时分,大家才离去。所以我们的婚事也等于办了喜酒,只是省去了拜堂入洞房一些环节。大家走后,我和李玲就进入了我们的新房。也直到进入新房后,我们都才意识到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横在我们的面前。这样我们坐了许久,说了许多话。直到李玲困得不行了,才催我说,睡吧。我说,你先睡吧。李玲就先睡了。到后半夜,我也困了,也在另一头睡了下来。新婚的第一夜,我们就像两具僵尸一样硬挺了一夜。这次婚期,医院给了李玲半个月假,之后的几夜,我们依旧是这样硬挺着过来,再后来,我们则是相拥着默默地流泪:直到累了,才相互为对方擦去泪痕睡去。
假期结束的时候,我爹我妈同我们商量了一件事。我爹对我说,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集镇上给你开个水果店。我妈解释说,你们结了婚,你搬到镇上后也便于照顾李玲。我说,果园呢?我爹说,果园我和你妈来管。我说你们管得了吗?我爹说没什么管不了的。你要是不放心,镇上离家也不远,搭个车回来也就个把小时。你回来指导一下,具体怎么操作的,我和你妈来做。李玲说我看这办法行。我想了想说,那就开吧。我们说干就干,立刻到镇上租门面,进货,也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门面开了起来。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到镇上开水果店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首先是我受不了那些刺激,最初的刺激是给医生们送喜糖,本来我们讲好不办喜事的,但李玲上班后,还是接受了医生们送的礼钱,那些礼钱分别为50元、100元不等。也是断断续续地送到李玲手里的,有时碰上了,想起她结了婚,就顺手给了她。今日这家,明日那家:而收了礼,李玲则必须告诉我一声。说今天又收了谁谁的礼了,说过了就又和我商量,说这事我们不能被动了,干脆一人送一包喜糖去,本来我心里不愿意,但我又不得不同意。我说,那就送吧。这样,我和李玲就到商店里买了喜糖。在家里一包包封好,每包12颗。然后挨家挨户去送。送了喜糖回来,我心里就有气了,因为那些医生们看我的眼神不对。他们接过喜糖时,一边对着李玲说着恭喜之类的话,一边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这样我就感到更加自卑了,如果是单单这样倒也罢了,问题是接下来他们医院一有喜事。李玲就得拉上我出场。而在酒席场上,他们只来给李玲敬酒,从来都不给我敬,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所以每一次,我就如坐针毡一般,饭一结束我就慌不择路地跑了,当然这些我也不计较。毕竟我是一个农民,人家是医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与他们不在同一个等次上,自然无法搭上话。让我无法容忍的,则是他们当着我的面“调戏”李玲。医院的医生们有个习惯,平时无事的时候喜欢站在大门外闲聊。穿着白大褂的他们,把手装在两边的口袋里,门边站着一群人,东家长西家短地神侃,或是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攻击。这样,每一次回到医院的那个家时,只要是远远地看见我一露面,他们就故意大声问李玲,说,唉李玲,你告诉我们实话,你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你是不是处女?别看那些医生是读过书的人,其实他们也是一肚子坏水。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他们说,你们这样子晚上怎么睡呢?他们说。你男人不能满足你,你想不想呢?他们还说,你们这样空对空没意思,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如偷个人算了。这些话尽管是对着李玲说的,但如同刀子一样割在我的心上。当然李玲还好;别人这么说时,她要么是骂上几句,或是哈
哈笑过就连忙走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对李玲说,李玲,我不想在这里住了。李玲说,你不在这里住到哪里住?我说我到店里去。李玲说,到店里住什么?店里连张床都摆不下。说过了,她突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又说,你是不是听了别人的那些话受不了了?我没有做声。李玲说,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又不能堵住别人的嘴。他们要说随他们说去,我们不听就是。李玲说的也是,因为这些刺激都是来自于外人。李玲并没有刺激我。这样,我还是听了李玲的,没有急于搬出去,最让我受不了的,则是我们天天厮守在一起,曾经有过的一点感情慢慢地就淡化了。当然李玲没有反常的举动,她每天依旧按部就班地上班,闲下来的时候也到我的店里帮帮我。尤其是我到县里进水果,或是回家指导我爹我妈管理果园时,店里的事情全是她照料的。而且从收入上来讲,我店里的收入比她那点可怜的工资可观得多,为此她在我们镇上是穿得最好的女人。她结婚后,医院为她调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那房子的装修全是我拿的钱,也是全医院中装修得最漂亮的房子之一。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我们的感情淡化。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不再相拥而眠。过去说不完的话似乎全部说完,我们在一起时再也找不到任何共同语言。我们就像机械人一样,重复着一日三餐,过着三餐一日的日子。这件事情最让我害怕,也让我毫无办法。我内心明白,这样的日子一长,我们的婚姻必定会出现问题。
当然我们这些变化,没有逃过我妈的眼睛。我妈是细心人,每次回家见到我们这样。我妈也很着急。有一天,她突然给我们出主意说,建新,李玲,你们这样不是个办法。李玲一下子没懂我妈的意思,李玲说,什么不是办法?我妈说,你们得有一个孩子。李玲笑了一下说,妈你这不是说傻话吗?我们怎么有孩子?我妈说,我是说你们得想法抱养一个孩子。李玲说,我也是觉得我们两口子的生活中少了点什么。但我妈的这个建议丝毫没有激起我的兴奋。我说抱养个什么孩子?我觉得我们这样挺好。李玲则来劲了,她说,抱养一个。我说我不养。李玲说你不养我养,这事不要你操心,我来找。这样,从那天起,李玲就像着了魔一样到处托人给她找孩子,她找同事,找镇计生办,给她的同学都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嘱咐说,除了缺胳膊少腿,有先天性疾病的不要以外,其他的都要。她的同学说,你办托儿所呀?李玲就格格笑起来,说,普遍撒网,再挑合适的嘛。看着她如此忙活,如此快乐,又一次次不顾辛劳地奔跑,我的自尊心就一次次受到了伤害。但受到伤害我也毫无办法,我只得把这种伤害隐藏起来,看她到底怎么折腾。因为我知道,即使是抱养一个孩子,我们的婚姻也不可能长久。我们的婚姻里隐藏着一颗炸弹,这个炸弹就是我们没有性爱。而这个和物质基础一样,也是婚姻的基础之一。缺乏了总有一天它会爆发的。而且它与道德无关,人有七情六欲,作为活生生的李玲,总有一天她不会孤守下去。
这样过了半年,李玲抱养孩子的事就成了泡影。尽管她撒了大网,但这网收上来却是连虾米也没有,虾米都没捞着,李玲的激情之火就熄灭了;激情之火一熄灭,她也就像失去了魂一样,一下子没有了精神气。不仅是每天吃得少,睡得少,而且脸上再也看不到任何笑容。身子也日渐消瘦了下去。和她上街,她也变得恍恍惚惚的,见了别人家的孩子,她就像猫见到了老鼠,直愣愣地望着别人家的孩子不转弯,就好像是别人抢了她的孩子似的。见她这样,我吓坏了。我说李玲,你这是干什么呀?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你这样下去会得病的。李玲说你不要管我。我说,我不管能行吗?李玲说,你管得了吗?李玲这样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是呀,我怎么管得了呢。她不是想要一个孩子吗,可是我能给她吗?我给不了。这样,我就不管她了。她想怎么样就让她怎么样去。同时我也下定了决心,想法同她离婚。因为她的痛苦是我带给她的,只有离开我,她才能找到属于她的幸福生活。我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能让她毁在我的手里,可是在如何离婚的问题上,又让我相当为难。我知道她是不会同意离的,如果不讲究策略,只会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所以我想看一段时间再说,至少得等她想孩子的心思淡了再和她谈这事。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李玲想孩子的心思果真就淡了许多,她又像以前一样快活了,脸上有了笑容。自从听到她的笑声,我的心里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一天,我对李玲说,李玲。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顿饭吧。李玲说,出去吃什么饭?就在家里吃。我说,我有话要对你说。李玲笑了一下说,有话不能在家里说吗?我说,晚上八点,我们在幺姑旅社见面,不见不散。晚上八点钟,李玲还是如约来了。我点了一桌子菜。李玲说,你搞什么名堂?搞这么丰盛?我说,你坐下我们慢慢吃慢慢说。李玲坐下后,我与李玲举杯喝了酒。李玲说,什么事你说吧?我说李玲,感谢你。李玲说,感谢我?感谢我什么呀?我说,感谢你给了我这么一段幸福的生活。李玲说,建新你怎么搞的?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直说。我说李玲,我们离婚吧。我们好说好散。李玲说,你把我请来就为说这事?我说就为说这事。李玲说,告诉你,不行。说过她就跑了。
这是我预料之中的。李玲不同意离,我只得再找机会。只是从这天起我就再不回医院那个家了,而是在水果店里住了下来。住下来后,李玲也与我赌了气,不再来店里看我帮我了。只是住下来后,我惹来了一些闲言碎语。街上的那些商店老板无事就取笑我说,建新,你住到这里干什么?你给别人腾地呀?当然对这些玩笑话,我没有当真,一笑就过去了,但有些话我还是当真了。有好朋友对我说,建新,你得回家去看看。我说,看什么?朋友说,你老婆和别人好上了。我笑了一下说,和谁好上了?因为这是我巴不得的事。那朋友不说那男人的名字,只是说,反正是好上了,不信你可以回去打听打听。这天,我以回家洗铺盖为由回了一趟医院。回家之后,我发现一个叫张炫的医生坐在我家里。李玲在厨房里弄饭。我说,家里有客人啦?张炫则站起来就走,走的时候,他冲着那边厨房说,李玲,我再找你来借。李玲没有回话,张炫就走了。张炫走后,李玲随即出来对我说,你还晓得回来呀?我说,我的铺盖脏了,得用洗衣机洗一洗。李玲没说话,又进厨房做饭去了。我则打开洗衣机忙碌起来,忙着的时候。我在想,朋友说的是不是这个张炫呢?张炫是个单身汉,门诊部内一科医生,人长得还说得过去。如果真是张炫在追她,那我也就放心了。正这样想的时候,李玲过来问我,你在家里吃不吃?我想了想说,吃吧。坐上桌子吃饭的时候,李玲说,张炫来找我借本书。我说噢。吃完饭,洗过铺盖,我就又回到了那边店里。之后,我又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张炫果真在追李玲。他有事无事老往李玲的科室跑,一泡就是一整天,晚上也老去串门。有一天,我爹请人带信来,要我回去指导一下果园的事,得到信后。我就去医院请李玲到店里来照顾店。没想来到她的科室,
发现科室里就她和张炫两人。他们面对面坐着,张炫紧紧地抓住李玲的手,正在含情脉脉地表达着什么。我一来,他们的手就立刻松开了。随即,李玲就镇静下来。对我说你怎么来了?张炫则闹了个大红脸,赶紧站起来望了我一眼,再望了我一眼,又望了我一眼,就走了。张炫走后,我说。我得回家一趟。李玲说,嗯。
回家给我爹我妈指导了一下果园的事,再回到镇上我就干了一件大事,把我的水果店迁到了夷城。迁走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是悄悄迁走的。迁到夷城后,我就给李玲打了电话。我说李玲,我们离婚吧。李玲说,王建新你怎么搞的?你搬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搬到了夷城。李玲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说一声?我说,我们离婚吧。李玲没再说话,“啪”的一声就将电话挂了。当天下午,李玲就找到了我的水果店。一见到我,她就大吵大闹,把我的水果掀得到处都是。我说李玲,你冷静一下,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张炫那么喜欢你,你们是非常好的一对。李玲说,你放屁!是张炫死皮赖脸地追我,我没有同意。我说,你应该同意,你应该有属于你的幸福。而这些我都不可能带给你。李玲说,你不要说了,我不会同意。我说,你要不同意,我就请法院判决。李玲说,你休想!上法院我也不同意。说过这话,李玲就走了。李玲走后,我还是向县法院递了离婚请求。三个月后,法院就作出了离婚判决。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李玲没有理我,走了。
离婚后,我把所有心思全部用到了经营上。我先后在几个乡镇开了分店,经营品种由原来单一的水果扩展到日用商品。之后,我又到几个城市开了超市,生意越做越大了。李玲与我离婚之后,也很快与张炫结了婚。婚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儿子,据说取名叫张明明。听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因为我觉得我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我爱李玲,爱一个人就要给她幸福。李玲获得幸福也就是我的幸福。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讲,人生只有一次,获得幸福该多么重要呀。因为生意越做越大。我就把根据地又从夷城迁到了夷陵市。迁到夷陵市不久,我又变卖了白云荒峡谷老家的家产,转包了果园、土地和山林,把我爹我妈也接到了夷陵。我爹我妈接到夷陵只过了两天,李玲就带着她不到一岁的儿子找到了我。见到她的那一刻,我惊呆了。李玲说,你还要不要我?我说你这是怎么啦?李玲说,我和张炫离了婚,也辞了职。我说,你离了婚?辞了职?李玲说,是我要求离的。我说,你怎么能离呢?李玲说,想去想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只有你对我最好。我说,你坐,坐呀。说过我扭头望了一眼店外,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阳光已走进了我的店里。因为阳光反射。我的店里更加亮堂。站在阳光剪影里的李玲也显得更加清晰和美丽。
责任编辑张曦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