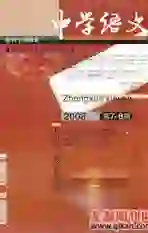新课改是否可以从取消《考试大纲》开始
2008-10-10杨智慧
杨智慧
21年前,自己还是一名懵懵懂懂的高中毕业生,高考时,一道选择与“梨花院落溶溶月”组成对偶下句的客观题难住了我。当时我们这些农村学生对这诗的上下句都还很陌生,无法靠记忆来解决。我调用了语境和句法结构两个思维点去思考,结果一出来,发现自己还是选择错了。现在来看这道题,觉得是很容易从平仄格律去判断的。
细细想来,很是奇怪,老师为什么高考复习时忘记讲这方面的知识了呢?难道他不知道这个考点会在高考中出现?难道那个年代没有《考试大纲》或者《考试大纲》没有现在这样的准确、具体?我问过那个年代教高三的教师,大多含糊其辞,我到网上搜索信息,还是找不到那个年代《考试大纲》的影子。
可是,我们现在的高考,透明度是相当高的,高的让我们有些厌倦了。每年3月份的《考试大纲》都成了教师和考生追逐的对象,尽管有时候只更改几个字,也让教师们“研究”地头头是道。至于高考题型和知识点,更是烂熟于胸,即使有个别变化,也早下“通牒”了!第一题字音,第二题字形……一直到最后的作文题,师生们都了如指掌,大家都准确地握着高考的方向盘前进,如果稍微有点更换就成为高考议论的热点了,这就是目前高考以及应考的现状。
于是,大同小异切合高考的复习资料漫天飞舞了,着眼高考的同步辅导和训练从高一甚至小学就起航了;教师们的《课程标准》束之高阁,仅留每年不断更新的《考试大纲》;出版商们跟上高考步伐忙活了这套书,又开始策划那套书;学生们做完了这套题,又开始做那套题……结果,忙坏了教师,发肿了出版商,累死了学生。
我总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语文,也不是我们希望的语文教育。有时候,我突发奇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语文高考,也不再编写《考试大纲》,让它真正回归到《课程标准》上来呢?
本来,《考试大纲》是引领考试的风向标,对考试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随着《考试大纲》的不断升温,已慢慢开始有违初衷了。现在我们的《考试大纲》,对每年高考的指引作用太僵化、太细微了,就连考试的题型和知识点都一目了然,且很少有变化,考试题目也形成了僵化的形式。考点以外的知识和考题以外的训练一般从高一开始就无人问津了。
以《课程标准》为依托的新课改,给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私下里都清楚得很:只要《考试大纲》存在,语文教与学的模式化空间和机械化操作就永远可能是新课改无法治愈的硬伤。
目前,人们探究的还是新课改以后《考试大纲》的知识点及题型,而不是《课程标准》的丰富内涵。有了《考试大纲》的新课改,即使《课程标准》出台多年,人们也还是显得无所适从,都在两眼望“大纲”地摸索,不敢越雷池半步。在这种状况下,各地新课程高考的《考试大纲》和试卷还是在纷纷抢夺师生们的眼球,各类新课改研讨会、观摩会的背后透过的还是漠然的目光,内容丰富的多模块教学中打理最多的还是必修课;在这种状况下,新课程的理念还是难以深入人心,语文素养还是空中楼阁,与《考试大纲》无关的知识和能力,还是很少有人去理会,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
我不由得想到了1997年“误尽苍生是语文”大讨论后的沉寂,想到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阵后的低沉,想到了研究性学习的悲惨结局,于是,我对新一场课程改革又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了。
其实,语文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学科,“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早已成共识。在这种前提下,语文考试只要关注的是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知识点和题型就可以留下一些可供开发和选择的空间,也就可以来点出乎师生们意料的突然袭击。我想,这样灵活的高考对于考生的选拔来说是公平而合理的,对于语文视野的开拓来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新课程改革的力度更是有促进作用的,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既然如此,何必每年的高考,都要在《考试大纲》的指引下变得比八股文还八股呢?
我在《名家谈语文学习》一书里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这些著名学者、专家在回忆自己学习语文的往事时,最难忘的还是那些语文教师的个性,而这些老师的个性不仅表现在教学方法上,更多的表现在不拘一格的教学内容上。解放前后的高考指挥棒作用是不明显的,各高校自主命题,语文教学有天马行空的自由,这些教师们都没有被《考试大纲》绑着手脚地做“题海战术”,而是真正领着学生在语文素养的天空中恣意漫游,语文的高素质人才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当然,人们习惯《考试大纲》已经太久太久了,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还真不容易。我想,如果现在还有存在的必要,也不必让考点、分值、题型等等透明得一览无余,更不必把每年的高考试卷制作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子。
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有一天《考试大纲》成为历史名词,让语文新课改能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让语文高考也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真正的语文素养能在高考中过关斩将,让语文能回归到自然的本色!
[作者通联: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