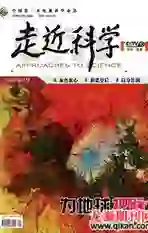最后的冲刺——一个博物馆和一座城市
2008-09-05探索·发现
探索·发现
寄居在孔庙的北京历史文物,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将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然而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建设随着工程的快速进展,建设者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
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杜迪阳设计的青铜椭圆桶,那个赢得喝彩的创意在施工过程中却遇到了空前的麻烦和挑战。
施工方几乎所有的技术骨干都被调到了这个施工现场,每绑扎一根钢筋都要进行精确计算。这个椭圆形的斜桶,从建筑专业的角度来讲最大的难度就是每一层钢筋绑扎后,都要校正偏差(图1)。

(1)新首博建设施工现场
为防止浇铸后出现问题,施工单位做了他们从未做过的试验——按1比1浇铸了一块模型。
当这座庞大的建筑到了即将封顶的时候,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随之而来:这个巨大的屋顶面积近15000平方米,它的北侧,即面对广场的位置还要伸出一个22米长的宽大挑檐,这样大的跨度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保证。
历史上曾经有过可怕的结局,上海有一座建筑的长挑檐屋顶,在一场特大暴风骤雨中被掀掉,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如何保证新首博宽大挑檐的安全,使得决策者们不愿意仅仅相信建筑结构设计师的计算。
在这之前,浙江大学力学研究所的专家已经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和测试过所有的数据,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首都博物馆业主委员会还是决定再委托北京大学对新馆结构的安全性进行风洞实验。
首都博物馆模型上数不清的导管连接着一个个微小的压力传感器,通过它将模型的每一个受风面上各点承受的压力传入计算机,进行综合数据统计。
在大型低速风洞中,他们模拟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周围的建筑环境,确保风洞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北大向首博业主委员会提供了380多页风洞实验报告,实验结果证明了设计是安全可靠的(图2)。

(2)风洞实验结果犹如给建设者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法国设计师杜迪阳的设计中,“新首博”外墙壁所用的木材、石材均需要从国外进口,价格极高。难道在中国就找不到与“新首博”建筑整体艺术气息相吻合的材料吗?
“新首博”的外墙除了用榆木外,最终选用了出自中国北方的石材“蒙古黑”,经过打磨,十分理想地再现了老北京城墙固有的色调(图3)。

(3)使用本地建材既保证了质量,还节省了经费
一座博物馆外在的形态毕竟只是一种符号,它的内核,即向观众展示什么和如何展示,才是骨子里的东西。
新首都博物馆应该如何定位呢?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悬念——因为世界上能够延绵3000多年,既有文字记载又有出土文物佐证的城市只有北京。
所有的专家一致认为:首博新馆的基本陈列应该定为北京通史。
基本陈列是一个博物馆展览陈列中的重中之重,根据专家的喜好来定位基本陈列,是长期以来博物馆界的一个惯例。
编写新首博展陈大纲的人们认为,这次展陈大纲内容不作为最终的定论,将来随时根据观众的意见进行调整。
展陈设计师肩负的责任,是要把那份以历史线条形成的几十万字的展陈大纲,用一种合理的展陈形式体现出来。首博业委会决定,“新首博”的所有展陈设计均向国内外著名设计公司公开招标。
一个博物馆的展陈形式设计公开招标,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这次方案征集共收到国内外18个设计单位参赛的44个方案。经过初审和复审,最后北京通史、北京民俗、精品展览、临时展览成为入选方案。
国际著名的美国纽约RAA展示规划设计公司,因曾经承担设计了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而名噪一时。他们带来的北京通史的展陈设计理念让人耳目一新。在布展方案中,他们把展线划分为内圈和外圈,内圈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外圈展示“世界文明概览”(图4)。


(4)图组:独特的内外圈展陈设计让人耳目一新(4-1)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展品;(4-2)展示世界文明的展品
内圈和外圈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展陈形式,和一般设计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过分突出自我,而是站在观众的立场上融入了“人性化”的设计思路。
他们的设计得到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可。
?当“新首博”的展陈大纲和形式最终定稿时,“新首博”的内部装饰工程已经开始,那个巨大的青铜圆形展厅的外装饰面将使用青铜板材。
按照设计要求,在这些青铜板材上要雕刻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纹饰(图5)。

(5)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典型纹饰举世无双
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被欧洲的艺术大师们誉为中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今天的设计师对古代青铜器的了解和领悟却少得可怜。
就在人们为了博物馆这个青铜鼎的纹饰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馆长韩永突然想起他的一个朋友,一个生活在北京郊区以铸造青铜艺术品为生的工匠王德龙。
王德龙,祖籍山东,生在北京,下乡插过队,回北京后在一所大学里做木匠。几年后,他突然迷上古代青铜仿制工艺,辞职办起一个小青铜作坊。经过多年打拼,小青铜作坊发展成为一个制作青铜器的工厂。
王德龙的青铜器工厂距离北京市中心近50公里。当王德龙得知韩永是为了首都博物馆的青铜鼎工程前来向他求援时,一时不知怎样表达内心的感受。王德龙向韩永讲述了自己对青铜器的理解,并立即构思了青铜器纹饰的草图(图6)。

(6)如果说法国设计大师杜迪阳设计的新首博是一件传世之作,这件作品的点睛之笔就是美丽的青铜纹饰
许多建筑设计师都解决不了的难题,就这样被一个青铜工匠解决了。
2003年春天,当人们企盼新馆工程早日结束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给施工造成了巨大冲击,工程进度被严重拖延。
2005年初,在北京市政府承诺市民在这一年要办到的56件实事中,首都博物馆新馆在年内建成并且开馆运行位列第九。
北京市政府要求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和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永签字,保证新首都博物馆在2005年年底之前开馆运行。
尽管梅宁华签字的承诺书上写的是试运行,但他明白,自他们签字的那天起,就意味着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基建、展厅的装修和布展已经同时进入倒计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偏偏在这时候民俗展的实施方案出了问题,准备施工的图纸一改再改,最后一稿送来的时候,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
具体实施方案确定后,立即进行大会战,施工现场最多的时候有近3000人在作业。
此时,首都博物馆年轻的工程部主任王瑞成了矛盾的漩涡中心。大情小事的组织协调把这位能干的女性忙得团团转。好在她沉着应对,难题总能一件件得到解决。
韩永的时间则被排得满满的,在首都博物馆南侧小红楼的临时会议室里,他每天至少要召集十几个会议。
其实更可怕的是,他们有时不得不推翻已经完成的工程,所有的参建者都没有遇到对施工标准要求得如此苛刻的工程项目。
?由于时间紧迫,首都博物馆的工程施工还没有结束,就同步启动布展的准备工作。
那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在它们的老家孔庙已经存放了很多年。首都博物馆的保管部,从“新首博”开工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文物搬迁前的准备。
文物进入展厅实物布展时,距离开馆已经不足100天。此时,如果文物到位,它们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如果文物不到位,它们的定位、固定还需要调整,后面的工作就只是一纸空谈。
怎么办?首博陈列部的程旭想出了一个布展与施工同步进行的办法。
按照程旭的办法,把需要上展的文物都拍摄制作成1比1的图片,贴在展线上,布展人员可以根据需要直接移动图片来调整文物的位置。当所有文物的位置最终确定后,再将图片换成实物。
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他们因此赢得了时间。
2005年10月,在武装护送下,第一批文物离开了它们寄居多年的孔庙,来到了新家。
由于在孔庙“老首博”的库房存放已久,会有无数的霉菌、虫卵寄生在文物,特别是丝绸和字画上。为防止受污染的文物把霉菌和虫卵带进“新首博”,所有文物必须用毒气灭菌灭虫。
按照惯例,文物进行毒气处理后需要晾晒3天,人员才能直接接触。但是对于赶工期的新首博物工作人员来说,3天实在是等不及了。
试营业前的1个月,北京武警总队的官兵进入首都博物馆新馆,承担起安全保卫任务。
对于首都博物馆的所有人来说,这几年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日子。阵痛与欢欣交织在一起,人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冲刺。当布展全部结束时,距离开馆试营业已经不到10天。在40多天的时间内上展12个大型展厅,没有一件文物损坏,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开馆的前夜,从西伯利亚快速南下的寒流掠过中国北方,北京的气温急剧下降。王瑞和她的工程部员工一夜没睡,一直忙到开馆前的最后一刻。
经过建设者们不懈的努力,“新首博” 终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图7)。

(7)准备就绪的新首都博物馆静静地等候参观者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