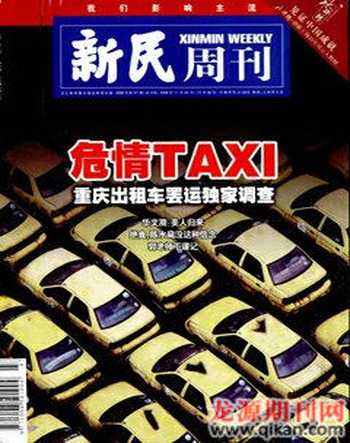读书时代的最后一片红叶
2008-05-30沈嘉禄
沈嘉禄
藏书票不仅代表了悠久的藏书文化,更可以在青灯黄卷的读书生活中,给学子以温暖的关怀和小小欣喜。但是当我们进入网络时代后,它的挽歌也唱响了。
铜臭味掩盖了书香味
金秋北京,香山枫叶正红,游客们纷纷爬上香山,顺便采摘一片红叶留作纪念,其中有些不乏浪漫情怀的人,有意将它夹在书中,想象若干年后的一个黄昏,在翻检旧书时突然激活这个枯萎的记忆。文明史告诉我们,书中的秘密,往往能像闺房秘辛那样,开启另一个故事的后窗。其实,比红叶更可靠的是藏书票。
素有“藏书票国际奥林匹克大会”之称的第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于日前在北京中华世纪坛落下帷幕。小小藏书票至少在读书人中间,激活了一个典雅的记忆。展品为42个国家和地区的1050位版画家的4375件作品,基本反映了当前国际版画藏书票发展的趋势。而且从版式上讲,在电子印刷越来越风行的背景下,古典主义风格让人多少感到一丝伤感。

国际藏书票艺术双年展从1953年举办首届起,半个世纪以来,已由国际藏书票协会联盟成员协会组织轮流主办了31届,本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是首次进驻中国,对于中国的藏书票爱好者来说应该说是一大幸事。但是,收藏界从来就不是拒绝功利的净土,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参赛的中外收藏家对藏书票交换显然更有兴趣。
藏书票作品的交流和交换活动是每届展览必有的内容,这也是吸引各国收藏家和艺术家不远万里前来参加的一个原因。但过分关注商业利益肯定会影响双年展的学术价值。曾经多次参加国际藏书票双年展的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理事黄显功对记者说:“这次展出的国内作品过多,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中国藏书票展兼有外国作品展出。而且参赛的外国收藏家,多利用这次机会进行商业活动,这不能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以前我参加过多次在欧洲召开的藏书票大会,这种猴急的现象很少出现。”
近年来,一向少人关注的藏书票突然在艺术市场上大放异彩。继去年10月苏州举办“全国藏书票大会”、汉沽举办“国际藏书票展”之后,今年3月落槌的藏书票专场拍卖更是让小小藏书票光彩夺目。随后,一系列藏书票收藏活动纷纷登场——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藏书票作品展、上海举办的“杨涵版画藏书票展”、中央美院举办的“子安藏书票个人收藏展”……似乎,藏书票已经被收藏界视作市场的新亮点,或者是新的财富增长点。
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藏书票
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中期的德国,同为今天收藏品的邮票则要在300年后才来到人世。最早的藏书票是德国勃兰登堡家族使用的“天使”藏书票,又有人说是LGLER(刺猬)藏书票,其实它们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藏书票在产生之初,是当时有藏书的特殊阶层——贵族与僧侣的特权。当时一本书出版后,竟然是“裸书”——只有内芯而无封面,购买者得拿到装订作坊请书匠做一个封面,或羊皮或绸面,然后压印家族、教堂或学校的荣耀徽记。
后来,藏书票传到法国、英国以至整个欧洲。藏书票的黄金时期出现在印刷技术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下半叶,从国王、总统、首相到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从社会名流到平民百姓都喜欢藏书票,各种主题、各种版式的藏书票在书房中异彩纷呈,形成了一道道具有文化内涵的风景线。有些书店根据顾客的需求制作藏书票,使藏书票的功能由单纯藏书标记的实用性开始向艺术审美层面发展,藏书票变得更精美。
进入18世纪后,随着欧洲近代工业结构的建成以及科技成果的输出,藏书票也随着传教士和商人、出版家、文化人等传到欧洲以外的大陆,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了藏书票协会或俱乐部,藏书票交流和收藏成为一种时尚。
黄显功是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上海市图书馆学会理事,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理事。在上海图书馆这个幽静的治学环境里,他专攻历史学、文献学和藏书文化。坐拥书城的儒雅书生,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藏书票收藏家,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他是一个学者型的收藏家,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一直在研究中国藏书票的历史。他对记者说:“中国人见识藏书票并非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事,事实证明,在此之前,一些传教士、西方学者和外交官就将贴在书籍中的藏书票带到中国。有时候我在上海图书馆库房里查阅资料,无意中就会翻到老旧的欧洲原版藏书票。”
后来黄显功经研究发现,在上世纪初,中国的许多教会学校、银行、文化机构等,以及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大学,其图书馆也曾大量使用藏书票。这也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现代化产生影响的一个证明。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藏书票文化
据黄显功介绍,1933年前后,著名作家叶灵凤、诗人郁达夫等人开始注意和推介藏书票,“凤凰”藏书票就出自叶灵凤手笔。1934年,李桦创办现代版画研究会,在其会刊《现代版画》第九期还推出了藏书票特辑,这是我国第一个手工拓印本藏书票集。上海鲁迅纪念馆里保存着一批木版画,其中就有鲁迅所藏的24枚中国最早的藏书票。藏书票与版画有天然的血缘关系,致力于版画推介和普及的鲁迅喜欢藏书票大约是很自然的事。
“文革”结束后,随着全民读书活动的兴起,中国藏书票的兴起与收藏活动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新阶段。黄显功与大多数收藏家一样,进入了自己的黄金岁月。“我的第一方藏书印是读大学时在刻印社刻的姓名章,十余年后才拥有一枚由篆刻家周建国先生所治的真正藏书印。藏书票呢,要到1994年初才有了第一张自己的票主书票。这张向版画家付费的作品,据杨可扬先生说还是上海首张付酬制作的个人书票呢。从这年开始,我的藏书票收藏算是起步了。”黄显功回忆自己的收藏经历,表情相当愉快。

在收藏与研究的过程中,不少中外作家、艺术家与黄显功进行亲密互动,使他获得了极为愉快的艺术体验。施蛰存先生在建国前就已经使用藏书票了,1996年底黄显功拜访老作家,得知叶灵凤所写的中国第一篇关于藏书票的文章就刊登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当年他们同处一间办公室。就在这次晤谈中,老先生找出十张“北山楼藏书”藏书票慷慨相赠,让黄显功大喜过望。
寻觅珍品的过程是愉快的,但黄显功的终极目标不是一个“藏”字,而是“用”字。他认为,藏书票当然是一个国际性的、有情趣的收藏品种,但我们不应该将它与书籍剥离开来,创作者在将它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来创作时也应该考虑它的使用性,藏书票与生俱来是与书籍共生死、同荣哀的,它应该牢牢依附在读书这档事上。“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藏书票文化。”他说。
基于这个清醒认识,黄显功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也在于利用上海图书馆的平台,加强自己与艺术家、作家及读者的友好关系,推动藏书票在读书活动中的价值显现。中外艺术家为黄显功设计制作的专用藏书票已经有100余种,这些藏书票都是可藏可用的,所以他的书房里贴有藏书票的藏書也逾千册。而同时,黄显功为中国作家、学者及读者策划设计的藏书票也有近百种,并组织、策划了100多种图书馆专用藏书票和一系列图书出版纪念藏书票的创作与出版。
中国特色是中国藏书票的存在理由
1953年,藏书票收藏家的首次国际性会议召开,之后隔一两年召开一次,同时举办展览,使藏书票在国际范围内有了交流的平台。1966年7月28日国际藏书票联盟(简称FISAE)的诞生,意味着藏书票的收藏家们有了自己的国际性组织。今天,联盟成员国已扩展到41个,会员上万。中国也是FISAE的会员国,我国的藏书票常出国参展,获得好评,特别是那些带有中国篆刻和中国水墨画的藏书票让老外耳目一新。
藏书票是欧洲文化的载体,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它也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作为人类印刷革命与纸质阅读的时代见证,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弥足珍贵。那么,中国的藏书票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也必须体现中国特色。那么中国特色是什么呢?作为四大发明的母国,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这些年来,黄显功一直在谋求与画家的联系,策划出版最“原始”的藏书票,并已经获得很大成功。在记者采访黄显功时,他喜孜孜地拿出一本画册的毛样,请记者分享他的快乐。这是他为北京女画家白逸如设计的藏书票专集,3年前黄显功得知白逸如有意编辑个人作品集后,就帮她联系出版社并设计版式。最后确定的版式异常精美,有点像传统册页的装帧,但极富现代感,每枚藏书票都是多色手工印刷。北京气候干燥,而具有水墨画效果的藏书票对室内空气湿度要求极高,所以白逸如每天最多印5张,一共花了3年时间才将集子的藏书票印完。“只印50本,它的珍稀性由此可见。我就是想通过出版这类经典作品集来提升藏书票的文化地位。”黄显功说。
他还在扬州结识了一位广陵刻字社的老工艺师陈义时,老先生年过六旬,是刻字社硕果仅存的老艺人,前不久故宫博物院还出高价请他与女儿一起重刻了一套武英殿古籍。广陵刻字社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木刻社,长期来为修复文物级的雕版及重刻古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投入与产出的巨大矛盾,这家单位的前景也相当黯淡,老先生的工作纯粹是凭一种文化责任。所以当黄显功请他刻藏书票时,老先生一口答应了。
“我为什么要请他刻藏书票呢?一方面是技艺精湛,另一方面,纯粹木刻的藏书票越来越少了。现在极大多数的藏书票创作者为了贪图省力,用三夹板甚至塑胶材料来刻,味道不对啦。同时,用电脑创作也成了一种潮流。这是令人担忧的。今天政府与学术界很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看木刻藏书票技艺与雕版刻制一样,也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
藏书票
藏书票被爱书人和收藏家喻为“纸上宝石”、“版画珍珠”、“书海之帆”,藏书票的基本形式特征是画面尺寸较小,一般在10厘米见方,画面上要有藏书人的标记,如国际通用拉丁文“EX-LIBRIS”(“属于我的藏书”)字样,或中文“藏书票”及藏书人姓名、别号、书斋名等。运用于藏书票的技法常见的有流行于歐洲的铜版、木版与中国、日本的木刻和丝网。为了普及藏书票,欧美国家的书店和图书馆还经常发行不印票主的通用藏书票,供普通读者使用。现在由于电脑技术的介入,也出现了电脑制作及喷绘的藏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