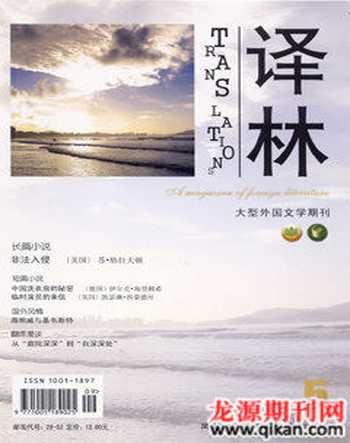福斯特对“英国性”的多重阐释
2008-05-30姜士昌
摘要:在福斯特早期对“英国性”进行的双重构想中,众多的人物因被排除在外而处境尴尬,这些人物的窘境就是作者自身窘境的写照,也使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英国性”这个概念的微妙和复杂。在后来的小说中,作者拓展了他对“英国性”的理解,为读者多维度地展示了英国社会的分裂状态,并进而表达了一种期盼“四分五裂的英国”重归完整的美好的社会理想。
关键词:福斯特 “英国性” 多重阐释 “联合”
福斯特的魅力源自他为英国知识界描绘的令他们渴望的英国形象。他能够对奥登一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他的小说反映出他“重新联结一个分崩离析、杂乱无章的文化的迫切愿望”(注:Bradbury,Malcolm.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12.),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指出的福斯特心目中“坚信大家终会看到”的那个“幻想”(注:Widdowson,Peter.E.M.Forsters “Howards End”:Fiction as History [M].Brighton:Sussex University Press,1977,p.93.)。而人们真正明白了这个“幻想”的意义与价值却是到了福斯特去世之后了。
福斯特早期的对英国的描述是马修·阿诺德式的。《最遥远的旅途》中文明的使徒与下里巴人们的对立贯串全书。故事讲的是一位世家子弟里基·艾略特与一位出身卑微的乡村青年斯蒂芬·沃恩汉姆由相互冲突到逐渐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在后者的帮助下挣脱了毫无感情维系的婚姻,最后为拯救后者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小说树立了两个遥相对立的“英国”——以萨斯顿为代表的纯朴的乡村和以剑桥为代表的文明的都市——它们各自声称自己代表整个国家,然而实际上又都无法做到。斯蒂芬·沃恩汉姆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和暗示性:他既不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也不是像《霍华德庄园》中列奥纳多·巴斯特那样的下层社会的一员,于是,他无法(或说无权)在上述两个“英国”之间进行选择,这一点颇令他悲伤。里基·艾略特虽与他身份不同,却有着相似的遭遇——他也陷入了这种两难选择。正因如此,里基才从剑桥跑到乡下,睁大双眼寻求他心目中的英国,却失望地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摆脱这个两难抉择的窘境。他的阿诺德式的信念开始动摇。他感伤地对人说,英国太浩瀚了,尤其是他的文学,但是,好像有一个英国在排斥另一个。(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51.)
在这种困境下,他的所有剑桥文化能够给与他的只有一种令他不安的、脱离一切团体的疏离感。然而,福斯特的强烈的戏剧化追求使得他精心描绘的两个“英国”间的划分在这里变得模糊起来。原来,斯蒂芬是里基的同母异父兄弟,他也正是里基渴望成为却又无法成为的那种“英国人”。他认定了这个“英国”就是自己的“英国”。当艾格尼丝(里基的妻子)试图把他送往殖民地时,斯蒂芬的反应出乎那些剑桥人的意料:
他突发一股奇怪的热情:宁肯饿死也不离开英国。“为什么?”她问,“你爱上谁了吗?”他捡起一块石灰石……没有作答。牧师低声说:“那与出国不一样——不列颠——血浓于水呀——”周六那天,一块石灰石打破了她家客厅的窗子。
于是,斯蒂芬半是无赖、半是殉道者地离开了威尔特郡。不要给他打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他从未与社会争吵。(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244.)
于是,福斯特把他送到萨斯顿去打碎更多的窗户。这儿似乎是个非常舒适的世界,在这里斯蒂芬什么也无需做。但是,正如作者所暗示的那样,问题并不在这儿。斯蒂芬的确是位爱国者,他那讨人厌的石灰块就是他与这片土地密不可分的象征。他既不像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又绝非像其外表那样质朴自然。他可以拿着费灵太太或艾略特的钱去赛马,去寻欢作乐,并感谢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为他带来了所谓的“质朴自然”的生活。他不否认诗歌可能会使生活更诱人,但诗歌怎么也不大可能取代诸如吃蛋糕这样的生活实际。不难看出,福斯特需要用他的这种天真无知来“豁免”对他的邪恶信念的谴责。他可能正站在一个英国的栅栏外,向着它的窗户投掷飞弹,但可怜的是,另一个英国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离他同样地近。这里,福斯特鼓吹的“英国性”似乎越来越像是图画似的伪装,斯蒂芬恰是那个既不属于剑桥又不属于萨斯顿的群体的象征。在小说中,斯蒂芬更像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人物,小说只构想了一个躯体而没有创造一种可触摸的质感。但是,他为读者制造了更大的联想空间,暗示了“英国性”的复杂。
莱昂内尔·特瑞琳指出,“对福斯特来讲,隐居决不代表个人的乡土观念”(注:Trilling,Lionel.E.M.Forster:A Study [M].London:Hogarth Press,1967,p.30.)。他是在说,隐居乡间并不是具有强烈乡土观念的明证。因为里基本人就曾说过:“我只有先喜欢英国人,才能喜欢上英国的一草一木。”(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174.)可见在福斯特看来,只有在与作为整体的英国发生关联时,《最遥远的旅途》中的人物才有其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把福斯特所真正意识到的东西看成他的创作意图,因为,无法确定的恰恰就是他的人物与英国之间的关系。福斯特竭力想用爱情的力量来拉近他所意识到的不同“英国”间的关系,这使得《最遥远的旅途》成为福斯特“最富有热情的书”(注:Trilling,Lionel.E.M.Forster:A Study [M].London:Hogarth Press,1967,p.67.)。虽然这种“热情”很快就随着杰拉德的去世而消退了,虽然里基也郑重地告诫艾格尼丝决不要忘记她“最辉煌的时期已经结束”(注:Forster,E.M.The Longest Journey [Z].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0,p.80.),虽然这种用爱情作为矫正对“英国性”的理解的方法难奏其效,但是,它至少帮读者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说里基无法选择归属于哪个英国的话,福斯特也是如此。威尔特郡是萨斯顿的替身呢,抑或是剑桥的翻版?它真能完全代表英国吗?小说的诗意的描述本意是想将其明朗化,却适得其反,产生了一种遮掩的效果。小说中那种意在拓展斯蒂芬人格的倾向颇令读者疑惑,作者到底想往哪个方向引领读者呢?显而易见,像阿诺德一样,里基也发现自己被卡在了“两个世界”之间。最后,他选了萨斯顿这个较为容易的选项,正像他的创造者很轻易地就选择了把他毁灭这个选项一样。然而,这绝没有解决问题。作者的困惑明确地反映到了这个仓促的结局上。
可见,福斯特早期对“英国性”的双重构想并没有达到自己所幻想的目标,因为有权进行这两种选择的毕竟只是少数人,众多的人因被排除在外而处境尴尬,这些人物的窘境就是作者自身窘境的写照。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了“英国性”这个概念的微妙和复杂。于是,在《霍华德庄园》这部小说中,作者拓展了他对“英国性”的理解并集中为读者展示了一系列英国社会的分裂状态:阶级与阶级、城市与乡村、唯美精神与现代工商业、癌变的文化与有价值的文化、分崩离析的文化与作为整体的文化、理智与情感、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命、乏味与激情、身体与灵魂、生与死、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注:Bradbury,Malcolm.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p.112; Richetti,John (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826.)整部小说在平静的表述背后隐含着令人焦虑的感伤的预言。
《霍华德庄园》的背景是“一战”前的英国。小说描写了来自不同社会层次的三个家庭之间的关系与纠葛,表现了英国当时的阶级斗争状况。这时的英国表面看似乎是一种异乎寻常地一体性的文化,实则在平稳的社会文化表层下潜藏着诸多裂痕。“对福斯特或大多数别的自由的人文主义者来说,‘一战之前不存在‘自由危机”(注:Widdowson,Peter.E.M.Forsters “Howards End”:Fiction as History [M].Brighton:Sussex University Press,1977,p.38.),这是彼特·维德森以后来者的眼光对那个时代的评论。这个评论看上去无可争议,可是不幸的是,当福斯特警觉地发现“我们的绿林灾难性地、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注:Furbank,P.N.(introd.).“Postscript” to Maurice [Z].London:Edward Arnold,1971,p.240.)的时候,读者便不得不开始诘问,这种灾难的种子来自何方?它是否确曾存在于那象征传统乡村生活的“绿林”(greenwood)之内?福斯特的担心不无道理:被少数心态平静的人们向往并没有什么可怕,而当那些尚未平息其“自然崇拜”的热情的人们为图消遣而纷至沓来的时候,“绿林”的危机才真正到来了。《霍华德庄园》里借助列奥纳多·巴斯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并没能解决它。在这部小说的“愉快结尾”(happy ending),列奥纳多先行让路后,马格丽特顺利入住威尔科克斯夫人的宅邸——霍华德庄园。这种中上阶层对乡村的占有欲望反映在福斯特的多种作品中。比如在1918年的一封信中,他就承认说,人们对他的偏见超过了对爱德华·托马斯的诗歌、散文、人格等方面的反对性阐释(注:Lago,Mary & P.N.Furbank (eds.).Selected Letters of E.M.Forster (I) [Z].London:Collins,1983,p.184.)。这大概是他对自己的感觉作出的一种反应吧:他感到托马斯的关于乡村的描写正在拉近乡村与市郊的距离。在后来的《我们时代的挑战》一文中,福斯特发现自己无法把社会对新城镇的需求和因此而对乡村造成的破坏这两方面的问题等同起来:“我坚信某种无法取代的东西已经被摧毁,就像被炸弹击中一样,英国的一部分从此消亡了。我不知道在精神世界里能有什么可用以补偿这种对传统生活的破坏”(注:Forster,E.M.Two Cheers for Democracy [Z].London:Edward Arnold,1951,p.67—68.)。这恰恰也是爱德华·托马斯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注:Motion,Andrew.The Poetry of Edward Thomas [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0,pp.112—120.)。可见,福斯特并没有完全把握爱德华·托马斯的诗歌。英国在努力创造一个适合英国人居住的民主环境的同时,却在不经意地听任它自认为自己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遭到毁灭,这是两人的共同担忧。
《霍华德庄园》并非仅仅在作类似于上述危言耸听式的预言。对“毁灭”的担忧促使作者关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实质问题:继承。《霍华德庄园》探讨的首要问题就是谁应该继承威尔科克斯夫人那个阶层所传递下来的那个“英国”。理论上讲,福斯特相信这个英国应该属于大家的共同财产;实际上,书中描绘的却是一个颇为私人化的结果:这份遗产被威尔科克斯夫人传给了马格丽特·施莱格尔小姐,她和海伦、亨利,还有海伦为列奥纳多生的儿子一块住进了霍华德庄园。这个结果反映出作者的某种个人愿望,预示着小说中各个人物所代表的英国不同阶层正在趋向融合和同化,他们将被迫去适应他们赖以生存的英国。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融合的圈子毕竟还是很小。那么多的人被排除在外,这也是颇有意味的。试想,站在伦敦甚或是赫特福德郡的新城镇的角度来看,霍华德庄园毫无意义,大都市和新兴城镇是不屑与老古董似的农庄为伍的;对巴斯特一家来说它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如何去欣赏它;再从威尔科克斯家族自身的精神气质(查尔斯则就其体格)来看,他们也没有资格继承这座房子。换句话说,整个中间阶层似乎都不适合保留这座房子所代表的那些传统。它的真正的继承者就应该是埃弗瑞小姐(Miss Avery)或玛格丽特,前者是旧式自耕农的后代,后者则是一位重视内在生活的自由党知识分子。于是,霍华德庄园——传统的田园式英国的缩影——终将被一位具有一半德国血统的继承者施莱格尔小姐所挽救。为了实现自己的幻想,福斯特不得不采用一个权宜式的结尾:马格丽特·施莱格尔最终成了威尔科克斯夫人,而且庄园的维护费用最终还得让威尔科克斯家族掏腰包。这里,福斯特的愿望和它对社会实际的认识之间的抵触明显地展现了出来。可见,一部旨在宣扬包容和民主的小说,无论它如何权宜,最终也只能是两者都无法确保。《霍华德庄园》的最终意义全集中到了主人公玛格丽特身上,纵然她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可赖安顿她本人生活重负的某种比她自身更强大的东西。福斯特在小说结尾所颂扬的那个“英国”在玛格丽特形象的支撑下逐步变得清晰可见起来。
显而易见,福斯特就是想要借助玛格丽特的形象来反映其社会理想——“但求联合”。这是小说中探讨的与“继承”问题并行的但却更为重要的另一个问题。首先是威尔科克斯和施莱格尔两家所代表的阶层间的沟通。困难的确存在,因为,通过施莱格尔的眼光,读者肯定会敏锐地意识到两个家庭之间的鸿沟有多深。在此问题上,福斯特不是个乐天派,但是他的确相信(或者希望)两个阶层之间的沟通是必要而且可能的,并且在安排情节上有意识地让双方看到他们相互需要对方。然而,两家的最终妥协并没有消除福斯特对英国即将“四分五裂”的状况的担忧。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英国已处于危机四伏的时代,各阶层的“联合”势在必行。虽然亟待调和的是中产阶级间的分歧而不是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但是,即便是威尔科克斯一家和施莱格尔姐妹打得火热,英国仍然是个“分裂的”国家,这种分裂不是仅仅这两个阶层的“融合”就能够解决的。这里暗含着一个假想,一个作家本人也难以预料其结果的假想——“四分五裂”的英国最终走向“联合”。该小说的假想性特征是它的力量所在,同时又是它的薄弱之处,因为这很容易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假想能否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这样的猜想之上。小说的结尾证明,作者本人对该假想的结果也没有什么把握。
也许福斯特希望将他笔下的不同英国“联合”起来的真正动机是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一个英国。新兴的民主主义的英国是否足以补偿它所取代的那个旧式的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点福斯特也没有把握。对霍华德庄园的修缮管理费用恰恰要依靠那位最有可能把它卖掉或者拆除的中产阶级成员的资助,勉强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一个英国——说明福斯特正处于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压力下,小说退却了,转而进入诗意的迷阵。诗歌掩饰了那些在小说中刻意营造的“联合”。正如李维斯所说,“福斯特先生的‘诗意的交流并非都达到了诗意的水准(要是真的去领会其意图背后的含义的话,福斯特先生倒真像是威尔科克斯而不是施莱格尔)”(注:Leavis,F.R.The Common Pursuit [M].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2,p.271.)。事实上,自从威尔科克斯家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他们的“绿林”之后,他们倒成了真正的最需要“绿林”的人了。玛格丽特自己不太需要怀旧,因为她有太多的关于“老辈人”的真实印象,令她回顾起来就焦虑不安;她理解为什么“我们周末才去造访的乡村却是他们真正的家园”(注:Forster,E.M.Howards End [Z].London:Edward Arnold,1973,p.266.)。玛格丽特的“乡村”有点像市郊的感觉,甚至有点宁静、文雅。值得庆幸的是,她并没有把它感伤化。她知道她的“联合”的愿望并不能保证真正的联合的实现,相反,还可能使它变得更难实现。在赫特福德郡,威尔科克斯先生肯定比她玛格丽特感觉更加自在。尽管玛格丽特希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耽于冥想的”英国,她最终看到的却是某种更为老派、棘手的东西——就像斯蒂芬·沃恩汉姆在威尔特郡的所作所为那样。但福斯特至少在一点上值得称道,那就是,他看到了英国也许太深奥了以至于无法分类,或者是隐藏太深而不能呼之即出。
如果说上述福斯特所追求的联合还是基于妥协与和解,那么,他1914年完成的同性恋小说《莫利斯》则第一次表明沟通与自由往往通过决裂来取得。《莫利斯》算是福斯特最具挑战性的一本书,其中以与本阶级决裂而达于“联合”的曲折经历给主人公带来危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愉悦,而两者都令人感到莫名的痛楚。小说写的是主人公莫利斯与同学克莱夫同性恋的故事。克莱夫后来抛弃了莫利斯,与一位门当户对但毫无生气的女子结婚,走上了仕途。莫利斯则各处求医,希望能成为“正常”人,但这一切只加深了他的痛苦。后来,克莱夫家庄园的猎场守护人艾列克爱上了莫利斯,最后两人放弃了各自的前程,奔向绿林,永不分离。相似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使《莫利斯》被称为同性恋版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小说的结尾显然是卡宾特与他的情人梅里尔的写照。《莫利斯》的主题远远地超越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整部作品是一腔诚实而自尊的呼吁。对福斯特来说,《莫利斯》代表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此时他已不再提倡和解与妥协式的沟通,而是在呈现人物与本阶级决裂。这种决裂不仅给莫利斯带来了幸福,而且为作者十年后创作《印度之行》作了思想和精神铺垫。
像上述那样基于对现实中某个“英国”的忧虑或者憎恶而展现出另一个真实的英国形象来与之抗衡,这并非福斯特的独创。这种构想,除了福斯特、劳伦斯的小说外,在诸如《乌有乡消息》、《伦敦之后》,还有《无名的裘德》等小说中和诸如爱德华·托马斯等的诗歌中均能找到,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作家们希望通过不同层次“英国性”间的比对而达于对“英国性”的最全面的描绘,甚而有诸如托马斯那样的诗人、作家去忠实地记录、再现“犄角旮旯”里的英国。可见,20世纪的英国作家更乐意局部地而不是整体地观察英国,人们会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把英国作为描绘对象的现代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地方主义者,而不是一位大市民。哈代如此,劳伦斯如此,爱德华·托马斯也如此,福斯特至少在思想上也是如此。福斯特笔下对复杂的“英国性”的展示表现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而其中的“联合”的主题则反映着他美好的社会理想。虽然这种美好理想最终未能、也无法得到切实的、完美的实现,它还是因此为福斯特赢得了更好的口碑,因为它代表了那个时代英国国民的愿望。
(姜士昌: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45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