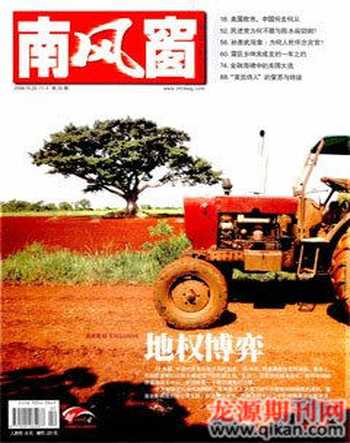濮存昕:我一定要正常的呼吸
2008-05-30
9月初的一个周一早间,濮存昕驾着他的红旗盛世车来到北京东南四环外的摄影棚,这位中国话剧舞台上中年一代的代表人物,看起来心情愉快,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整个上午,他不仅仅是在拍摄,还要在场景转换、拍摄暂停间隙兼顾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应要求与几家揣着不同主题的媒体做交谈,还要接待那些找上门来寻求帮助的社会弱势个体,尽量使他们感觉满意。55岁的濮存昕身上有某种类似境界的东西。与他做过交谈的人,对此大概不会有异议。
执与不执的境界
16岁时,身患疾症的濮存昕加入上山下乡的流放历程,在黑龙江种地、放马、演样板戏。7年后,才结束了边关生活。
回到北京,患过小儿麻痹症的濮存昕工作无门,终被父亲导入话剧演艺生涯,此生自此定格。如今,已逾知天命之年的他说,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太执的。人生天地间,一切皆在执与不执之间。
在采访中,应记者的要求,濮存昕谈起了话剧。30多年的话剧人生涯使他谈及话剧显得格外带劲儿。今年7月,北京人艺新推出《生·活》剧目,他一上来就提到了这出抗震题材新剧。汶川大地震之后的第九天,北京人艺就做出了筹排抗震话剧的紧急决定,意在迅速地用艺术方式反映地震到来时抗震救灾事件以及社会个体的反应。
有时候为了公益活动,为了抗震救灾,演出是不可以要钱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演戏是他赖以谋生的工作,是他的生活,是他付出给社会的,相应地,社会必定要给予他适当的报酬。他说,“要进入社会规则,但一定不逾矩。”
进一步问他,在任务和义务压身的时候,是否有把握也能确保演戏的质量?他点点头,毫不含糊地答道,尽量要使二者结合起来。
论资排辈,这位自称已经算得上人艺前辈的艺术家,今天依然在坚持他认为应该坚持的,他已经有足够的基础和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做事情了。在访问的时候,他大段地朗诵着人艺正在重新编排的《哈姆雷特》里的台词,脸上是挂着笑意的,开心而满足。
他在乎自己的舞台和观众。在那个空间里,他说,我尽量要求自己每一次、每一次地把生命交给舞台和观众,我真的把生命给他们,我不相信他们不在乎我。他还说,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一个受喜欢并且影响观众、影响社会的演员,是真正的演员,不是一个一般的演员。
安与不安的境界
拍摄与采访工作交替进行。当采访的话题转到北京残奥会时,濮存昕很直率地申明自己不是志愿者。

濮存昕曾经努力要申请成为一名志愿者,但结果未被批准,因为不达标。他无法牺牲每一天时间,什么都不干,全天候守在志愿者的岗位上。而且志愿者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岗位,需要进行严格的训练。他说自己是一个与社会各方面保持往来与合作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做到这一点。对于没能成为志愿者这个事实,他表示很接受,认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不是一种秀。因此,对于濮存昕来说,没有成为北京残奥会志愿者也许反倒是令他比较心“安”的,这样,他可以有更多机动的时间为奥运做出贡献,比如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参与制作的一组组奥运公益广告。
此外,在奥运期间,濮存昕无偿参与了一些文艺演出。他无疑十分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知道什么事情是真正适合自己的,知道怎样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让自己心安理得。但是,他也有“不安”的时候。
他说自己这种人是会做秀的,只要一出现就能受到关注,对外界都具有或轻或重的影响,因而需要恰当地拿捏好尺度,“我们内心也有一种不安,普通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儿,谁都不知道;我们做一件好事儿,又有名、又有利”。
聊到这儿,话题被一帮大学生的到来给打断了。学生簇拥着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前来请求濮存昕的援助。2001年,濮存昕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爱心基金会,主要资助对象是艾滋病孤儿和失学儿童,本与白血病不相干。但这一次是偶然撞见的,濮存昕说,要是没碰上,我也不会管这件事,但现在碰上了,就要帮帮他。
濮存昕爱心基金会将支付一笔钱,帮助已经确认可以进行配对治疗的白血病患儿进行骨髓移植手术,患儿父亲手捧着濮存昕在化妆间出具的一张给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超规定亲笔批示,落泪却不知怎么表达谢意了。
送走这拨人后,有记者问,你做这种事情,有终点吗?濮存昕说,生命旺盛的时候,总是在参与社群。但总有一天,你要结束自己的参与,说公益要永远做下去,这不太可能。我也有主动离开的时候,需要更多年轻人的投入。
爱与理性的境界
濮存昕说,自己“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骨子里就有红色情结。而红旗盛世的出现,无疑为他圆梦这种红色情结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成为他实现心灵深处一直以来那种民族情感的最好载体。所以,濮存昕开着大红旗,自信更自豪,红旗盛世对他来讲,承载的不仅仅是尊贵与自信,还承载着他的梦想,这款车是他的面子,更是他的内在精神气质。用濮存昕自己的话说就是:“开了将近20年车,很多国际豪华品牌车都遇到过,但红旗盛世才是让我最舒服的,这种舒服首先来自心理,因为这是红旗,民族汽车第一品牌,中国汽车工业的开山鼻祖,高端且厚重。”
一个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濮存昕对“红旗”的这份情感。濮存昕常讲起他对红旗颇不满意的一个小细节一脚垫上印着鲜明的、毛主席当年亲笔所书的“红旗”两个字,使他无论如何也下不去脚。“谁都会有这种心理,那么大的红旗两个字怎么能印在脚下物品呢?我小的时候,红旗的一角可是天天系在脖子上的!”
当然,生活中的濮存昕与他塑造的经典艺术形象一样,理性多于感性。所以,对表演艺术的完美追求,若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来,便决定了濮存昕对物质享受的品味方面仍然不失理性,不要求过度奢华,但不能容忍缺陷。尽管对于红旗品牌拥有深厚的“红色情结”,但是,濮存昕对于自己选择红旗盛世的标准依然称得上“苛刻”,比如驾驭的得心应手与安全,以及作为高级车应有的卓越品质。

濮存昕说,红旗盛世最让他感到欣慰的地方是,民族自主品牌现在能够造出这样高品质的车了,红旗盛世吸收了世界最好的技术再进行自我创新为我所用,可以在它身上得到名车的享受。濮存昕认为选车有两个层次:买第一辆车时,考虑的是价位,买车是为了享受自由,为了有一种自主感;现在买车,考虑的是汽车品牌、汽车文化带来的影响。“选择红旗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民族汽车工业的旗帜,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高端车。我们可以用5年时间来亲近红旗品牌!认知红旗品牌,这是一种选择的兴趣。如果说仅仅为了爱国才买红旗,那样反而使红旗品牌概念变窄了,还要看它的科技性、先进性与高品味内涵,像红旗盛世这样的汽车才是我们国人的自豪。”
其实,当拍摄与采访进行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原先计划的报道主题已经被推翻了。原以为濮存昕是在为红旗做代言人,其实,他只是一位红旗盛世的忠实车主,一位红旗品牌的爱好者。正如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公益事业领域的某种标杆,认为那只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是不正常的,他从不对号入座,也不予理会。他说,“我一定要正常的呼吸,正常的喜怒哀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我要是去迎合,我就是假的。”凝聚了无数国人厚望与热情的红旗汽车,当然也一直崇尚着正常的呼吸,吞吐之间博采众长,厚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