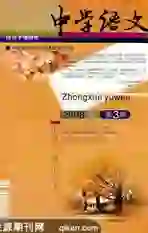雅淡:唐宋词的文化选择
2008-05-14邓嗣明
邓嗣明
词为江南审美文化之代表文学样式,已为许多词家和文化史家所确认。在他们看来,在宋代,其文学主体乃以词名,就因为中华文化南移,江南文化处于中心地位所致。如冯天瑜等的《中华文化史》尝言:
也正是在北宋,文化中心南移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之语。词为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如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的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也多数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
的确,随着中华文化中心的南移,社会习尚、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急剧变化,“自唐迄宋,变迁孔多……前则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576页)。“犹多古风”的唐代,其占主导地位的是北方文化,色调浓烈雄放,史称唐型文化;而“别成一种社会”的宋代,其中心地位的文化为江南文化,色调淡雅婉媚,文化史家谓之宋型文化。正如一些文化学学者所言,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奔腾着昂扬的生命活力;昭陵石雕中雄壮健伟、神采飞扬的“八骏”,乾陵石雕中粗壮雄伟的石狮,李爽墓中双手握拳、昂首挺胸、足踏怪兽、远眺怒吼的陶天王俑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两宋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宋代建筑尚白墙黑瓦,槛枋梁栋,不设颜色,专用木之本色;宋代瓷器、书法、绘画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即如宋人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参见《中华文化史》634页)概言之,唐型文化的审美特质为“雄浑”,而宋型文化的美学意蕴乃“雅淡”。雅淡,正是江南文化的本体特征,而植根于江南文化土壤中的审美文体——词,正以婉约雅隽、细腻雍容为审美主位。就词体的审美流变看,处于“雄浑”与“雅淡”审美转变的轴心人物,乃南唐后主李煜。
后主李煜是南唐时代江南文化的代表人物,词体一入他手,格调巨变,审美观念至彼亦情韵独具,遂成江南文化审美风格的标志。他的审美理想直承六朝“婉媚”、“畅情”资质的同时,自己又鼎力“改革花间派涂饰、雕琢的流弊,用清丽的语言、白描手法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抓住自己生活感受中最深刻的方面,动人地把情感表达出来,给人深刻的艺术感受”(新加坡谢无涯《南唐李后主词研究》)。李煜审美趣味的独特之处,在于追求一种疏离色欲的“纯情”。在继南朝“文、笔之辨”,“人心”、“文心”分割的基础上,能自觉地开掘“情、欲疏离”的审美意境。因此,他的“畅情”并非“纵欲”,他的“婉媚”亦非“淫靡”,在审美方式上开“雅化”风气之先。情、欲,乃审美与非审美的两个不同观念,纯情为雅,私欲为俗。刘熙载言:“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艺概·词曲概》)后主的词作常为纯情抒发,力避俗欲纷扰,因而显得清雅真丽,虽粗服乱头而不掩国色。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指的似为此种“雅化”风范。李煜在亡国前的深宫之作是纯情抒发,他于国破家亡后“日夕以泪洗面”亦复如是。然而,“词之雅正,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士大夫之词也在不同的层次和角度上铺陈爱情的美丽和脆弱。因其美丽,故能成为其政治生涯、仕途经历中的一丝温情;因其脆弱,故极易破碎毁灭。正如一尊晶莹澄碧的古玉器,它的任何一条裂隙都能使至情之人征引出人生的缺憾。士大夫之词在对爱情的吟咏中便潜隐着一种深沉博大的人生悲慨。
下面是李煜的《相见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首词反复使用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春红、胭脂等颜色字;江水如蓝,林花似火,正是人生得意尽欢的青春季节。世界的灿烂似乎涵咏着未来的美丽和辉煌。然而春日的胜景总是苦短,寒雨如抽,夜风如刀,将春红和春红所象征的一派浓情斫尽,春景锦缎似的容颜一瞬间憔悴殆尽,美丽永远如梦一样稍纵即逝,不可把握。“太匆匆”用叠字叠韵,韵调迂徐舒缓,犹如心灵深处沉重的叹息,透露出一种彻骨生命之寒意。又《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叶嘉莹教授对这一首词的分析极为精到,大意是说:“春花秋月”仅仅四个字,就同时演出宇宙间永恒与无常的两种基本形态:春花秋月无尽无休。而人的生命却随着一度的花落月缺而长逝不返了,“往事知多少”将人世无常之词写得动魄惊心。“春花秋月何时了”乃是写宇宙之运转无穷,往来之茫茫无际。“往事知多少”乃写人生之短暂无常,是去者之不可揽返。“何时了”三字却又早已透露出了负荷着无常之深悲的人,面对此无常无尽的宇宙之运转的深深的无奈。“问君能有几多愁”,对人生作彻底的追问。“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乃作彻底的答复:人生所有的只是一片滔滔滚滚的永无穷尽的悲情而已。
只有把后主放在审美文化演进的位置上,才能看到他纯用白描、畅情率真、笔致雅化的词史意义和美学贡献。“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正是对他把词由为礼歌而作纳入抒情畅情轨道的精辟概括,从此,词体遂成抒发情性的中介,雅化的词家情致使词的审美层面提高,因而,词的地位也随之提高了。李煜功不可没。后主风雅疏狂,不事雕饰,确为江南第一词手,后人尊他为“词王”殊非过誉。
宋词的雅正审美风韵建构于北宋,成熟于南宋,所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就是指此而言。这种流变的基础,在于中国文化的南迁至南宋的最终完成。南宋以降,以“雅淡”为审美特征的江南文化居于中心地位。雅淡美韵的形成,亦得自江南地域山明水秀的“江山之助”。因此,沈德潜说:“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其所之地。”(《艿庄诗序》)词至南宋,从表达方式看,已由男子而作闺音的“代言”变为词人的自身独白,语言的纯化、雅化,典故的精选、活用,使得词作丽而不俗,具有浓厚的书卷气,集中映现江南士人的品格和气质。
据考,宋室南渡,政治中心代表人物的籍贯亦江南化,其“明慧文巧”的气质使雅正之风几臻极致;同时,在南宋,江南士大夫居于政治集团的中心地位,已成中华文化南迁的重要标志。因而,词体作为一种雅化文体要求越来越高,正统词人提出,词应“无一点俗气”,甚至“宁僻无俗”。曾慥《乐府雅词》在选词时,将柳永词汰除尽净,其原因乃在柳词“涉谐谑”。同时,此时与柳永当年以俗词“忤仁庙”而落第的遭遇相反,雅词已成士人“释褐”的资本,且倍受皇帝青睐。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载有太学生俞国宝于小酒肆醉笔写词,而极为高宗爱赏,赐官荣登庙堂的逸事。因而,典雅风韵在词体上显现更著。“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所谓“工”,所谓“变”,就是指词体的雅化程度而言。
典雅精致风韵,确为南宋一代词家情致。雅以为“淡”,远去俗气,兴于六朝江南文化的审美观,南宋词人也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趣味和理想纳入六朝以来的江南文化传统,认祖归宗,以见所自。靖康之后,“晋宋风味”、“晋宋人物”几乎成为当时品评作品及人物的价值标准和理想规范。南宋词人正是以“晋宋风味”来雅化自己的词作的,这样,词遂成文人士大夫抒怀寄意孤芳自赏的一种新诗体。姜夔孤高雅洁,性情冲淡,其词亦具凄清逸怀之美,在中国词美学史上被目为雅词代表人物,亦为江南文化艺术精神之集大成者。词论家都认为他独具晋宋风韵。陈郁在《藏一话腴》中说:“白石道人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陈撰《玉几山房听雨录》亦云:“南宋词人……要以白石为极诣,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献湮灭,乃能雅尚如此,洵称豪杰之士矣。”周密《齐东野语》尝为自叙:“参政范公(成大)以为(白石)翰墨人品,皆似晋宋雅士。”时人皆以白石深得晋宋遗韵。
事实也正是如此,姜夔确为江南文化艺术精神陶溶出来的一位词人,他的词备具山林缥缈之美,亦显孤高凄清之姿,为一代雅词之宗。据《砚北杂志》载,顺阳公盛赏白石,“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云:‘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寂寞而凄凉。这里表现的孤高与清绮之美正是雅词的特质。白石身处江湖,爱赏自然,常于玉雪映梅、新柳被水的清幽中寻找一种澄澈空明凄清冷寂的境界,以“自琢新词”,表达其江湖林下的清趣与雅韵。
[作者通联:湖北荆州沙市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