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兰朵》的中国使命
2008-02-11杨时旸
杨时旸
这部中国版歌剧从诞生起,就承载着要有中国式解读、要体现中国味道、要展示大剧院硬件设施等诸多“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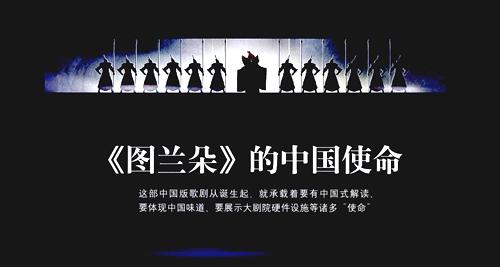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开幕演出季进行过半的时候,大剧院终于向“原创”迈出了一步。2008年3月,大剧院版本的歌剧《图兰朵》将正式亮相。在这部歌剧原作者普契尼诞辰150周年的时刻,国家大剧院选择了这部有着“中国内容”的意大利歌剧,并着手制作其“中国版本”。
也因此,这部歌剧从诞生起,就承载着要体现中国版的独特解读、要有中国味道、要展示大剧院硬件设施等诸多“使命”。
第三个续写版本
2007年6月6日凌晨6点,中国青年作曲家郝维亚在意大利租住的公寓里接到一个电话。郝维亚有些不耐烦地对电话说,“谁啊?”电话那边回答,“你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陈佐湟。我们想请你续写《图兰朵》。”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邀请之前,郝维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已经在意大利居住了半年,专门研究歌剧。他从来没想过成为全世界第三位《图兰朵》的续写作者。
这部歌剧是原作者普契尼的封笔之作,在尚未完成之时,普契尼因病去世,留下了一个未完的结尾。在郝维亚之前,已经有两位作者曾经为《图兰朵》进行续写创作,一位是普契尼的学生、意大利作曲家阿尔法诺,因为他当时无法看到普契尼的总谱,续写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狗尾续貂。而第二位续写作者贝里奥又是一位现代作曲家,续写的部分总使人觉得与前作脱节。因此,这次中国人的续写成为了新的关注点。
在确认消息之后,郝维亚开始与大剧院商讨具体细节。国家大剧院给出的要求是:这次的版本首先是普契尼式的,意大利的,其次还要是中国的和大剧院的。这个想法和郝维亚不谋而合。
所谓的中国式是跑不了的。我想的不是怎么故意做出中国味道,而是怎么能不把中国味道流露得太多。”郝维亚说,“我的中国心在那放着,但是洋装怎么能合适地穿在身,这是个难题。”
对于这部歌剧的再创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承接传统的版本做经典的传承,二是彻底颠覆。而作为国家大剧院的开山之作,毫无疑问要选择前者。
“其实颠覆比传承简单,在歌剧里来一段西皮二簧,我绝对做得到,那很有中国元素,又很先锋,但是我们不能那么做。”郝维亚说。
作为国家大剧院这样级别的剧院,已经为一部作品的稳重和经典做出了要求,对于这一点,参与创作的艺术家完全了解,“我们不应该着急玩先锋,玩破坏和变化,而是得把每一种艺术形式最好的基本形式展现出来,忠诚于原著让大家先学习。”郝维亚说,“如果最后观众觉得我的续写不是续的而是原来就存在的,我就算成功了。”
淡化肃杀凸显“爱”
起初,大剧院版本的《图兰朵》想选择意大利著名导演泽菲•雷利作为总导演,但是对方已经84岁高龄,他的经纪人谢绝了中方的邀请,最后改为中国的导演陈薪伊。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陈薪伊开始着手研究各个版本的《图兰朵》,结论却是,“看不懂。”
在面对记者的时候,她问,“你看得懂吗?你也看不懂吧,因为这个故事,意大利人就没弄懂。”陈薪伊所说的,“没弄懂”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在她看来,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冷酷而嗜杀的公主,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段故事(图兰朵大致讲的是一个中国公主以猜谜招亲,猜中者可成亲,猜错便处死的故事)。“所以我决定,我们的这个版本不能弄得太实,一定要虚着一点。”
“虚”指的是不确定朝代,并且模糊掉紫禁城的概念,只留下中国背景。在众多西方的版本之中,《图兰朵》的故事一直以肃杀为主要基调,从歌剧的第一句“北京城里杀人了”开始,西方对于东方荒蛮的想象就弥漫开来。而这一次国家大剧院的版本更多是想强调“爱”的主题。
“我并没想去颠覆西方那些版本中阴暗的色调、我只是想把这个故事做成一个带有英雄主义精神,爱情至上观点的歌剧。我要强调男主角卡拉夫的英雄气概和爱可以改变一切的观点。”陈薪伊说。她认为,《图兰朵》这部歌剧最初的诞生,是普契尼借用了异邦的故事展示当年意大利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交锋。
在这样典型西方化的精神内涵中,如何在大剧院的版本中突出“中国”?陈薪伊添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代表着残酷的楼灵公主,一个是代表着爱的羽人。 按照陈薪伊的设定,将以羽人最终战胜了楼灵公主作为结尾。
这样的基调和结局安排,放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版本”背景下考虑是完全可以预想到的。
展示剧院的实力
如果说,郝维亚的续写和陈薪伊的指导都是他们对《图兰朵》的首次尝试,那么这部歌剧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舞美设计,对总监高广健已经是第五次了。
1997年,在为意大利上演的《图兰朵》做舞美设计时,高广健就明白,西方人请中国人进行创作就是要看到最原汁原味的中国味道,所以无论是舞台背景还是人物形象,高广健都有意识地向京剧靠,结果受到西方好评。
1998年和张艺谋在太庙合作的实景版的《图兰朵》,也再次把艺术空间嫁接进了现实之中。
这次国家大剧院的舞美有所不同。
“大剧院给我提的要求就是做‘中国版——中国人看着认为是中国版,而且外国人看了还得认可。”高广健心里明白,作为中国国家大剧院第一次制作自己版本的歌剧,是不可能让他过于个人地展示自己的想法,用他的话说,“让我自己玩个性是不可能的。”
在这样的要求下,高广健决定仍然用具象化的设计手法描绘出一个“中国式”的环境——他选择居庸关的经典狮子造型放在舞台两侧,突出了皇朝的威严;以汉代的白玉表现公主的纯洁;选择青铜纹样展示地宫的阴森。“我故意模糊了朝代,选择不同朝代的图样放在一起。不是我无知,而是为了传达中国的概念,故意借来最有代表性的符号。”高广健说。
高广健还有一个任务——利用这部歌剧,展示和开发出国家大剧院舞台硬件的可能性。无论对高广健个人,还是大剧院方面,这个任务都是必须做到的——国家大剧院有着国内顶尖的舞台设备,在第一部自己版本的歌剧中,展示硬件甚至是演出的一部分。
高广健说,如果没有这些外部的要求,让他发挥自己的个性,他最想做的,是一部极简风格的设计,不用具体形象,而是让观众自己想象。“但是这不可能,这是大剧院第一次做,就得做最基础的。现在的创作在这么多要求下,可以说是夹缝中生存。”
能做的,只有包装
歌剧《图兰朵》之所以被国家大剧院选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主题与中国有关。
这部歌剧本身来自一个神话故事,放到中国的背景,是因为在当年的意大利看来,中国代表着遥远而神秘的东方,与神话世界几乎等同。其实,惟一与中国元素真正有关的,是原作中包括《茉莉花》在内的七段中国音乐。而作曲家郝维亚分析后发现,这些音乐在剧中,只是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茉莉花》用在图兰朵公主上场的时候,这是歌劇的主导动机。这个故事是要剥离所有的现实生活,做成一部大歌剧的演绎方式,反映神话。普契尼晚年想突破自己,不想再写以前那样现实主义的东西,他好不容易这样,想摆脱现实,而我们现在要把它再拉回到现实里。”郝维亚说。
在导演陈薪伊看来,所谓的“中国版”,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制作的版本,有着中国式的审美,除此之外,没有太多的空间贡献给“中国味道”。
“毕竟这是一部意大利的歌剧,而且音乐主题已经定下来不可改变了。”陈薪伊说。就像乐评人陈立的比喻,“所谓的中国版就是西餐中做。因为材料就是意大利的,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包装。”
对“中国版”歌剧《图兰朵》中,从主题挖掘到舞美设计,舞台硬件设施展示,大剧院都想尽可能地一次性给公众奉献“中国水准”,同时它还担负着“走出去”、到国外巡演的任务。在诸多前提的预设下,这个由中国团队再次创作的“中国版本”《图兰朵》会有怎样的表现,目前还不得而知。
无论怎样,这次尝试使已经有百余个版本的《图兰朵》增添了一个中国情态,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大剧院版《图兰朵》创作的意义,更多地是留存进了世界版本的历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