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外商
2008-01-06赵风
赵 风
明星可以制造,外商为什么不可以制造?一个异想天开的点子,竟引发了一出阴差阳错的荒诞剧……
1. 招标外商

坞山县北靠大坞山,南临濯玉河,是个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小县。
可隔河相望的邻省天马市却是另一番景象,招商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城市就像个发酵的面团不断膨胀。
坞山县的头头脑脑们望着天马市,就动起心思,决定也把招商工作好好搞一搞。
于是,坞山县领导班子,带领各部委、各科局以及各乡镇的头头脑脑们,大车小车几十辆,前往天马市考察。从天马一回来,县里立马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会上向各科局和各乡镇分派了招商任务和指标。
文化局的招商指标是五百万。文化局局长叫詹四斤,望着这五百万指标,他搔起了头皮。
詹四斤,生着个五短身材,走起路来往上一冲一拱的,很活络的样子。他虽然没什么大能耐,但对当官还是很向往的。
他中专一毕业,就当了干部。从组长一直做到乡长。在乡下干了十多年,就要求回城。要求回城的干部多,僧多粥少,不好安排。好的科局去不了,就来到了文化局。
詹四斤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就遇到县里掀起的招商热潮,并下了招商指标。眼看其他局的招商工作都已行动起来,一会儿听说这个局招来了开兽药厂的,一会儿又传来那个局招来个开洗脚城的,詹四斤那个急啊。
特别是听说去年和他一起从乡里调回城,到铁路办当主任的巴公楚这小子,竟也从温州招了个开卡拉OK的,詹四斤觉得心里特不舒服。
说到这个巴公楚,和詹四斤可是死对头,他们曾是同一个乡的同事,前些年,两人为争乡长的位置,一直明争暗斗。后来詹四斤当了乡长,巴公楚便和他闹别扭,处处较劲作对。
去年他们又一起调回城,詹四斤到了文化局,巴公楚调到铁路办。文化局虽然穷,但兵多将广,年轻姑娘一大群。
巴公楚调到铁路办当主任,虽说升了半级,可铁路办是个挂名单位,出门连辆车都没有,只有一枚公章一个“兵”,那女“兵”虽然眉目清秀,却长了一个蒜头鼻。但这回招商,巴公楚竟跑到了自己前头,詹四斤听了,哪能舒坦?
面对县里下达的招商指标,詹四斤急得抓耳挠腮。任务完不成可不行,县里下了死命令,年底工作总结,完不成招商任务的,一票否决,财政拨款减半。
詹四斤别的都不怕,就怕财政拨款减半这条。文化局各单位工资本来就到不了位,倘若财政拨款减半,那这个局长怎么当?
就在詹四斤急得团团转时,戏工室主任胡通走了过来。这胡通原来是剧团唱丑角的,脑子活络,点子多。詹四斤到文化局虽说还不到一个月,但胡通私下里和局长早就喝了几次酒,成了好朋友。
胡通对詹四斤说:“詹局,别急,咱要招就招个货真价实的外商。”
詹四斤鼻孔一拱,说:“内商都招不来,还外商?做你的大头梦吧!”
胡通神秘地把嘴巴凑近詹四斤,一阵叽咕,詹四斤听着听着,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脸上就变成了个笑菩萨。
几天后,坞山县爆出了大新闻,说是文化局招来了一个真正的外商,叫乌尔马,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富翁,资产有几十个亿,不是人民币,是美元。
县里的头头一听这消息,就问詹四斤,此事是真是假?
詹四斤说:“千真万确!过几天,外商乌尔马就要来坞山实地考查。项目嘛,炼油厂!”
县里的头头说:“好!好!咱这坞山地面儿也不小,濯玉河水深,叫他们把炼油厂建得大大的,好好炼!”
2. 外商失踪
建炼油厂的外商说来还真的来了。
这天,詹四斤安排全局所有人员去迎接外商,各单位拉起横幅,打着彩旗,剧团的演员们化了妆,打着腰鼓,扭起了秧歌舞。
詹四斤还叫胡通到县实验小学,弄来了鼓号队。小学生们鼓着腮帮子,把那队号吹得震天响,鼓手把大鼓小鼓敲得地动山摇。市民们听见鼓号声,都涌到街头来看热闹。
不一会儿,一辆小车从省城方向开了过来。小车一停下,从里面走出一个身材很高的阿拉伯人,那人头上包着阿拉伯格子方巾,身上穿着阿拉伯长袍,罗圈胡子爬了个满脸满腮。
阿拉伯人在一位小姐的陪同下下了车,胡通扛着台摄像机前后奔跑。詹四斤紧挨着阿拉伯人,向县里的头头介绍道:“这就是乌尔马先生!”
巴公楚听到消息,也匆匆赶来,夹在看热闹的人群中看外商,他见乌尔马非常年轻,就既眼红又疑惑。他凑到县里头头身边,小声嘀咕:“乌尔马先生这么年轻,资产有几十个亿?还美元?”
县里头头一听,忙把詹四斤拉到一旁,小声问:“乌尔马先生这么年轻,该不会是……”
詹四斤耸耸肩,说:“外国人不比中国人,大老板一般都很年轻。”他顿了顿又说,“乌尔马先生是总经理,董事长是他老爸!”
“呵—”头头长长地吁了口气,放心了,指示詹四斤,“要用最高规格好好招待外商,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合同。”
詹四斤设宴招待乌尔马,县里的头头都来作陪。然后,在县城最高档的宾馆“翠云楼”订下一个大套间,让乌尔马住了下来。
第二天,乌尔马当着县里头头的面对詹四斤说,他想先到全县看看,然后再看看濯玉河。还叫詹四斤把濯玉河的水文资料拿来,他要好好研究研究。
詹四斤见昨天一天的吃喝住宿招待,就花了五千多块,现在又要他拿濯玉河的水文资料,心想:这外国人名堂多,真难弄!
胡通一见头儿的脸色,连忙扯了扯他的衣角,小声说:“詹局,就按他说的办。”
詹四斤跺了一下脚,没吭声。
县里的头头听说乌尔马要到处看看,就知道来的外商货真价实,高兴得直咧嘴,忙说:“好的!好的!就叫詹局长陪你到处看看!”
县里的头头发了话,詹四斤只得叫胡通借了辆桑塔纳,带着乌尔马在全县跑了一圈之后,又绕着濯玉河看了好几个来回。
当乌尔马望着那清粼粼的河水时,竟兴奋得哇哇大叫,和陪他一起来的姑娘又说又笑。胡通扛着摄像机,跟在乌尔马身后,屁颠屁颠地来回跑,忙得满头大汗。
晚上,乌尔马研究了一夜濯玉河的水文资料。第三天一大早,乌尔马一个人跑到河边来回晃了好几趟。吃过早饭,又找詹四斤要车,说是要再去一次大坞山。
詹四斤听说又要去大坞山,心想:这大坞山满山的烂石头,树没一棵,就连茅草也比瘌痢头上的毛多不了几根,有啥看头?便支支吾吾地好半天没开腔。
乌尔马见詹四斤不吭声,忙用夹生的汉语说:“詹局长,我真的很想再去看看大坞山,请您方便方便!”说着,把手往胸前一放,头一低,向詹四斤行了个阿拉伯礼。
詹四斤只得把手一挥,让司机把局里的破吉普开了出来。
乌尔马倒也不计较,连司机也不要,自己开着车,一颠一颠地,和那姑娘高高兴兴地上了路。
在大坞山上转了一整天,到太阳快落山时,乌尔马才恋恋不舍地下了山。下山时,他像捧着宝贝似的,怀里还抱着一大堆山上的石灰石,回到宾馆。

乌尔马走后,詹四斤怔了好半天。一想起乌尔马那兴奋的样子,就觉得胸口憋闷,便走到窗前,“哐”地打开窗户,朝着外面吐了一口气:真是的,划不来!
詹四斤掏出手机,刚要给胡通打电话,却见胡通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詹局,不好了!外商……外商不……不见了!”
3. 招商费心
外商咋会不见了呢?这话还要从头说起。
原来,那个一直陪着乌尔马的姑娘叫詹含辛,是詹四斤的女儿,在省城南华大学读大三。
当胡通见詹四斤为五百万招商指标发愁时,他忽然想到电视里正在重播一个叫作《明星制造》的电视剧。头脑活络的胡通,便想起了詹含辛,想起了南华大学。
他想南华大学是全国知名的大学,知名大学肯定有留学生。外商是外国人,这留学生不也是外国人吗?明星可以制造,外商为什么就不可以制造?我们先制造出一个外商,在县里头头们面前显摆显摆,然后想个法儿把他弄走,到时完不成招商任务,总不能怪文化局无能,将财政拨款减半吧?
胡通把自己的想法同詹四斤一讲,詹四斤当时就笑眯了眼。
第二天,詹四斤就带上胡通,驱车上了省城。头天晚上,詹四斤老婆听说他要上省城,还特意嘱咐他:“你这次到省城,一定要去看看小辛,这死丫头好像谈了男朋友,还是个外国人。如果真是外国人,看我不打死她!”
詹四斤听了心想:外国人有啥不好?我现在正愁找不到外国人呢!
詹四斤和胡通来到南华大学,兜里揣着胡通临时编的“剧本”,一进门,只见女儿手上拿着讲义夹子,和一个外国男孩走出教室。那外国男孩是个阿拉伯人。

一见阿拉伯人,詹四斤不由想起了老婆的话:莫非女儿的男朋友就是这阿拉伯男孩?
见詹四斤绷着脸,胡通就猜到头儿不喜欢这阿拉伯男孩。胡通觉得“制造外商”这事儿得指望小辛这丫头,不能让父女俩闹僵,于是,他一扯詹四斤,小声说:“詹局,这阿拉伯好哇,出石油呢!”
詹四斤“咕噜”一声咽口唾沫,忍着气,朝女儿走了过去……
詹四斤见了女儿,就按和胡通事先商量好的口径,把此行的目的说了。詹含辛听说是请乌尔马到坞山去扮外商,拍电视剧,觉得挺好玩,但她对乌尔马能不能演好外商,没把握。
乌尔马几斤几两,她心中有数。这乌尔马平日节省得很,两人去回咖啡馆,还实行AA制。逢到节假日,乌尔马就去当家教,靠打工维持学业。
偏偏詹含辛是个浪漫的女孩儿,就是对乌尔马着迷,一见乌尔马那身阿拉伯长袍,和满脸的阿拉伯罗圈胡子就“犯晕”。
乌尔马爱詹含辛也是爱得一塌糊涂,觉得这女孩儿很特别。他早就听詹含辛说过她的家乡,那儿山美水美,还有那高高的大坞山和清清的濯玉河,心中早已神往。
现在一听说要去她的家乡扮外商,乌尔马开心得差点跳起来。他从胡通手中接过“剧本”就认真看起来,一等学校放假,就和詹含辛来到了坞山。
把乌尔马安顿好的当晚,詹四斤就和胡通商量好了,等到乌尔马演完外商戏后,就想办法把他弄走。
谁知,胡通办法还没想出来,乌尔马却不见了。
4. 外商被拘
尽管詹四斤和胡通这两天一直在为弄走乌尔马挖空心思,可一旦发觉乌尔马不明不白不见了,不禁也慌了神。
詹四斤忙回家问女儿,女儿吃惊地望着他,急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而胡通则满街到处找,商场超市、歌厅舞厅、桑拿会所,转了一个遍,也没看到乌尔马的影子。
胡通找了一夜也没找到乌尔马。天亮时当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刚走进詹四斤的办公室,桌上的电话突然“丁零零”地响了起来。
詹四斤一听,电话是派出所副所长侯五打来的,说乌尔马已被拘留,叫文化局派人去交罚款。詹四斤问交啥罚款?
侯五说:“你们招来的那外商嫖娼!”
啥?嫖娼?詹四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要开口细问,对方却把电话挂了。
詹四斤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原来,昨天傍晚,侯五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人在“翠云楼”宾馆嫖娼,并提供了房间门牌号码。
这个侯五原是街头一个混混儿,一次无意间他帮派出所抓住了一个逃犯立了功,给有关领导留下了好印象。第二年,侯五就通过关系进了派出所。他工作特卖力,每天挂着个警棍,在大街小巷到处走动。没几年,竟当上了副所长。
侯五在派出所感到“皇粮”不够吃,就自己去找。当他接完举报电话,心里乐开了花:哈哈!财运来了!于是就喜颠颠地直奔“翠云楼”。
再说乌尔马回到宾馆,刚在外间沙发上坐下,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侯五就推门而入。
侯五一进门,抬眼一瞧,是个外商,不由一愣,但侯五这人就是胆儿大,管你外商不外商,你敢嫖娼,我就敢抓!
侯五在外间看了看,又一把推开卧室门,见床上躺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女孩。那女孩一见警察推门而入,慌乱地把被子往身上一盖,钻进了被窝。
侯五走到乌尔马面前,“嘿嘿”一声冷笑:“乌尔马先生,请随我到派出所走一趟!”
乌尔马跟在侯五身后往里一看,见床上突然多出一个女孩,大吃一惊,又见侯五要他到派出所去,便说:“警官先生,我……我不认识她啊……”
可侯五哪容乌尔马分辩,强行将他带进了派出所。
抓回乌尔马一审,得知他竟是詹四斤从南华大学请来的留学生,侯五心里亮堂了:这詹四斤胆敢弄个假外商来糊弄县里头头们!
侯五顿时乐开了花:哈哈!爷们这个月正好缺钱花,现在天上掉下馅饼了!
这时,侯五正跷着二郎腿,坐在办公室里静等詹四斤送钱来。可等了半天,文化局也没来人。侯五又打电话催交罚款。
詹四斤瞪了胡通一眼,问:“多少钱?”
胡通伸出巴掌说:“一万五!”
詹四斤一听这数字,惊得浑身一颤:“怎么要罚这么多?一般罚款不是三千吗?”
侯五“扑哧”一笑:“中国嫖客罚三千,乌尔马可是进口嫖客,非得一万五!”
詹四斤气得朝胡通吼道:“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一万五你自己想办法,局里没钱!”
胡通吓傻了:妈啊!我就是一年不吃不喝,也凑不齐一万五啊!
胡通急忙去找侯五。好说歹说,差点没给他磕头,侯五才答应私了。侯五接过胡通递过的五千块钱,也不开收据,揣进兜里,然后,放了乌尔马。
乌尔马从拘留室出来,但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派出所。他看过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也要讨个说法。
乌尔马要说法,侯五脸就白了。
侯五抓过不少中国人,但没抓过外国人。中国人被抓,只有自认倒霉,乖乖掏钱了事,哪会要说法?
可对付外国人,侯五没经验。
侯五在屋子里团团转,一时没了主张,就冲着胡通吼。胡通听他一吼,就往文化局跑,找詹四斤讨主意。
詹四斤哪里拿得出什么主意,只好把胡通大骂一通。之后,就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跑,去搬女儿詹含辛这个救兵。
詹含辛听说乌尔马被关进了派出所,吃惊地忙问詹四斤,这是为什么?
詹四斤哪敢说明事情的原委,只好随便编了个理由,然后就催着女儿赶去派出所。
见了詹含辛,乌尔马总算同意不要说法,出了派出所。第二天,乌尔马就和詹含辛登上了返回省城的汽车。
5. 外商来信

望着阿拉伯人和女儿上了车,詹四斤松了一口气:外商我招来了,却是别人赶走的。尽管到现在他也没搞清楚究竟是谁瞎举报,错将乌尔马抓进了派出所。但那减半的财政拨款,总算是保住了。
詹四斤不禁在心里暗暗感谢那举报之人。但转念一想,他的心又提了起来:万一日后县里知道真相,可咋办?看来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
果然,第二天,县里头头就问詹四斤,好不容易招了个外商,为什么没呆两天就走了?
詹四斤那敢说出真情,只得支支吾吾地说:“外商好像是嫌咱这地儿环境不好吧?”
头儿说:“啥环境不好?咱这软环境、硬环境好得很呐,政策优惠着呢!要不,你再去找乌尔马先生谈谈?”
“好,再谈谈!再谈谈!”詹四斤答应着出了县委大院,抹了抹头上的虚汗,他哪还敢再去找乌尔马?
转眼就到了年底,县里招商总结,文化局倒数第一,得了个黄牌警告。幸亏有个乌尔马抵挡了一阵,县里财政预算时,才没减文化局拨款。
但到年关时,侯五拿了一大摞发票,要詹四斤报销。詹四斤一看,近万把块,心里一沉,但又没办法,把柄被人抓住了!
詹四斤气得手打颤,拿起笔签字,笔尖把发票给戳了个对心穿。
侯五一走,詹四斤想起胡通,觉得都怪这唱丑角的!刚好这时,胡通也进来找他签字。詹四斤把脸一绷,说:“签啥字?”
胡通支支吾吾地说:“前……前几个月,我帮外商交……交了五千块钱的罚款,你看……”
胡通话没说完,詹四斤就大吼起来:“出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有脸找我报销?”
胡通碰了一鼻子的灰,只好转身退了出去。见胡通垂头丧气的样子,詹四斤心里又有些不忍:“回来!”
胡通一回头,詹四斤说:“先把发票放在这里。”然后便对胡通交代,要他把侯五的事好好处理一下,不能让这家伙像个牛虻似的,老叮着文化局这头牛背。
不知胡通是咋弄的,反正县里终于知道了外商之所以离开坞山,是因为侯五把他当嫖客,给抓进了派出所。县里头头很生气,把公安局长叫去训了一通,并说,此人要严肃处理。公安局长挨了训,窝了一肚子火,回来就把侯五的副所长给扒了。
等到寒假时,詹含辛回到了坞山,一进门,就交给詹四斤一封信。詹四斤问:“谁写的?”
女儿说:“你自己看吧。”

詹四斤打开信封,信是乌尔马写的,再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为啥?
原来乌尔马是个真外商。乌尔马的父亲老乌尔马是个有眼光的商人,早就盯上了中国这个大市场,见儿子喜欢汉语,就把他送到中国留学,让他熟悉中国国情,为日后打入中国市场做好准备。
乌尔马来中国不久,就爱上了詹含辛。但乌尔马的父亲对他要求很严,除了基本生活费外,零花钱得让他自己挣。
所以詹含辛一直以为乌尔马是个穷光蛋,但她做梦也没想到乌尔马家族的资产,真的如同胡通瞎编的那样,有几十个亿,而且是美元。
上次来坞山,乌尔马当天就看出,詹四斤请他来,并不是在拍什么电视剧,但其动机究竟是啥,却搞不清楚,他也不想搞清楚。
但乌尔马对大坞山和濯玉河确实很感兴趣。他研究了濯玉河的水文资料,知道这濯玉河水位很深,直通长江黄金水道,可以建个深水良港。而大坞山上的石头,则是生产水泥的上等原料。
他经过几天调研,搜集了不少大坞山和濯玉河的资料,正准备回国一趟,向老乌尔马汇报,并想请父亲也来坞山实地考查一下,在坞山建个大型彩色水泥厂。
谁知,就在乌尔马准备在坞山大干一场的时候,侯五竟把他“请”进了派出所,这让乌尔马很伤心。要不是詹含辛出面,乌尔马定要打赢这场官司,讨个说法……
看到这里,詹四斤的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瞎了眼,竟把个已经引进门的亿万富翁,给硬生生地逼跑了。
詹四斤当天就想去省城,再次把乌尔马请回坞山来。
可女儿说:晚了,晚了!乌尔马早回国了。
6. 鱼鳖争斗
再说侯五,他早就盯着正所长的位子了,可如今连副所长也被扒了。他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出,心里恨死了詹四斤:要不是这家伙弄个假外商,自己哪能落到这地步?
侯五跑到文化局,要找詹四斤算账。可一打听,詹四斤出差去了。侯五气得牙痒痒,便跑去告了他一状。
詹四斤出差回来,还没下车,就接到县里头头的电话。詹四斤满肚子狐疑地走进头头的办公室。
就见头头脸色铁青,指着他大发脾气:“你詹四斤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弄个留学生蒙骗县里!”
一听是这事儿,詹四斤松了一口气,忙说:“是谁说我招的是个假外商?乌尔马先生是货真价实的外商!”
头头更来气了:“到这时候你还嘴硬?”
詹四斤说:“不是我嘴硬,乌尔马先生是个留学生不假,但他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外商!领导要是不信,我可以拿出证据来!”
詹四斤说完,就急匆匆回家,拿着乌尔马的那封信,又赶回到县委大院。
头头看完乌尔马的那封信,好半天没作声,然后打电话叫来了侯五。
侯五一走进头头办公室,见詹四斤低着头,坐在那儿,心里不禁得意起来:哈哈!詹四斤,你也有今天!
头头看完侯五当时审讯乌尔马的笔录,一时拿不定主意,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便沉着脸对詹四斤说:“你必须尽快地把那个阿拉伯人给我找来,不然……”
詹四斤和侯五各怀心思,走出县委大院。
詹四斤心想:得赶快把乌尔马请回来,不然这头上的乌纱帽就要被风吹走了。
而侯五万万没想到那个阿拉伯人竟真的是个大富翁,心想:倘若让詹四斤把那阿拉伯人再次招到咱坞山来,真的在坞山建起个彩色水泥厂,那自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詹四斤一回到局里,就连忙给女儿打电话,得知乌尔马已经回到了学校,便连忙借了一辆桑塔纳,急匆匆地往南华大学赶去。
侯五一边往派出所走,一边想:自己错把那阿拉伯人当嫖客抓了起来,虽说狠狠敲了詹四斤一笔,但眼下如不赶紧采取补救措施,惹恼了县里头头,自己今后只怕没得好混的了!
侯五走进派出所,一见院里那辆警车,顿时心里一动:有了!何不抢在詹四斤之前赶到省城,把那阿拉伯人请回坞山。只要能把乌尔马请回来,那就是大功一件,到时头头一高兴,自己想当个所长还不是小菜一碟?
想到这儿,侯五一伸手,拉开了车门,钻了进去。
侯五开着车,把警笛摁得“呜呜呜”直叫,一路风驰电掣地驶出了县城。
可一上到去省城的国道,侯五心里不由又打起了鼓:自己曾得罪过那阿拉伯人,我这一去,能把他请回来吗?
想到这里,他不由恨起了当初那个举报人。该死的,都怪这人多事,如今害得老子像个被人驱赶的老鼠,一刻也不得消停!
侯五边开车边想,可是一出县界,路况逐渐平坦,侯五的心情就渐渐变得快活起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老子先赶到省城再说,至于事儿能不能办成,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么想着,侯五一加油门,警车一溜烟地在国道上飞驰起来。只见他一边手握方向盘,一边还嘟着嘴巴吹起了口哨《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吹着吹着,警车就驶入了邻县一个交叉路口。
这路口在一个下坡处。这时,只见侯五的车头往上一抬,紧接着就车身朝下,向岔路口猛冲而去。谁知快要接近路口时,一辆吉普车从斜岔里的一个加油站爬上了主干道。
侯五一看吉普车,好像是文化局詹四斤那辆破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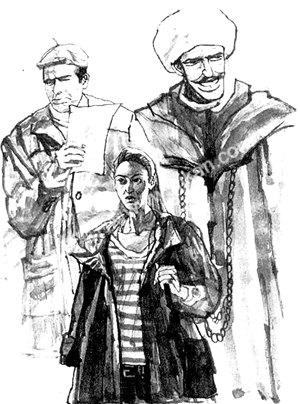
一见吉普车“吭吭哧哧”地在前面爬,侯五不由心中一喜:幸亏有远见,看来詹四斤也是去请那阿拉伯人。但他那辆老爷车哪跑得过老子的警车?
侯五这么一想,当即加大油门,朝吉普车猛冲过去。到了跟前,侯五猛按喇叭。不料吉普车不让道,还在路上扭来扭去,不让他超车。
侯五生气了,口哨也不吹了,用手拍打着方向盘,骂道:“詹四斤,你找死啊?”
其实,侯五是骂错了人,这会儿坐在吉普车里的并不是詹四斤,而是铁路办的巴公楚。
巴公楚咋会坐在文化局的吉普车里呢?
原来,当巴公楚亲眼看见詹四斤招来一个外商时,就觉得闹心,总想挫挫詹四斤的锐气。
那天,是他让蒜头鼻躺到乌尔马的床上,然后就给侯五打了电话。
乌尔马走后,他听说乌尔马原来是个冒牌货,顿时喜得他胡子翘上了天,心想:詹四斤,有你好瞧的!
谁知,巴公楚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前天他的一个在天马市工作的亲戚告诉他说,自己正在联系一个阿拉伯外商,这外商叫乌尔马,是个亿万富翁。
巴公楚一听,惊出一身冷汗,心想: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原以为那阿拉伯人是个假货,谁知是个真外商,万一今后县里知道当初是自己给侯五打的举报电话,那还得了?
等亲戚一走,巴公楚连忙打电话给他在文化局开车的姨外甥,要借车子一用。他想抢在亲戚之前把乌尔马弄到坞山来,将功补过。
姨爹要车,姨外甥哪能不从?他见詹四斤借了一辆桑塔纳去了省城,就把局里那辆破吉普开出来,送巴公楚上省城。
当然,巴公楚也知道侯五和詹四斤都在打乌尔马的主意,此时,他见侯五在后面拼命想超车,哪能给他让道?
侯五见吉普死活不让道,不由火了,心里暗骂:就算把你挤到路边摔死,老子也要超过去。
于是,他一扭方向盘,强行超车。眼看就要将吉普车逼到路边,哪知一辆桑塔纳从省城方向急驰而来。
刚好这时,路面有个急转弯,三辆车同时来到转弯处,桑塔纳司机哪知道前面的吉普车和警车在国道上表演“秧歌舞”?毫不知情的他还是一个劲地急驰而来。
侯五见对面突然来了一辆桑塔纳,暗道一声不好,急忙伸脚去踩刹车,不想忙中出错,竟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警车朝前猛冲过去,只听“咔吱吱”一阵闷响,警车和桑塔纳的“肚皮”做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桑塔纳被撞到半空中打了一个翻身,四轮朝天,“扑通”一声,摔到了路边的秧田里。
侯五的警车虽说没滚下路面,却一头撞向了路边一块水泥墩上,车头撞了个稀巴烂。侯五经这么剧烈的一击撞,撞得五脏六腑都挪了位,脑袋上也撞起一个大青包。
再说文化局那辆破吉普,当司机从后视镜里见警车强行冲过来时,顿时惊得急忙一扭方向盘,哪知用力过猛,虽说避过了警车的冲撞,但车身却朝路边护栏冲去。吉普车撞倒护栏,打了几个翻身,“咕咙咙咙”滚到路边长满茅草荆棘的斜坡下,顿时散了架。
车里的巴公楚好不容易从坡下爬上来,只见他衣服挂成了渔网,脸被荆棘划开了一朵花,血水流了个满头满脸,活像戏台上的小丑。
这时,侯五也从车里爬了出来,一见巴公楚,心想都是这混蛋惹出来的事,不由怒从心起,冲着巴公楚大吼:“没长眼睛啊!咋不给老子让道?”

巴公楚心里比他还气,回吼道:“你找死啊,想拉着老子垫背还是咋的?”
两人正吵成一团时,桑塔纳里的人也从秧田里爬了起来,只见他满身泥水,成了不折不扣的大花脸。巴公楚和侯五细细一看,这人竟是詹四斤?!
詹四斤狼狈地爬上路面,坐在水泥墩上喘了一会儿粗气后,瞪着侯五,仰天长叹道:“侯五,侯五,你干的好事啊!好端端的一个外商,硬是被你逼走了!”
侯五吼道:“这能怪我吗?”他一指巴公楚,“要怪就怪这混蛋,是他瞎举报的!”
尾声
詹四斤虽说早巴公楚和侯五一步赶到省城,但女儿却说乌尔马到外地签合同去了。
刚好这时,文化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要他马上回去,因为县里听说,又有一个大外商落户天马,要组织全县各级干部到天马去参观考察。
谁知到了天马一看,那个大外商不是别人,竟是乌尔马!县里头头气得差点当场昏过去。
从天马回坞山没几天,县里就给了詹四斤留党察看处分,把他调到铁路办去管蒜头鼻。
巴公楚重新回到原来的乡镇。
而胡通不等县里处分,便自动辞了职,到南方一家小报当记者去了。
至于侯五,职务早就扒了,由于私自驾警车酿成车祸,毁了三辆小车,被开除了公职。不过,这回他倒没去重操旧业当混混,而是在濯玉河边开了一家小餐馆。
陡然从年轻姑娘成群的文化局来到铁路办,成天面对一个蒜头鼻,詹四斤心情郁闷极了。
这天,他踱步来到濯玉河边散心,无意间走进了侯五的小餐馆。来的都是客,这时的侯五,竟自动放弃前嫌,笑容可掬地把他迎到桌旁坐下。
詹四斤刚一坐下,巴公楚恰巧也晃了进来。
三个昔日的冤家对头,大眼瞪小眼地看了一会儿,然后竟像老朋友一般,一齐坐到了桌旁。
三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朝濯玉河望去,只见河对岸那家彩色水泥厂上空,“咕嘟咕嘟”地冒着白烟;到大坞山上运水泥石料的船只,在濯玉河中穿梭而行。
望着那烟,那船,詹四斤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说:“唉—本应建在坞山的水泥厂,却跑到天马去了!”
巴公楚和侯五也跟着长叹一声:“唉—教训呀,教训呀……”
(题图、插图:杨宏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