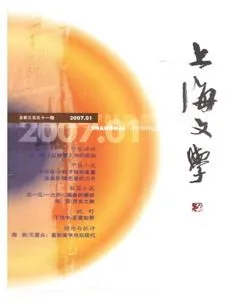一些奇奇怪怪的或庄重的事情
2007-12-29安妮宝贝陈村
上海文学 2007年1期
时间:2006.8.21
地点:北京某饭店
安妮宝贝寓所
陈 村:你写的那个《莲花》和前面有些不一样。我蛮喜欢《莲花》,觉得《莲花》比前面要大气。安妮宝贝(以下简称安妮):这本小说对我写作的七八年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它是一本有清洁感的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同类。它是有一种孤立的气息,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的。
陈 村:你比较好,你比较安静地在那写着。有些人呢安静地写,有些人呢安静地不写。
安 妮:我是韧性比较强大的人,习惯一心一意地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这七八年下来,也觉得挺难的,很多的误解是非包括被贴在身上的种种标签,如果心里不是有一股蛮劲,人肯定会被改变。写作也会成为一件复杂的事情。但我是坚持要把写作当作一件单纯的事情,只对自己发生的,一件单纯持续的事情。即使到现在,外界所持的态度都需要自己来担当。《莲花》出来后我去书店,会看到一些书店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很庄重的书,会把它放在学术类的或者艺术类的书一起来做推荐,因为《莲花》整体设计是清雅大方的,它是二一本认真的小说。有些书店依旧会把它往流行小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书里这么一放,因为他不读你的书,他就按照媒体标签来看你,觉得你畅销,那么写的肯定是商业化的东西。书一旦畅销,别人的心态里就会有奇怪的东西,他不再愿意客观地来理解你评价你,完全忽视一本作品的内涵和价值。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人,有时候会对这种粗暴很气愤,尤其对《莲花》,现在书的市场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确很多,但《莲花》是不一样的,它是这样清洁的书,依旧在被误解。
陈 村:就让它去吧。哪里还管得上那么多呢。没办法的。
安 妮:作者的变化只有读者知道,在读书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写信给我,写来很长的读后感。我的读者是些很细腻的人。我的小说风格太明显,所以一贯是喜欢的会持续稳定地喜欢下去,不喜欢的根本就拒绝尝试对它有一点点的了解。
陈 村:你不理会就行了。没有精神也没本事跟那么多人要说服他们。
安 妮:吃鱼吧,趁热吃。
陈 村:你平常出去,不大出去?
安 妮:平时不太见人。我一个人在家里呆得住,看书,养猫,种花,做饭……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对事物的温度,比对人的要高。因为能够交流的人,其实也不多。真正能在交往中把你往上提高的人,是很少的。但最近出去还是多的,比较闲,所以有时候朋友开的书店里办讲座,比较有意思的我会去听一下。前两天很好玩,我认识一些易经算卦和懂得西方占星术的人,对这种东西比较感兴趣。懂易经的那个人很有意思,住在北京闹市区里,但和他妻子似乎是与世隔绝一般地生活,隐士一样地生活。日子过得安静恬淡,整个人显得神定气闲。我喜欢这种似乎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他们的心在另外一个空间里。我也算了几卦。
陈 村:相信这些?
安 妮:我对那些玄妙的东西都很感兴趣。就跟我对天文、地理、植物学等学科有兴趣是一样的。
陈 村:你自己觉得算得准吗?
安 妮:算得挺准的。把以前的事情也都算出来了。
陈 村:那看到这种人很可怕。
安 妮:你觉得很可怕吗?他是用很理性的原理来计算,不是按照灵性感觉凭空猜测。比如占星,命盘是用电脑推算出来的,这个事情是科学。不是他有特异功能,能看到你的命运。他就是掌握一个技术能帮你推算。易经也是,每个卦都有个解释,但这个解释空间很大,可进可退,实在是很智慧。我最近就是这些活动比较多。老是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我喜欢结识这些行业比较特殊的人。
陈 村:称作演算。我不相信这个,也有人给我算命。算了我也不相信。坚持不相信。我不相信别人给我算命。因为以前的事情我总是知道的,因为以前经历过的。以后的命怎么样就随它去吧。给我算好什么时候要死啊,什么时候发财啊,没用。糊涂账蛮好的。什么都算好,什么今天中午要在这里和你吃饭,还吃的是虾。这样就不好玩。
安 妮:哈哈。也是。
陈 村:我在上海很少出去。有时候出去无非是跟孙甘露啊小宝啊一些坏人一起吃饭。
安 妮:你们都是很多年的朋友。这样很好啊,可能还是年代不一样,你们的年代可以积累起朋友。
陈 村:而且那都是很多年的人。你想孙甘露我有一张照片抱着我女儿。过两天我女儿马上20周岁了。你这个人太敏感。
安 妮:我非常敏感,对外界,对人,对自己,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会被敏感所累,有间歇性的比较强烈的抑郁,内心总有波动,所以时时需要用反省和自控来平衡它。写作的人大概都会这样。
陈 村:人傻头傻脑的好。傻头傻脑,生活里面不会弄得自己很难过。你不上论坛是好的。论坛是害人的地方。
安 妮:我很少上网,从来都不在论坛浪费时间。主要是不喜欢和别人辩驳,每个人的观点可以允许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对错标准。但有些人就是觉得要驳倒对方,显示自己很准确,我恰恰觉得那是没有底气的。探讨何来准确与否,有底气的人也更可以海纳百川。论坛上很多这样浮躁自以为是的人,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水平。网上我不反驳别人,网下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在播下各自的种子,然后得到那些因果。上海现在过去得也比较少。有时候过去也就是过路,一两天,然后就很快就走了。最近一直都没过去。对上海感觉可能就慢慢远了。还是想去云南或者其他的地方住一阵。
陈 村:如果我年轻一些身体好一点,我就带一个笔记本电脑带个相机。我在云南住两个月,挪动一下,到成都住两个月。看看朋友。
安 妮:如果要做事情,可做的其实很多,但是我有时候会什么都不做。我容易情绪反复。上次去占星,那个人说我最大的负面是没有安全感,老是寻求这世界上不存在的安全感,像是回到母亲子宫里的安全感。他说我很矛盾。一方面我是个生命力强盛的人,新鲜求知,总是在积极探索外界的真理和科学,很有好奇心,但一方面又特别没有安全感,总是想缩回到自己的内核里面。也许人再长大一些,性格慢慢会好一点。我希望自己能够平衡,安静。
陈 村:你防止人家进入内心。不安全感呢每个人都有。一般人神经粗糙一点。你经常要对付的是自己,外界对你其实还是蛮好的。每个人也都是,自己管住自己。
安 妮:这两天在网上下载了《金刚经》的一个读颂,是和尚念的。我觉得听和看感觉不太一样。
陈 村:后来你像《莲花》里面去跑那个路,那个路很危险。
安 妮:那条路,后来觉得是生命中做过的有意义的重要的事情中的一件。它首先对我的人生发挥作用,然后又对我的写作发挥了作用。
陈 村:我的一个亲戚去梅里雪山转山。
安 妮:增进仪式感也是修行的一种。这些事情能让人获得很大的安全感,平静下来。不太焦躁。目前为止,我还是把宗教当做一种哲学,全身心信仰还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转折。
陈 村:生活太烦乱了。你喜欢北方还是南方?
安 妮:我始终都是喜欢上海的,对它有感情,只是现在感觉跟上海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每次下了机场,开到高架桥,看到大楼,心里就很愉快,觉得回到熟悉的地方,空气里的湿润都让人高兴。如果能找到一个上海男人我就回去了(笑)。但现在想想在北京是不大会碰到上海人的,除非你还是回上海。我没有动力回去。找到一个动力就回去了(笑)。
陈 村:我跟阿城聊的时候就聊到家的问题。有时候父母是家,孩子是家,你的爱人就是家。有的时候你要出去走,有时候要回去的。其实在一个地方,有你亲人,有朋友什么的,你在这个地方比较安静。
安 妮:其实有些朋友在或者你能在那里呆下来的,都是家。我喜欢上海,是喜欢上海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彼此有点距离感的矜持的干净的情意。这是南方人的个性。在北京你能遇见很多华而不实满嘴胡话的人,北方人的性情我不太适应。但北京外地人多,城市气氛比较开放。一回到上海,别人都说上海话,我都听得懂,但说不好,很别扭(笑)。
陈 村:本土的,王朔那样是本土的。
安 妮:他擅长纯粹口语化来写作。但南方作家不会这样。我喜欢用书面语来写。我的写作和我的口头说话是不一样的。写作要用一种明显高于生活的语言,更为雅致和脱离。需要从生活中提炼出来,但与它有距离。就是这样。你的表达要逾越生活一定距离,不能与它一个等级,语言意境想法都要高于现实生活。这样才能带给读者精神的空间,拔高的有美感的空间。这样的写作,能让人抬起头看看天空,看到日月星辰的美,而不是老盯着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心态里都是计较和庸碌。不要老是在地上打转。现在很多小说乱七八糟,搞不清他们怎么写。
陈 村:我跟你说他们是电视剧化。电视剧是把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到屏幕上去。
安 妮:现在好像用抽离客观的带有一定宗教感的态度来写作的人很少。国外的就不说了,有很多畅销小说是写得很好的。不管是技巧上还是内容上绝对要比中国当代作家好。
陈 村:总体好得多。
安 妮:但是中国的一些古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前段时间在看《礼记》。《礼记》记录一些很琐碎的礼仪,比如吃饭怎么吃,鱼要怎么来放。秋天的时候鱼肚子要朝哪个方向,夏天的时候要朝另外一个方向。它都有讲究,而且它的讲究都是有自然常识和人情世故的道理。我很喜欢这种物化的叙述。最详细的是丧葬,怎么节制悲哀,穿丧服,生死对古人来说是大事。里面有一段,是说曾子快死的时候在病床上,他儿子在旁边。还有一个小童。那个小童说,就在你旁边有块席子,那块席子又光滑又华丽,这个席子很好,你应该用上。曾子就对儿子说,这个席子是我一个朋友送过来的,你现在就帮我换上,我要躺到这块席子上去。他儿子不答应,说,你现在病很重,如果把你搬过去就会影响到身体,你就可能出危险,不能把你移动。曾子训斥他的儿子说。你对我的那种爱还不如那个小童。对一个人的好是要让他得到他喜欢的东西,最起码是要满足对方的心愿,让他高兴。而你是用你的要求来要求我,还自认为你是在对我好。训斥完以后。儿子就把他的席子换了。刚刚换好,把他放下去,他就死了。他死之前还是完成了他的心愿,躺在一个又光滑又华丽的席子上面。那段描写我看完之后就很有感触的。古时候的人很端庄,他们的想法都是很端庄的,很庄重。传统文化这一块现在被关注太少,很多人完全没有把它当回事情,又说它已经落伍了,不适应时代了,已经被西方的文明和科学冲击掉。但在传统文化里,一些好的东西是要保留下来的。包括它的待人处世,怎么看待生死看待人生的一些事物,包括对社会的理想主义的想法。这个都是财富。但现在被完全忽略和不考虑。
陈 村:现在很焦灼,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焦灼。很少思考内心,很少往深处想。
安 妮:《论语》和荀子也很好。我喜欢荀子是因为他的文笔,他的古文流畅华丽,比喻精确。荀子说明观点喜欢用比喻,而且是一连串的排比下来,但意境都很妥帖。我觉得那些文章写得太美了。文字就应该写得这样美。
陈 村:我做过两本书。做过老子和孔子。当时做的时候呢,对我来说好的,不是做了一个好的文本,好的就是因为你要工作你就必须好好去读,读一些和它相关的东西。做孔子以前我也读过《论语》,读了也就读了。工作的时候你就要仔细地读。要想一想的。
安 妮:我看《礼记》的时候,每天给自己规定要读完多少页,清晨梳洗完,泡杯清茶,坐在书桌前一本正经地读它。甚至不是躺在床上看,我把它看做是一个庄重的工作。一边读它一边翻字典,有一些词很难理解它的意思,都是古字已经消失了,就搞不清楚。我买了一本很厚的古汉语字典,那里面几乎全都能查到。碰到看不懂的字就用它查出来。碰到好的段落就把它抄下来,再以自己的理解在后面补充一些心得笔记。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就比粗粗地读一遍要好得多,更深入。把它当成一个任务读完。
陈 村:你现在还在写吗?
安 妮:我最近没写。最近就是看很多杂书,接触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是古代文化比较多。然后看看接下来写什么。下面一本可能是随笔。要等两年再写一个长篇。一年做一个长篇还是做不了,时间太短,准备不充分。
陈 村:有人就是赶着做。有人一年要写好几个长篇。我说这是自杀。
安 妮:长篇是个大工程。要搭框架,查找资料,确定各个部分……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一般早上开始写,写到中午吃饭。下午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写,一般不太中断的。中断了就气接不上,需要一个完整的持续的状态。每天的心态要稳定。最好的状态,大概每天也就只能写到三四千字。现在写作是很慎重的。知道它是有影响力的事情,是对别人有使命的。因为很多人在读你的书。
陈 村:那就不错了,每天能出产。
安 妮:其实大概四千也写不了。我想了想,一般两三千。
(两人去安妮家)
安 妮:我最近还是觉得传统文化和宗教哲学,这两块对中国的作家来说还是很重要。很难想像一个作家他对古老的文化和宗教哲学不感兴趣,他能围绕什么主题进行写作。他写作的主题能超越他所在的时代和现实生活,能有多少距离。有距离的思想,才能够客观地存在下来。
陈 村:中国的很多作家,因为我们是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很多作家就是在事后,就是写作开始之后一段时间去补课去了。
安 妮:我上次看明清笔记,看到一个小故事。有一次科举考试,大概有四五百人,等候在一个地方,那里刚好有棵大樟树。那个樟树有多大。大到能够把这几百人都遮挡在它的树阴下。这种小细节我觉得很美好很诡异,它给你提供了想像感,一种神秘的美感。就是有那么大一棵樟树。
陈 村:现在就是不一样。就是昨天和阿城讲到陶渊明。实际上陶渊明是中产阶级。他做官是一个中产阶级,他隐居也是中产阶级。他的那些诗歌里是没有对收获的感悟。要是农民写的话一定是写老天保佑多收粮食什么的。但是在他的诗歌里不是。
安 妮:因为他本身有了物质基础,可以在精神上拥有更为强大的保持恬淡的尊严和自由。他的思想可以超越现实生活。
陈 村:出这样一个人要死一百个人呢。
安 妮:昨天去参加一个摄影讲座,有人认出我来,过来和我探讨写作的问题。我就跟她说,刚刚开始写作不要抱很大的野心,提前给自己设定许多标准,认为自己要写的得跟所阅读过的喜欢的小说一样。这样的话会很吃力,因为你不一定能够写得出来,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内心支撑,内心支撑需要时间的磨练和个人的修炼。写作的初期,只能是写你的内心想写,尽量真实和单纯的内心表达。内心里面有东西在,才把它写下来。不是你的东西,你没办法写它。
陈 村:其实一开始写作就和作者自己有关。
安 妮:对。不能把写作当成一个职业计划。比如说,我今天开始要成为一个作家了,那是不对的。写作和其他职业是不一样的。其他职业可以靠经验积累,靠学习摸索,然后建立起来。但是写作,我觉得需要一个天性的底子。这种艺术工作,比如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是需要和它符合的天性。如果你做得太吃力,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本来就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是不大赞成把写作当成一个什么职业来谋生。这个是不可能的。靠写作谋生很艰难,而且会使它变形。你只能是天性里有与它的缘分,然后它是你喜欢的事情,你做了,并且做得高兴,做得顺利,它才会选择你。你不能选择它。有些读者也会来问这样的问题。写作还是一开始就把它当成一个兴趣。如果你写出来了就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如果没有写出来还是把它当成兴趣。
陈 村:有时候要有很多机会。不是说每个人都可能成功。每个写得好的人都可能成功。
安 妮:是的,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诗写得很好小说也很有想法,但是没有机会。比如我有时候给他们推荐稿子,出版社都不感兴趣的。有的稿子的确写得很好,我就给我认识的编辑说,你看一看最起码读一读。编辑会说这个小说也许不行,没有任何市场前景。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在朋友圈子里传递一下也是好的。有些事情只能顺其自然。我觉得要是我那时候没写出来,还是在工作的。
陈 村:人不要用写作把自己害死。如果说谋生压力太大的话,你写作肯定会变形。
安 妮:写作上面不能寄托太大的野心。现在很多人在写作上面附加了太多的东西。当然我谈的纯粹是我的个人观点,因为写作本来就是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方式。不要在写作这个事情上面附加太多的野心。比如想用这个小说博得别人对你的欢心欣赏,然后在书里面卖弄你的知识。的确有很多人他们看过非常多的书,他书里面会引用大量的别人的观点。黑格尔啊,康德啊,苏格拉底啊,诸如此类,他随手就会写下一段某某人这样说。基本上会用一个很大的格局,因为他想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先发制人地给你一种气势感。往往这样的恰恰就是大而无当的。有力的东西它一定是简洁的。不需要你摆弄那么多花头绕来绕去弄出各种理论,然后引用很多名人名言再能说出你的观点。肯定不是这样。准确地有力地能够打触到别人的观点,肯定就是一句话就能讲清楚。我用一个短句就能说清楚。然后读者就能知道你大概要表达什么意思。
有些人的写作干脆是为了评论家写的,他不想自己的书是否有读者,是否会有人爱读,并从中得到影响。他不在乎,他只要一个圈子里的所谓名声。但我是觉得书只有通过被阅读被流转它才具备生命力,它才拥有对别人的使命。
陈 村:用高级的词汇。大词。
安 妮:玩一些花招他以为都是他的一些武器。甩弄甩弄一会是大刀一会是红缨枪,那出来别人就服他了,其实他根本没有自己的绝活,这样的人不是高手。前段时间我读了汪曾祺的一个短篇小说,好像叫做“少年,昙花,鹤”,好像是这个名字。很短,但是很优美洗练。句子简洁和清爽。它的事情,就是一个少年从早上到晚上一天遭遇到的事物。他看到了昙花,他看到了鹤,他路过田野的时候邂逅了一群鹤。他又在竹子上面雕刻古诗。小说里头蕴含着非常清雅的,中国乡土乡村的人与自然的联系,细致入微。他的写法就是举重若轻,平平淡淡很简洁很干净地说了一些细节说了一些行程。但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就是到了一定的境界。这个就变成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似的,但他的自言自语是有很大的底气在支撑。但大部分的写作就是太重了,野心太大欲望太重,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很粗陋浮躁的。
陈 村: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
安 妮:他这么一篇我就很喜欢,其他的东西我没看。我觉得现在很多当代作家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就是很有情怀很准确的文字。
陈 村:他可以写得很清淡。自描似的。
安 妮:就是清淡的。
陈 村:但我读着觉得不如他的老师。我觉得沈从文写得最好的是《湘行散记》,他更出名是他的《边城》,这是小说。小说必须要有很多连接。但在《湘行散记》当中像素描一样的在那写着。我觉得这两个人好在什么呢,都是以淡而取胜。在沈从文那里就更自然。汪这里呢能感觉到他把枝枝桠桠是修过的,沈这里就可以泥沙俱下的很俚俗的。而且沈从文的那些文字是说不清楚是土是洋的,可以觉得很洋,也可以觉得很土很土。他而且没有技巧痕迹。他就这么说下来,但是非常舒服。今天的人,包括新时期以来的受表彰的那些小说,这些小说或多或少都和政治在呼应,或多或少是找一些“秀”的东西。
安 妮:这种形态还是依然存在的。有很多作品要寻求它的来自外界的寄托点,因为可能作者没有他自己鲜明而坚定的人格力量。怎么讲呢,作品可能分两类。一类是由作者人格力量支撑的,读者读这个书可能是读这个作者的人格,他被作者的人格吸引。但有些作者在自己的书里面是不存在自己的人格的。他需要找其他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就可能是政治或时代或其他看起来庞大的东西。他只能靠一些外物的介入。
陈 村:一开始就是错的。你刚才用了一个很好的词:自言自语。一开始写作自言自语和你写给特定的人看。昨天阿城说了一句话,说你本来是为你认识的人写的,现在是为不认识的人写的。一开始都为认识的人写,我愿意为一个女孩写一首情诗,我愿意为我的几个哥们写一个小说。你就会有一个动力。慢慢的那些固定特定的读者没有了以后,他就会去找一些这个社会所需要的题材。这些故事可能是前面的故事的一些变形。但是这些故事的理念,这些哲学不是真实的。再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很无趣。
安 妮:你看书店那么多书,有时候选择却很难。好书很少。我现在买杂书多,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很多,小说类就很挑剔,一般还是看外国小说,美国的欧洲的小说。我看小说的目的非常地明显,是拿一个东西在拆分。我拿到一个小说,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读者要进入它的世界,是要像一个手工艺人那样,自己在干活还要看别人的东西是怎么做的。现在看小说就是这个目的,拆分它,分析和总结它的整体结构和叙述上的技巧。在技巧方面外国人的确要比中国人做得好。他们的技巧精细并且有逻辑和想像力。小说本身还是需要技巧的,这个技巧对于作家来说属于自我价值的一部分。就像两个人同样在玩一样东西,我玩的姿态能比你好看,我的某一个动作能比你更得窍门。那就是很好啊。这个炫技就是需要的,但不是像有些小说它除了技术什么都没有,缺少作者自我真实的人格在里面,那样也是无意义的。最好是两者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
陈 村:中国小说系统和西方小说系统真的是不一样的。西方很多小说的系统是在他们的传统的带领下可能是哲学啊来形成的。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反思。在中国呢,我们发现可能在形式上会很接近,但是我们没有哲学,没小说后面的那些东西。
安 妮:对,是这样的。但这个其实很重要。
陈 村:对你的作品有批评的人有一部分是说,你反复去写了一些,有人说你写了小资有人说你老是说棉布的衣服木头的纽扣什么什么的,白色的裙子。
安 妮:这种评价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到要点上。我自己会知道我的作品中有哪些缺陷,但那些缺陷肯定是不在他们所指的那些东西里面。因为这些评价是表面虚浮的东西,可以说他并没有好好读过你的小说,如果你认真读完一个小说,你不会只看到里面的人穿什么衣服。那是有问题的读者。提出这种批评的人我不会听他的意见。但如果他能戳到我的要害。我会听,因为这其实是对我的帮助,是需要感恩的。但如果彼此在不同的思想层面,牛头不对马嘴,是不需要彼此对话的。
陈 村:刚才不是在说嘛,包括我这种人,我是比较早的觉得你写得还不错。但是这里面也有误区。误区是什么呢,你写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其实你的作品中实际上有意无意的呢,所写的表面生活后面有比较精神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说,就写棉布衣服,就永远可以抓住一些人。一些人认同是从心里,认同或者说书中的状态引起了他的什么想法。我是在想,在你的作品中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天生的还是什么,你比较敏锐的就是你表述的这些东西。在以前的作品中,要去这样地表述年轻人生活态度也罢,他跟周围世界关系也好,都是缺乏的。这些是你作品中有价值的东西。
安 妮:每个写作者关注的面不一样。我会关注人在生活中的困境,他的思想,情感,情绪,心理上的各种困境,因为你得写真正来自内心深处的东西,它们是客观的永存的。每一个人都站在他自己的悬崖边上,不管一个人出来多堂皇,看起来多风光,显得很高兴,但他会独自生活在他自己的黑暗里面,没有人可以帮他承担和解决。每个人的生活背后都有缺陷存在,这个缺陷很难靠自身能够得到完满的。可能是破损的或者分裂的脆弱的。它也许跟宗教有关系。我自己对这块东西比较敏感。我对其他表面化的东西不感兴趣。宗教还是试图让人达到完满,试图带来超越,平静,摆脱掉肉身和宿命带来的控制。人其实是很卑微的,今天出生了过几十年就死了,当中做了一些自以为很了不起的事情。人本身来讲还是应该看到自己身上无能为力的,看到自己身上残缺的,也没有可能靠自身来修复的东西。需要更高的一些东西。能够压制超越这些表象的东西。我自己写小说还在学习。人如果老沉浸在表象上是得不到超越的。每天都发生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有什么意义呢,它无非就是一种表象,演变出来的各种苦难各种各样的痛苦的形式。人应该怎么样做一些事情,真正为人类做一点事情。让你身边的人要让他们有自觉,最起码让他们心里有一些清醒,要想一想自己和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包括你和你自己生命的关系。我觉得这些表达都很重要,即使也无力得到正确答案。但如果写作要有使命感的话,无非就是用你的书来影响别人内心的东西,让他变得敏感和清醒自知,更洁净更有勇气,而不是被生活繁荣或痛苦的表象轻易地压制住。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有一种使命感的。你说写作一定要为政治为国家做点什么这个也很难,要为整个时代作出贡献也很难。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个个人活动。它只能对人的内心产生影响。
陈 村:是的。
安 妮:那种重复的事情就没必要做它。就像大部分稿我都不写。但是如果我有某些机会去做一些跟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而且会带给我改变的一些事情,那我愿意付出我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是一个质的变化,而不是一个量的不断的重复。
陈 村:有些事情也让人兴奋的,我没有做过的,试试看能不能做。我现在就很不对头。我有时候宁愿发帖子。发帖子又没钱没名利。
安 妮:但有你的新想法。
陈 村:我觉得很直接,有新的想法就写了贴掉,还要等你发表等几个月我就不愿意。而且在那里呢可以比较放肆。如果我用很多不规则的方法去写作的话,编辑要找我麻烦。我也懒得去争辩我为什么要这么写。日子过得很快。
安 妮:是的,日子过得快,但有时候我也没觉得压力很大,因为可以找到一些奇怪的有趣的事情来做,也可以一直在写作。每个人必须要背负属于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一个人一年能把一两件事情做好,就很足够。做单纯有力的事情,一直持续,一直创造,是抵挡空虚最好的方式,就跟古时候那些手工艺人或者画壁画的僧人一样。写作就是一个作家的手工艺活。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