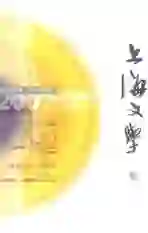把文字唤醒
2007-12-29张炜
上海文学 2007年5期
三十年前的读与写
1990年,明天出版社曾经出版了我的小说集《他的琴》。这不是我出版的最早的一本书,却是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其中最早的一篇小说《木头车》是1973年写的。严格地讲,它才是我最早的一部作品集。它概括和代表了我三十多年前的阅读和写作,等于是那一段写作生活的全部。
对我来说,当年的阅读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一件事,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当时在一片林子里,别说是图书馆,就连接触人的机会都很少。只要传到手里一本书就感觉珍贵得不得了。有时候得到一本喜欢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晚上睡觉还要把它放在枕边。
后来能看一点儿翻译作品,中国古代的书,如《红楼梦》,还有一些武侠书,一些革命作品。很少。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鲁迅的散文集《野草》,封面暗绿色,上面画了紊乱的野草。当时我不能说完全看懂了这本书,但能感觉它的深沉和美。那是我小时候读的惟一的一本鲁迅的书。后来读了巴尔扎克的书、妥思陀耶夫斯基的书——他有一本《白痴》,让我怎么也读不懂。几乎所有的字都认得,却读不懂。
当年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连收音机都很少。我们最信任最依赖的,就是纸上的文字,是阅读。我们对文字本身有一种神秘感和敬畏心,有一种追究和探索。比如书中自然段的划分吧,这对我就很神奇。为什么从这里分开?依据是什么?方言、儿化音、生僻字,都让人心向往之,都要问一个究竟。我们对于文字、对于印刷品,真的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敬重。所以我们很理解中国古代“敬惜字纸”的说法。我们对文字有情感。
我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学习写作的,文学之路就从这里开始。
今天,打开一部当代文学史,会发现一连串的名字,这些人出生在四五十年代,或者稍晚一点。他们就是在我熟知的那样一种气氛下阅读和写作,进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人。和现在的许多文学起步者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对文字有过那样的一种情感,并且一直继续下去。他们比后来者更依赖文字,有一种叩问和求证的精神。如果一个字、一句话写错了,很难宽容自己。
最早的文学开始大多写诗,我也一样。因为一些长短句子、押韵,很符合少年的文学冲动。我写了大量的诗,再后来才是写散文、戏剧、报告文学,最后是短中长篇小说。这种文学训练的过程,好像是各种体裁都尝试一遍,并且由诗进入。对诗歌的这种迷恋和爱好,对我意义重大。我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写短篇为主,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诗的写作。诗对于语言、意境、音乐性,有一种更高的追求,它对一个人文学道路的牵引力是最强的。现在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在社会上的阅读量很大,在文学中占的比重也很大。但是诗仍然在我心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
我永远不会放弃诗的写作,可能一生如此。很早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几岁吧,那本唯一的、也是著名的诗刊要刊发我的一部组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消息。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形势及其他诸多原因,组诗不能发了。这又令我多么沮丧!如果发出来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努力地写诗、一直这样写下去吧。
诗给了我巨大的馈赠和恩惠、巨大的满足。它给予的那种幸福感让我不再忘记。我不是诗人,可是我永远忘不掉诗,永远忘不掉在散文和小说中把诗人的热情一点一点、不曾间断地释放出来。
初中毕业后无学可上,我们一帮同病相怜的失学少年聚在一块儿,发了疯地模仿起一些大诗人的作品,不停地写起了长诗。没上高中非常痛苦,我们把对文学的理想和信念,以及没有升学的愤慨,全部寄托在长长的诗句之中。
我们那一代人对于文字的信赖,对于书本的痴迷,是现在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有人也许会问:你今天,还会把自己喜欢的书放在19ec65a1bc0db2a16769f764dfddf78ae77154602f73deb9b82e195e8105b814枕边吗?是的,但更多的是放在一个很小的柜子中,我只把自己最喜欢的书藏在里面——而我的大书架子上,却有成千上万、几万册的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从小柜子里摸出一本书,这本书会让我获得持久的幸福。我读了十遍或更多,仍然入迷。这种让我不能舍弃的书大概有四五十本,都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只要你对书的情感仍然停留在三十年前,没有泯灭,或迟或早都会找到这样一些书,把它们放到枕边——或是类似的什么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地方的。你在不停的阅读和筛选的过程中,会慢慢地变得心里有书了。
有人说,你的那只小柜子里可能百分之八十是小说吧。不,里面的小说连一半都不到。理论书,科学家的书,宗教书,什么都有。
现在有不少孩子想当作家。为什么?其中有的出于挚爱,有的却认准了这是一条名利之路。他们不是因为作家伟大,因为文学可以为自己的民族镶上一道金边,不是怀着一种敬畏做出了这个选择,不是。他们没有心怀崇敬和自豪去爱文学,满脑子就是怎样畅销、怎样出名。他们对于阅读的迷恋,对于文字的依赖和忠诚,根本没有;至于对词汇和语言的执著与敏感,还有起码的专业忠诚,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人从哪里出发是不一样的,这与他最后能否抵达,是关系重大的。
我们那时候对于写作的爱,基本上无关乎名利。所以我们能够迷于文字。我们是如此认真地、反复地推敲它们。如在一个自然段里,我们不能使用同一个词,甚至不能使用同音或相近的词;在同一句表述中,不能重复同一个字或同音的字。还有音调和节奏:我们写出来以后不知要读多少遍,默读,从声音、平仄上感受它是否悦耳。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意思表达得清楚,还要让其有一种好听的韵律,所谓的一唱三叹。诗就是讲节奏的、有音乐感的。词与句的对错是一回事,讲求它的音乐感又是一回事。我们对自己的文字养成了极其苛刻的习惯,追求高度的完美。不仅用字要准确,而且还要求字形优美。同一个意思的表达,可能还有选择什么字的问题。有的字的样子不好、用在这个地方显得很丑,那就要更换。有人说汉字还有丑俊吗?有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怎么会没有丑俊?还因为词序的排列、语境的问题,有些字就得被苛刻地挑拣。还要考虑到字的直观表意性质,比如说“倔犟”,我一定要用带牛字的“犟”,因为我心中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牛”劲的。
我们当年觉得作家是最了不起的职业,最不可思议的人物。那是人生的神秘吸引,而不是过生活的一条路。这种概念是怎么形成的,一时难说,但我们的少年时期就是无比地钦佩作家,就是要仰望和追求。也有人非常钦佩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我们选择的是作家。作家伟大而奇特的灵魂、语言的能力、丰沛的诗意,他为一个民族提供的思想和意义,负载的荣誉;他的可记载性、在文明史上的地位,是这一切吸引了我们。
我从未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是一个作家。因为这个概念在心里形成得太早,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一个爱好者。
三十年前我们绝不敢如此轻浮地对待一个称号。我们的阅读和写作还笼罩在一种神往、勤勉、追求的气氛当中。这种气氛已经成为记忆,它不但至今难以忘却,而且还将伴随我们走得更远。
何为文学阅读
现在打开网络,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写作。快速的浏览式的阅读,来不及在闪烁的光标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没有这种耐性,也没有这种信赖。作为网络写作,他们甚至认为看得懂就可以了,句子对错无关紧要。既然如此,读者的仔细和缓慢也就太划不来、太傻了。一掠而过最好,或者根本就用不着看。
就这样,阅读受到了伤害,进而又伤害了写作本身。今天的读与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一个时期,一个民族的语言状态和言说方式,表现和印证了这个民族的特质,其内涵、情态、信心和力量等等,都从中显现出来。这个民族是否认真,有无恒力和定力,有无追求的意志,都能够从集体的言说方式上得到表现。
语言的演进有一个过程。中国的新文学发展从白话文开始到现在,虽然受到大量翻译作品的影响,经历了不断的演进和变化,但仍然植根于中国古代经典。它一路跟着新的社会发展下来,成为活的、变化的、跃动的和生长的,在一天天前进。它成了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最精炼最灵活、也是最有生命力的表述和概括,是一个民族语言的牵引,是一个民族语言的奔跑。所以文学的语言直接影响到一个时期新闻的语言、一般的生活用语,甚至影响到公文写作。相对枯燥刻板的公文是在文学语言的牵引下,缓慢而又谨慎地往前行走的,它需要在等待中接受最新的表述,包括一些词的使用。
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杰出作家使用的句子和词汇,以及他们的言说方式,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到达一般的作家那里;再过两三年即到达新闻媒体和学生作文中;最后,又是两三年之后,就开始出现在公文当中。这就是语言演进的大致轨迹。当然,再杰出的作家也要向民众、向生活的各个方面吸纳语言,但是最终的概括和升华,是完成在他的手里。
我的意思是说,网络和繁杂的通俗劣质传媒,破坏了一个民族在语言方面的正常演进,造成了整整一代人、一个时期无法深入准确的表述,进而失语,对人们的心态和思考形成负面影响,积成了实际生活中的创造障碍。因此,如何唤醒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文学阅读、理解文学阅读,就成了整个民族的、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
现在人人都痛感浮躁对人的伤害。无趣、寂寞,求助于网络、电视等声像制品,结果不仅没有缓解这种症状反而使其更加严重。刺眼的灯光效果,闪烁的光标,五光十色斑斑驳驳。可是它反衬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却让他们显得更加灰头土脸。要抱怨找不到对象,要做事没有方向。不自觉地过去了一天,明天又接踵而至,一天一天就这么消耗掉。而过去,我们有一杯茶、一本好书,几乎什么都有了。你现在试试看可不可以?大概不行。因为已经丧失了对书的感情,书太多了,让人反感和要扔掉的书太多了。一句话,我们被淹没在声音和文字中,我们无法选择也无力鉴别。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都已经太疲劳。
我有一位朋友,他说苦于找不到好书。我送给了他一本,结果第二天让我看到了一个疲惫而兴奋的他。他说读了一夜的书,说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书!可见真正找到了一本好书,读进去,全部的想像空间被占满和利用了,跟着书中的一切去设想去游走,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他不是一个文学中人,一本小说却能把他如此吸引。他现在正读这本书的第三遍。可见人世间好书还是有的。
二十五年前省图书馆的朋友为我找来一本地质游记方面的书,结果给了我长久的快乐,至今还带在身边。那是文革时出版的书,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在我看来都是美的,好极了;真正的艺术品,无比朴实,连同封面和装订,处处优美。可见任何时候,好书都是有的。
关键是读书要有个心情,有个方法,有个区别。不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评价高于一切,而是指它们需要完全不同的阅读方式,就好比不同的食物需要不同的吃法一样。读文学作品,一般而言关注的重点不是它的情节,而是细节;不是中心思想之类,而是它的意境;不是快速掠过句子,而是咀嚼语言之妙;不是抓住和记住消息,而是长久地享用它的趣味。
一部作品里没有直接说出的话,所谓的话里有话、隐在字里行间的话,还有意味,都要品读出来。文学阅读就是还原作家创造那一刻的感慨、不安和兴奋。文学作品主要不是读故事,不是读情节,而是在细节中留连,展开悟想。人是具有幽默感的,人能够靠想像编织别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实际生活经验的支持,这在文学的阅读中至关重要。这些能力不是受教育得来的,或者说主要不是受教育得来的,而是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能力或者在后来的教育中得到加强,或者被覆盖、歪曲和丧失。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人在进入大学或深造之前,是很能在好作品中感动的,这之后却读不懂了,变得不辨好歹了。
有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朋友对我说出一个困惑,即现在有那么多的小报网站、那么多的信息传递渠道,我们接受的刺激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读小说之类?这等于问文学何为、其存在的理由,当然是一个大问题。我仔细想了,对他说:你通过眼睛和耳朵去捕捉和了解的社会信息,它和文学阅读还完全不是一回事。文学阅读会让你慢下来,以获得文字和语言的快感。比较起一本绝妙的深沉的小说,你所看到听到的那些信息和故事,它们还是直白、简单多了;它们没有独特的想像力,表述上也不够讲究,显得粗糙多了;而且好的文学作品的意境、它的细部,还要靠你自己去想像——这个过程就是再创造。你要靠自己去把死的文字唤醒,并把它们立体化、还原成鲜活的生活。声像网络不太需要那么多的思想,你只是“知道了”而已。文字的阅读,一千个人读,会因为每个人的教养资质不同、每个人的思想方法及性格的不同,产生一千个差异巨大的结果。还有,真正的文学作品是现实中不会重复的东西,它仅仅是一些极为个人化的虚构世界。这才是文学的魅力。文学的语言多么讲究,文学的意境多么高远;它的气氛、它的人物,这一切是多么地奇特。整个文字的帷幕后面总是站立着一个人,这就是作者本身,一切的奇特都来自这个人。
人与人的差别是巨大的,这就是生命的神奇。
文学写作和艺术创造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工作。它甚至不能靠集思广益,不能搞群策群力;它只能靠独特的灵魂、特异的生命,靠生命在某一时刻的冲动和爆发。它的结果是不可替代的、个人的,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第二次的活的风景。一千个人能代表和再造莎士比亚和屈原吗?当然不能。他们是不可以用智慧交换,也不可以用技术再生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愿意买精装的书,最好是全集。我觉得那么伟大的灵魂、那么好的艺术和思想,就应该用最好的包装把它保护起来打扮起来。大套书摆在那儿,不是为了排场为了好看,而是要从头看下来,以了解这个人的灵魂深处,了解一些转折,看他一生对这个世界有多少感情。畅销书作家为什么总是少一些价值?就因为比较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感情,他们不牵挂我们的生活,不牵挂我们数千年的历史,也不牵挂我们的未来。面对全集,由于时间的问题,可以一边翻一边看,粗读细读不一。一部全集,就是一条生命的长河。我们有可能知道这个人是怎么生活的,怎样从少年到青春、到壮年、到晚年——他刚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心灵状态是怎样的,到了青年、壮年时,又有多大的创造力,到了晚年有没有垂死的绝望、思想是否清新,等等。这等于回忆自己的过去,认定自己的现在,想像自己的未来,看看伟大的人物,看他们当年与自己的时代是怎样产生摩擦的。
我看到一幅好画喜欢得不得了,可是我更喜欢看画家的全集。我就不相信一个人全部的创造痕迹放在这儿,你就窥不见他的心,你就不了解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对他们的理解,音容笑貌,有时觉得远远超过对生活中熟人的理解。这就是文学艺术的魅力所在,它说到底是人的魅力。
有一位作家
有一位战争时期的作家,自幼聪颖过人,酷爱文学。他同时要为一个理想奋斗终身,所以参加了队伍,边打仗边写作。这个作家一直让我尊重和崇敬。有很多人的写作都在模仿这位作家,我更是如此。他的作品,我每一个字都读过,这份景仰无以言表。现在好多人一读到那个时期的文学,就要先有几分轻薄。其实不必。那时有一些作家是非常纯粹的,当年就为了救国,为了把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倾其所有,撇家舍命。做人要纯粹、求主义、求真理,都不能掺假,这和对待艺术是一样的。作家一心向着名利,就不是真正的作家。他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写作有一种单纯的力量、强盛的力量,今天看起来仍然打动我们。这种力量是永恒的、无限的。比较那些过分简单地将文学与革命、革命与人性对立的作品,他的写作今天看,仍然葆有其丰富性和宽阔的感性空间。
他是坚定的战士,骨子里又是很唯美的。他追求完美,浪漫气质与生俱来。即便在极左的年代里,他写女性、写爱情,写人性之美,写自然,都那么饱满……随着时代往前发展,到了网络称雄、到了全球一体化,到了我们又兴奋又无奈的当下,他也随之跨入。一切都在风里,人可以把门关上,可是呼吸时却要进入血液。每个时代都有好坏间杂的东西,毒素进入体内,就需要强大的免疫力,让白细胞把它杀死。这位作家头脑非常清醒,他对极左时期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有过极为深刻的批判。可是他也毫无犹豫地痛斥物欲统领一切的时代风气。
同样是老作家,有人对物质主义,对强大的欲望控制下的生存是十分适应的。有人在一些场合总是笑着,不停地说着:“青年多好啊,那是我们的未来啊!我相信未来啊,一片光明啊!”这让人看了听了很舒服。宽容、信任、乐观,没有什么不好。其实呢,说说吉祥话儿,博个口彩,原是不难的。难就难在凡事有个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没有说为什么相信未来、根据是什么;也没有说对青年充满希望的理由,更没有说对哪些青年充满希望。
而我尊敬的这位老作家却不是这样。他远没有那么乐观。面对全球一体化语境下的欲望泛滥,物质主义的全面入侵,他愤慨忧虑,痛心疾首,写了大量文章谴责和呼吁。他对一部分青年、一些现实,失望甚至绝望。他期待有更多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他忧虑到什么程度?那是真正的忧伤绝望。七十多岁的人了,非常痛苦。纯粹的人,其痛苦总是非同常人。多少年了,我想见他又几次却步,总觉得有机会当面表达心中的敬爱。我总是把时间往后推移。
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开得很长。老作家的弟子想约我一起去他那儿,并且定了个时间。可是因为心里没有一点准备,也太匆忙了,结果还是没有去成。回来不久,我却知道了一个胆子比我大的文学青年,他早就拜访过老人了。他说了去见这位老人的经过,满足了我急着要知道老人是怎样一个人、喝什么茶、家里藏书多少、起居细节等等。他说去时带了礼品:一点核桃、绿豆豇豆、一些牛皮纸——老作家喜欢包书皮。看这位青年想得周到,送牛皮纸、核桃等,礼物像老人一样清爽淳朴。我真想和他一起去一次,可他后来都是自己去的。最后,几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突然又得知另一位中年作家也见到了那位老作家!他回来详细说道:作家现在很老了,非常不愿说话;那天老作家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从济南来;老人就说到了我——中年作家说那是俺邻居;老人沉思了一会儿,说:“你多跟他交谈啊,要站住脚跟……”老人只重复了这么几句。中年作家很轻松地说出了这番话,并不知道对我意味了什么。他不知道我正听到了从小崇敬的人——关于我的谈话!
一个人一旦被一种文字、一种情怀和美所击中,大概一生都不会忘记。物质利益会忘记,被精神的射线所击中,则不会忘记。这天晚上,我自己出门,一个人登到了南郊山顶,又到白杨林里,走得很慢很久。我需要平静自己。就是这个白天,我得到了最大的消息,最大的肯定和最重要的人生叮嘱。这种激励,足够了。
大约在他去世前四五年,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去找老人谈出版作品集的事。我这个朋友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对老人喜欢敬仰极了。他准备把老人的书出得漂漂亮亮,让封面、印刷装帧及一切方面完美无缺。他每出了书都要反复抚摸,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去了,三四天以后回来,情绪极坏。他说:以前我见老人总是谈得很好,想不到,我们这次几乎没有说话。老人失望了——不,是绝望了。他这些年里先是不愿参加社会活动,再是不愿出门;现在连屋门都很少出,长时间躺在床上。不愿吃饭,不愿说话。头发胡子很长,瘦得要命。他说,他当时给老人鞠躬,然后说了出版的事,儿子还大声重复客人的话,老人却只是翻翻眼睛,啊啊两声,把脸转到墙的一边去。儿子很抱歉,小声对客人说:父亲头脑很清晰,但是……只喝一点儿稀粥,人不会长久了。
不久,老人去世了。
我多么痛惜。我对那份坚毅能够理解。我们是两代人,对待生活细节的评价和处理方法可能有许多差异,但他憎恨时代的丑恶及永不妥协的精神,永远让我钦敬。对比那些总是“相信未来、一片光明”的哈哈大笑者,我更信服这位老人。他能让我想起鲁迅。
我们可能不太同意他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但是我们会对他的这种选择、他的立场、更有他的牺牲,肃然起敬。我不能想像他头发很长、胡子很长、一点一点煎熬自己,那时的心境。但我知道他是我们时代里最沉重的一颗心。在心灵的天平上,还没有另一种重量可以把它平衡。我会记住他说给我的话。
两难的时代
未来是怎样,青年是怎样?我不敢不负责任地随便放言。我口说我心,我必须问问自己,你是怎么看待未来的?我承认自己很难回答。我只能如实地说,我对未来充满了忧虑。但是为了未来,我不会放弃任何积极的努力;我又是怎样对待青年?我不能说自己不相信青年,但我对青年同样充满了遗憾和疑惑——尽管如此,我对这个时代青年当中的杰出人物还是感到了由衷的宽慰,甚至为和他们同处一个时代而感到高兴。
我不是一个简单的乐观主义者,既积极也消极。我正尽一切努力,以自己的积极战胜自己的消极。这可不那么容易。
现在网络纵横、西风劲吹,整个的欲望都解放出来呼唤出来了,剩下的问题怎么办,那就全看我们自己了。泥沙俱下,目不暇接,阅读品不是要什么有什么,而是常常让我们瞠目结舌。一些网站、图书、影视,更有其他媒体的渲染,所见所闻充满感官刺激极尽撩拨。还有大学,本来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她通常代表青春和知识,是一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可是有一次我因为要查资料打开了一个大学的网站,竟吓了一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学生们在那里互发帖子,那是怎样的语言怎样的观点,怎样的素质,你会不明白他怎么考上大学,更不明白有的还是研究生博士生。这不是寥寥几个帖子,而是相当大的面积。其中少数正常和正气一点的,有些许义愤的,必定遭到围攻和嘲弄。既然如此,当我们谈论青年和未来的时候,还敢于轻易放言吗?
生产总值大幅攀升,社会生产力空前解放。言论环境也变了,仅就文学创作而言,已进入从未有过的多产期。我们有大量的作品,各种各样的作家。无论偏激也好、不偏激也好,现在到了真正考验人的精神和创造的时候了。对于一个巨大的事物,人的反击和抵抗也需要拿出同样大的力量,这种对决必要留下自己的痕迹。能这样坚持的人,他想平庸都办不到。一个僵化和板结的时代有什么意思?那只能让创造的精神沉沦下去。时下,好的作家,杰出的作家,也许正在产生或已经产生;但更有在欲海中沉浮招摇的作家,更愿虚名盈世,被金钱欲望牵得越来越远。其实,每个时代的杰出艺术家本不会多,看待一个艺术家十年二十年还远远不够呢。一百年产生几位就不错了,剩下的就是互相不可取代的、有特色有意义也有价值的作家艺术家了。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经验,所以其表达是不可取代的。观察艺术和文学,如果不能视野开放,仅拘泥于当下,肯定会觉得满目疮痍,会有极大的不满意。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不自觉中正使用了更大的人和艺术来作为参照。
现在,只有现在,这种泥沙俱下、混乱不堪的创作格局中,一个作家能够坚持自己,同时又具有不凡的才能,那么留给一百年的机会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忧虑,一方面又不无乐观。我们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之中。我们对经济的飞跃、物质生活的大幅度提高,有一点儿庆幸;同时又对人的贪婪、强横、无理和野蛮,对环境的难以修复,感到椎心之痛。我们常常要在两难之中生活、思考和创作,有时不免陷入悖论。在野蛮者眼里,什么文学、艺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最珍贵的思想,什么永恒和伟大,只用一个脏字就可以打发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我们的生活还会有什么希望?可是没有希望,放弃积极,很可能沦落到更不堪的、极度恶劣的情绪之中,这当然是不行的。于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更多的坚持和奋争。
无论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事情不是两难的,所谓的福祸相依。如果发现不了核能,原子弹不会有,人类就此毁灭的危险也没有;可是巨大的核能源也不能利用。超级大国有了核武器,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如何坐视。经济不发展,无法强国,无法自安。历史有过再好不过的说明。保护环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我们已经把人的欲望、物质主义的欲望调动起来,释放出来,再与环境相谐相安已经难上加难了。事实上,这种道理不是我们今天才发现的,这种两难也不是我们第一次提出的。伟大的哲学家罗素,那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到中国来考察了一番,而后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儒家思想太好了,它倡导的生活方式,对物质和思想层面的把握非常好,是一种优雅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指导下的民族会是非常安逸和文明的;他说只可惜,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文化,即西方骑马民族的文化,那是物质主义的、掠夺的文化,你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无法与其共存。可见大哲学家罗素早就想明白了,我们人类实在处于一种两难之中,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今天的拚搏,说白了只是一种追求生存的斗争。问题是我们要明白,人在这种两难中仍要有所作为,要拿出更多的智慧和勇气才行。我们还不能随波逐流。无论做什么,还是应该有一点理想。要关怀这个社会,不能丧失最后的一点公益心和正义感,这不是空洞的大言,而是最基本的东西,更是生存所需。
开讲之前,许多人希望讲一讲刚出版的长篇《刺猬歌》,我还是没有讲。为什么?因为一个作家要写三十多万言才能尽兴的东西,他自己在这里用一席话去概括,会是相当危险的。既然需要那么多的语言才能表达的,简化和说明只会造成歪曲。你们听了我今天的演讲,也大致会明白我的新书会写些什么。至于它是怎么写的,有怎样的语言和细节,是否会给人以语言的享受,那还要自己去判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