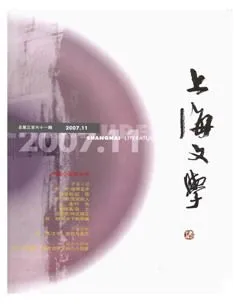文学:虚构与真实
2007-12-29南帆
上海文学 2007年11期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需要文学?为什么需要一批作家来对生活“说三道四”?这至少说明,生活中的一些过程和内容可能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我们知道了一切,文学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作家和艺术家——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能够与世界进行一些独特的对话。他们说出了特别的感想。每个人其实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世界对话,而作家与世界的对话享有一个特权,这就是虚构。通常我们都把虚构称之为谎言,但是作家的虚构享受道德豁免权。作家是可以说谎的,作家可以运用这个权利说出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更为重要的东西。所以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历史学家通常是要真实地去记录,历史学家说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作家的虚构说的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这个必然,或许不一定会真的发生,但是按照这个世界的理想状态,按照一种必然性而言,应该是要发生的。这就涉及到了文学的真实与虚构的问题。
作家的虚构通常是有一种真实感的。我们常常喜欢将“真善美”相提并论。什么叫“真”?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问题,也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问题。现代意义上来说,哲学似乎是一个研究大问题的学科。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全民学哲学的热潮,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民族智商特别高,而是因为当时我们对哲学有一种特别的理解。我们愿意认为哲学是带头学科,有人告诉我要学好文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首先一定要学好哲学。现代哲学内部的各个方向划分得非常细致。古希腊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将哲学理解为一门智慧的学问。有趣的是,通常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不会随便自称为带头人。比如说,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话往往非常的低调,但很有智慧。就文学而言,我认为还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是,这个世界有一些形而上学的大问题,我们认为还是交给哲学去处理,比如说什么叫“人”?又比如说什么叫“真”?文学要处理的是这个问题里的一个小问题——真实感,这是文学有别于哲学的一个方面。文学中的很多景象我们会感到真实,我们用我们的感官经验给予证实。文学描写一个血淋淋的场面、描写一个街道、描写一个人物的肖像、描写两个人物的对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耳朵、用我们的眼睛察觉到这是真的。可能还有另外一些真实感,它有更内在的逻辑,比如说神话,比如说一些非常浪漫的故事,比如说孙悟空、猪八戒,我们从未见过,但是我们仍然产生了真实感。这些内容某种程度地与我们的日常经验发生了契合。因此,即使是神话、即使是夸张、即使是象征,我们仍然能够理解,仍然有一种真实感。文学虚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包含了真实感。对于文学家而言,虚构是一个巨大的权力,他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自己的世界。有时我们还会用虚构解决另一些问题。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因为失恋曾经企图自杀。这部作品的出现表明,歌德的文学虚构不仅使这个世界多了一部名著,同时歌德也通过这个虚构解决了自己的心理问题。所以虚构的想像不仅处理自己与世界的问题,同时也处理自我与内心的问题。
但是,对于文学而言,虚构还必须诉诸于第二个环节,就是叙述语言,想像不能够悬空地停留在脑子里面,而是必须通过语言叙事凝聚起来。叙事,就是把事情述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什么叫事实?一个事件的开端、结尾和事件发展的进程,很多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刚才我在巨鹿路上看到一起车祸,这个事实在不同人眼中是不一样的,一个农民和一个记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从更大范围来看,比如说一场战争,不同历史学家的理解也不会一样。他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什么地方开始,在什么地方结束,他们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们存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差别,这肯定影响到人们对于事件的观察和理解。作家进行他的叙述时,会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但是,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和作家的理解非常一致的。比如,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电影还没有结束我们都不约而同站起来往外走。这说明我们基本上对电影中的事件应该结束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共识。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福斯特。他曾经很俏皮地说,多数小说结束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婚礼上的鞭炮声中,一个是把棺材钉上的时候。恋爱而至结婚,或者,一个人死去了,这通常是结束事件的基本方式。但是,某些独具慧眼的作家可能对于事件会有独到的看法——有时他会观察到事件还没完,或者他会观察到事件更早就已结束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同时也体现在叙事之中。所以虚构可以体现为想像,也可以体现为叙事,而这个叙事常常包含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虚构、想像、叙事都有了一定的成规。每一个文学家的虚构都不再是从零开始的,他前面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现成经验。总结这些成规,文学史上、文学理论上也已提出很多的概念,也有很多的角度,比如说诗歌、小说、散文等就是几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和想像方式。同时也存在其他的概括方式,比如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今天我主要想谈一谈这一些概念背后的真实以及它是怎样进行虚构的。
所谓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觉得这是文学上的一种理论总结。对文学的理论总结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总结不应该制造框框,而应该成为创新的起点。文学总结经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总结出来的经验在初级的层次上都是教导后人应该如何遵从,但是在高级的意义上,很可能是树立了一个必须绕开的目标。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特别注重创新。如果和体育相比,文学应该是更鼓励创新的。创新经常有很大的风险。体育竞赛的重要目标是拿冠军,因而体育选手不一定敢冒这个风险。文学中没有“第一”、或者“冠军”这个概念,不存在你打败我或者我打败你。“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不存在争“第一”的负担,因而反而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无拘无束地把自己心智之中最灿烂的一面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所以我认为不能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样一些理论总结,变成文学发展的框框。当然,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说,有必要梳理这些理论概念的来龙去脉,它们背后有很多历史上的、哲学史上的、经济史上的原因。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些概念背后也包含着文学的感觉,这与我们的虚构、与我们如何理解真实、怎么处理我们眼前所见的世界、怎么进行文学的处理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我想先谈一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艺术家、作家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模式。但是,这个概念也被搞成了理论史上最为乏味的概念之一。其实这个概念并非特别难理解。进入历史的环境之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是在浪漫主义之后出现,在文学史上主要是反对浪漫主义的传奇、夸张、强调象征性、强调抒情性等等。高尔基曾经有过一个很朴实的定义:现实主义就是对现实不加粉饰的理解。其实,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下去就会发现,现实主义就是保持了强大的真实感,但它是建立在我们对常识信任之上的真实感。常识是很简单的知识,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常识是一致的。现实主义还强调典型人物。这种理论主张,典型人物的性格必须代表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一个具体的人物,都有自己的脾气和爱好,自己的相貌,他凭什么代表这个时代呢?他凭什么代表千千万万其他人呢?因为这个人物身上汇聚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理论方式后面存在一种假设: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种细节之间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这个时代哪一天不再是一个有机整体,那就找不到一个中心,典型就丧失了基础。之所以我在这里提到这一点,因为这与后现代主义有密切的关系。现实主义的另一种意义是表现了底层人民和被压迫阶级的疾苦,例如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是就现实主义的字面涵义而言,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什么是现实?其实我们所知道的现实都是每个人感受到的现实,不可能存在一个抽象的、权威的、一致的现实。我们最多只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现实,所以每个人只能看到现实的一个方面,这就造成一个问题——谁感受到的现实更重要?感受现实的人的内心意识叫不叫现实?意识流小说的出现,就在于说明一批作家认为内心的意识是现实中很重要一部分,甚至认为真正的现实在于我们内心。这是意识流小说对于世界的理解。如果我们接触过一些西方作家的资料就可以看到,有人认为现实主义就是没有想像力,就是爬行主义,就只是贴在事物表面上的描写而已,而且认为仅仅遵循现实主义的人不配做作家。这也许是对现实主义的另一种理解。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现实主义就是真实感,这就是真实感的来源。当然,现在这种理解出现了一些模糊地带。比如说前些年有一部电影叫做《黑客帝国》,里面的场景让我们都觉得一切都发生于现实之中,但是实际上许多场景都是虚拟的。这个还是不是现实主义呢?早先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概念的时候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今后还将遇到的一个问题。我看这部影片的感觉是,每个场面都让我感觉非常真实,但是整体上又是非常的不真实。这是我们以后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现实主义之后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大的文学潮流就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指19世纪后期开始的各种文化运动,包括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等。这些在20世纪初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进入了中国,对很多中国作家产生了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的现代主义基本消失了,一直到80年代之后又重新出现。当初王蒙写了一批意识流或者说准意识流小说,后来又有马原、苏童、余华、格非等等一些作家进行过各种实验小说的尝试。我们习惯于把这一些作家称之为先锋作家。现代主义和现代生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两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们曾经把二者等同起来了。有的理论家发出一个号召:既然我们的生活要走向现代化,那么我们就要写现代派作品。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什么叫做现代生活?“现代”该怎么界定?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任意挑出日常语言的一个词进行定义,我们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什么叫做文化?这个词在世界上有一百多种定义,以后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千种定义。我们日常中所用的词很多都有这样的问题。通常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有效的策略:那就是看看这个词相对于什么而言。例如,现代就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全世界很多思想家围绕“现代性”进行争论。有人认为现代性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有人认为拥有核弹头的就是现代社会,还有的人认为家家户户都用上抽水马桶就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至少人们认为,现代性将带来一个理性的、物质丰富的、而且民主的社会。奇怪的是,我们绝大部分的现代主义作品,色调都非常阴暗,情绪抑郁,没有人感到乐观快乐,很多现代主义作家都对这个世界惶惶不安,总觉得不对头。乔伊斯是这样,卡夫卡是这样,爱略特也是这样。萨特也揭示了人与人之间阴暗的一面——“他人即是地狱”。为什么这些作家总是感受到反面的东西呢?这是现代主义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谜团。理论家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一种理论认为,在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个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个人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意义有助于开拓世界,开拓市场,当时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单位,个人造就了资本主义早期生气勃勃的局面。但是不久以后,个人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批人为代表,另一方面以从事艺术活动的另一批人为代表。前者在经济活动中仍然非常具有开拓性,但是他们在生活趣味和美学趣味上越来越保守。后者抵抗这些趣味,表示讨厌和蔑视,他们从年轻时开始就进行反叛,这形成了西方在80年代所谓的“迷惘的一代”、“颓废的一代”、“嬉皮士”,他们的中心意图或者说强烈愿望就是亵渎和践踏中产阶级趣味,让他们的父母难堪。现代主义有一大部分的精神资源就是来自于此。他们的反抗不是进行阶级斗争和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体制,然后夺取政权,他们强调的是用个人的内心,用神秘的感觉抵制西方物质社会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所以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其实是一种矛盾120d25ca057951e33a55e2fa9c83277e的关系。
现代主义另一个引起我们关注的特征是它对于技术与形式的探索,这与前面我所说的叙事是有关系的。现代人文学科之中,语言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结构主义、分析哲学以来对于语言的研究使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包括主体、自我的形成。理论家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自我的建立是在各种符号的交叉之中确立的,并不是我们在使用符号,而是符号训练我们,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这说明了语言在人的精神活动重要作用。语言限制了我们精神的发展,语言决定了我们的精神姿态。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语言之中,语言是不可旁听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语言之外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人不屈不挠地要找到我们精神上更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语言实验。这一批人多半是作家诗人。诗人在词语上颠来倒去地反复摆弄,有人认为是在搞语言游戏,我认为他们是想通过语言的实验寻找到人类精神上新的可能性。现代主义很多作家热衷于艺术实验的背后,也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觉得现有的世界令人失望,他们在尝试能否写出一种新的特殊感觉。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现在大家都在用“后”,什么后工业时代、后革命时代等等。后现代的“后”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指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但更重要的还不是时间上的界定——另一方面就是指不同的文化类型。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来临之后,现代主义就会消失了,事实上是两种文化类型共存。西方文化里面,现代主义仍然存在,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只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很多。经过了一大批非常理论家的研究和讨论之后,某些方面我们已经得出了基本的结论。我们总爱说雅俗共赏,有俗文学和雅文学,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使二者的界限正在越来越模糊。以前大学课堂里面是决不教这些非经典作品的,像麦当娜的歌、金庸的小说是进不了大学课堂的。后现代主义之后,人们对大众文化有了比较新的开通的看法。另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利奥塔——提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整体性。由于人类整个知识体系的变化,整体已经崩溃,我们不要继续保持整体性的幻觉,他号召“向整体性开战”,世界上每个局部都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统帅这个局部。现在历史大叙事已经消失了。所谓的历史大叙事就是指我们在谈论、写作、理解历史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这些前提是不需要论证的。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突然失效、崩溃了。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这看起来非常简单,其实这句话对西方社会的震动非常大。这意味了终极标准的消失,人们什么事情都能做了,包括杀人、放火……没有什么可以遭受谴责。另一位著名的理论家杰姆逊更多地强调后现代社会的深度消失。“深度”已经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式,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总是不相信我们眼睛看到的事实,总觉得在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本质。这个深刻的本质也许是上帝,也许是真理。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深度消失了,我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表象后面不再存在什么深刻的本质。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很多问题还在争论之中,远没有结束。
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我个人认为一般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是西方的东西,不见得完全适合中国。当今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以上几种主义交织在一起,这个意义上中国比西方的问题还要复杂。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地域广阔,情况很复杂,不是用几个主义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中国东部沿海一些城市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西部的一些地区仍然处于前现代。一次会议上一个作家认为,中国的状况有些不伦不类。我的观点是,不伦不类的地方更易于出好的文学。太安静的地方文学很容易睡着了。中国像个热气腾腾的大工地。中国正在从农业大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有一些后现代的因素在出现。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已经进入了大众文化的社会,满街的报纸、杂志,下班后回家看电视,这时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什么叫真实。我们再度回到这个问题上。很多时候,符号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我们不知道真正的世界在哪里。我们都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知道的很多东西并未见到。我们的信息量很大,但我们就是在信息之流中接触和了解这个世界。我一直对于一件事深感兴趣——数码成像。我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以前拍电影使用各种特技。不管怎样夸张,特技总还是需要一定的原型。今天一切都可以交给计算机来处理,不需要任何原型。《侏罗纪公园》或者《泰坦尼克号》中的许多镜头完全是用计算机制作出来。这就是说,真实的世界可以完全被甩下。那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科学和神话正在发生伟大的结合。以前我们认为科学反对神话,科学求真。现在的科学正在发展出无比巨大的造假能力,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都说明人类长久以来确立的生存坐标正在瓦解。撇开理论家谈论的这些深奥的理论,我觉得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些无法确定、既真实又恍惚的感觉。这不一定都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之中。比如,虚拟经济就常常让我产生后现代的感觉。我们不能对后现代作简单化的理解。我曾经到过一些非常落后的乡村,有的人家里非常的破烂不堪,但是他们的破桌子上有一台电视,彩色的电视屏幕里正在上演带有异国风情的海边别墅的生活。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拼贴能培养出什么呢?自卑?确立心中的奋斗目标?仇视的情绪?追求公平的理念?不知道,总之不是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经常谈论的另一点就是“消费历史”。历史已经不是我们怀念、感知久远的祖先的那种历史,历史已经成为我们消费的对象。我们把历史拿来逗乐,闹着玩,就像在喝一杯咖啡似地把历史喝下去。中国文化是很重视历史的,“以历史的名义发言”证明历史是严肃而神圣的。今天电视里上演特别多的是古装戏。有的人认为作家写不了现实,就逃避现实去写历史。我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解释。今天的人文学科里面,历史还是一门最严谨的学科。但是在历史影视剧里面,它变得最没有规矩。服装、礼仪、人物年代以及各种情节都错得一塌糊涂,历史成为最容易虚构的对象。历史完全被肤浅化了。张艺谋的《英雄》用武侠的模式所套秦始皇时代的历史,非常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内涵变成了几个武侠互相打来打去,最后还装模作样地悟出所谓的“无剑就可以得天下”。对照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话,这种后现代的确只是一个逗人开心的小玩具了。我在阅读之中常常有这样的感觉,文学对社会对人的理解日益简单。经典作家常常会出现很复杂的情感判断。鲁迅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真是说到家了。仅仅是“怒其不争”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大作家的鲁迅还有强大的怜悯之心。《唐·吉珂德》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主观主义的人物,但是他还有伟大的一面,为了自己的信念“知其不可而为之”,很多时候迂腐和伟大也就是一步之遥。文学不一定能清楚地判断历史,但是文学力图揭示历史、社会和人性的复杂。《红楼梦》可以有各种解读,但一个基本的情节就是贾宝玉和一大堆女孩子的故事。贾宝玉在自己的选择之中显示出生活的难处。这至少是男女关系之中的难处。但是也可以有轻松简单的写法,比如金庸的《鹿鼎记》。不论来多少女人+5L3Ve6H1jMntkZCS7m5Jw==,韦小宝都照单全收,生活中不存在这方面的难题。《红楼梦》之所以比《鹿鼎记》深沉——让我用这么一个过时的词语,就在于它揭示出生活内部的难点。贾宝玉可以反抗,但是他反抗谁呢?所有的人都这么溺爱他,生活却又是这么不如意。他没有办法找出他的敌人,他进入了“无物之阵”。这是一种奇特的生活状态。很多侦探小说非常好看,情节上起伏跌宕,但是所表现的生活相当简单化,内在的理念非常简单。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对每一天的变化感受深刻。杰出的作家正是利用手里的虚构特权发现我们一般人在生活中不能发现的事情。如果做到这一点,他就没有辜负这个特权。
(本文系作者2007年4月27日在上海作协“城市文学讲坛”的演讲,整理金洁明,已经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