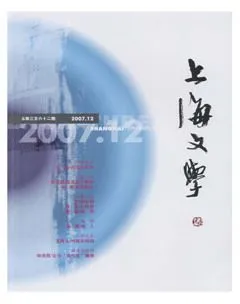文学“现代化”猜想
2007-12-29李海霞
上海文学 2007年12期
在中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界,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并不是最有力、最前卫的观点。相比于高行健的小册子和它引发的几只“小风筝”,徐迟的一心想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派”的努力只能算作一场徐迟式的“歌德巴赫猜想”,但是考察这个猜想依然是有意义的。徐迟是一位有着五十多年创作经历的横跨现代与当代两个时代的作家;他又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派”的鼓吹者、参与者;建国后他又以报告文学家的身份为人们熟悉。① 徐迟的文学生涯丰富而驳杂,其思想和言说方式都有值得我们深入思索的东西。
1980年4月,《外国文学研究》发起了“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参与讨论的多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讨论的文章也多以介绍、述评的方式出现,可以说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学院式文学活动。一年多以后,徐迟在该刊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很快,《文艺报》在1982年11期上予以全文转发,并同时发表理由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火药味渐浓;1983年2期,《文艺报》发表李准《现代化与现代派有必然联系吗?》再次向徐迟发难,文章明确批判了徐迟的论点,并重申了现代派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至此,外国文学领域引发的这场“现代派”的启蒙运动宣告失败。但是,在新时期以来不多的几次文艺争论中,比如之前的“苦恋”风波、有关“朦胧诗”的争论、戴厚英的《人啊,人》的争论等,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把文学问题的核心紧紧地缠绕在了国家生活的重中之重“四个现代化”上,这令整个关于“现代派”的讨论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态势。
《现代化与现代派》这样开头:“这样的文章,虽然时机未很成熟,却还是要写一写的。”这里所谓“未很成熟”的时机,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面开始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二是指“坊间也并没有多少现代派的文艺作品”。② 这个观点,令人想到30年代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中茅盾的意见:“必先有了多了某一派的文学作品,然后该派的文学批评才建设得起来……批评材料的缺乏,虽天才的批评家恐亦难以见好。”③ 鼓吹“文艺现代化”或者为“现代化的现代派”鸣锣开道,未见得就是在鼓励一种新的文学流派,但既然中国文学向来有理论先行的传统,那“写一写”这类不合时宜的文章却是“宜早不宜晚”的。事实上,徐迟本人早有将“现代化”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冲动。1978年中国文联理事会扩大会议上,徐迟提出了把“文艺和现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他用“文革”式的语言颇为武断地说:“文艺的现代化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我们的新诗当务这个当务之急;古体诗词一样应当务这个当务之急。短、中、长篇小说要务这个当务之急。革命回忆录更是服务于这个当务之急的。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要务这个当务之急。儿童文学尤其要务这个当务之急。话剧、歌剧、京剧和地方剧种都要务这个当务之急。歌曲、音乐要务这个当务之急。绘画、雕塑、工艺美术要当务这个当务之急。电影本身就是高度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艺术形式,特别能够务这个当务之急。舞蹈就是舞这个当务之急。曲艺、民间文学要高歌这个当务之急。摄影就摄这个当务之急。我们的刊物和正式复刊的《文艺报》当然是要务这个当务之急的。……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现代化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当务之急!”次年2月,在诗歌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说,文艺要务四个现代化的当务之急,“那时(按——指去年)这样说,也许稍稍早了一些;今年说,正是时候;再不说,肯定是不对的了。”所有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结合徐迟的文学活动,我们能够理解他对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有可能实现的“美好前景”所怀有的热情。徐迟在“新时期”以写科技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扬名,但其实他从建国伊始就开始关注、报道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50年代,我忽然发了一个怪论:从今以后,我要读的是生活这一部大书了。便开始在全国旅行……真是左得可爱!”④据徐迟的主要传记作家徐鲁介绍,徐迟是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开始他的巡游全国的文学实践的:“先后到过鞍山、长春、沈阳、包头、武汉、重庆、昆明、兰州等新中国主要钢铁基地、重工业城市和新兴的工业基地,并西出阳关,纵贯柴达木盆地,深入大西北刚刚开发的油田、矿山采访调查……”⑤ 这一时期他写了散文特写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和《庆功宴》。综观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徐迟所热衷讴歌的是机械大工业的作业场景,比如描写我国第一座自动化高炉的《在高炉上》;写内蒙古草原地质工作的《草原上的钻机》;写桥梁建筑的《汗水桥头》和《长江桥头》,以及1958年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桥飞架南北》,和后来描写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刑天舞干戚》;写柴达木盆地油田开采工作的《第一棵采油树》;写测量工程的《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些“工业题材”的作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突出科技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宏伟功业;二,突出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工程师级别的高级科技人才)的高超技术;三,突出党民一心的团结建设场面,尤其突出党的领导的正确和重要。这些作品,为我们描绘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激情场面,也表达了作家对新中国最热情的讴歌。
虽然“新时期”以来,徐迟多次表示50年代的这些创作是“粗糙的”:“我离开了温柔的音韵的镣铐和美妙的格律的束缚,而投入了宽大的散文的怀抱,写了一些激动的和愤怒的,主要是论战性的粗糙的东西。”⑥就文学性而言,徐迟的自我批判里确实包含着真实的痛苦,尤其当我们今天在《瓦尔登湖》这样的译文里惊叹作家的文情并茂之时,我们亦不能不为他的那些创作中文笔的粗糙生硬而惊诧莫名。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那个说:“我曾睡在一个建设工地上,我以为我睡在共和国的跳动的心房上”的作家,并非简单地将手中的笔做政策的传声筒,他的创作是真诚的,这份真诚源自于他对现代化的“赤子之情”。1982年至1984年,李欧梵曾两度分别在中国和美国对徐迟做过访谈,他回忆说:“当徐作为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营客来美时,我把他带到芝加哥旅游。在来自中国的作家中,他是唯一为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欢呼的人,而其他的作家都更喜欢爱荷华的田园风光,而且有不少人还认为芝加哥的建筑很丑陋!”⑦ 作为一个“现代派”诗人,徐迟将满腔的浪漫激情献给了机器大工业,这在中国作家中是不多见的。⑧ 即使是他曾经交往甚密的那些现代派大师们,包括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和在上海最出风头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刘呐鸥,他们都没有真正地在现代化大工业这个层面对现代生活认真思考、深入体会过。当他的同伴们还在跳跃着上海的狐步舞之际,徐迟就已经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了:“将来的另一形态的诗,是不是一些伟大的史诗,或者,像机械与工程师,蒸汽、铁、煤、螺旋钉,利用飞轮的惰性的机件,正是今日的国家所急需的要物的,那些唯物的很的诗呢?” ⑨
强调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徐迟并非始作俑者,而这篇《现代化与现代派》亦非他天真的想像之作。1947年,朱自清就曾提出过“新诗现代化”的观点。他说:
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我们迫切地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地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现代史诗”一时也许不容易成熟,但是该有一些人努力向这方面做栽培的工作。⑩
袁可嘉也是“新诗现代化”观点的重要代表,只不过他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阐述这一观点。袁可嘉接受了瑞典理论家瑞恰兹的“包容诗”的概念,在诗歌艺术上追求一种“高度综合的性质”。袁可嘉认为194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最缺少的品质就是这种现代诗的“包含性”,而新诗现代化的新传统就在于新的综合的包含的传统。这种综合的传统暗含着一种评判诗歌的标准。袁可嘉认为一首诗优劣要依据它的容量(包含性)鉴别出来,“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袁可嘉从批评的包容意识出发,主张现代新诗应以平等的态度接纳政治,但总体来说,他的这一理论是为了现代主义文学在建国之后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
建国以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度成为中国作家最强烈的浪漫想像。这令包括徐迟在内的大批作家纷纷与之前颓废的现代主义个人情感告别,“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何其芳);他们热情拥抱并讴歌了即将展开的现代化建设,新中国的诗风、文风亦为之一变。茅盾曾在1958年作过这样的描述:
今天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就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壮丽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我们做着我们的先人从来没有做过、甚至没有梦想过的大事,我们破除迷信,大胆创造,使我们国家的工农生产、文化活动,一天天地除旧布新,创造了奇迹,我们祖先的美妙的幻想,在今天我们国家里,都变成了现实。
正是在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理想”的召唤下,甚至在经历了“文革”十年之久的劫难之后,中国人仍然对“现代化”的“美妙幻想”矢志不渝。
“新时期”以来,最先宣扬文学现代化的是周扬。他在一次讲话中说:
为什么要研究外国文学?……产生了世界文学,使文学摆脱了地方性、狭隘性。……四个现代化,向外国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是这样,在社会科学、文学方面,有所不同,但也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11}
高行健和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其对形式和技巧的宣扬背后,推动和促进文艺“现代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潜台词。从叶君健为它做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纯文学”家们对“现代派”的推崇和徐迟的出发点是极为相似的:
蒸汽机发明后,人类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起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的欧洲文学,无论从表现形式或思想内容方面就与18世纪的文学不同。……这些变化基本上都是蒸汽机时代的产物,现在都已经成为了我们新文学的主要形式。……但我们人类的历史现在已经又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电子和原子时代。机械手已经取代了“流血流汗”的体力劳动,自动化成为了我们时代生产方式的特征,脑力劳动已经在许多先进国家也成为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重要因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跟着起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表现这种认识的方式也与蒸汽机时代不同,在文学艺术上从而也就有许多不同的流派、表现形式和风格出现。这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必大惊小怪。{12}
新的历史时代需要新的审美方式和文学艺术,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叶君健的看法和徐迟形成了有力的互动,“新时期”以来,徐迟本人除了对科技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倾尽心力之外,在文艺现代化问题上更是不遗余力。如前所述,徐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过自己的文艺现代化观点,这也令我们得以观察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发展变化。最初,他认为: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文艺……必然是、只能是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文艺。
新诗(按——指现代化新诗)当然要歌颂我们党、国家、军队、人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新诗人要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义不容辞地奋不顾身地起来发挥新诗的战斗武器的作用……{13}
至此,徐迟的言论都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对文学反映现代化的要求延续了近代以来以“国富民强”为主旨的现代国家叙事的线索,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与这一线索是紧密相连的,而非断裂的。活跃于80年代之初的“改革文学”是体现这一国家现代化想像的最集中代表,国家对现代化的强烈要求“逼迫”作家及时、迅速地反映和应和这一时代命题。蒋子龙在谈到《乔厂长上任记》时就说:“《乔厂长上任记》是被‘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这一类文学很好地将“改革者”的形象放在峻急而宏大的“现代化”图景之前,塑造了像乔厂长、李向南这样奋发蹈砺的国家英雄形象,一时间影响巨大。但是,文学与国家政治的“蜜月期”维持不久,裂痕出现了。1979年,《上海文学》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评论,要求文学叙事脱离国家政治的统辖,“名正言顺”地发表文艺自己的声音。文章说: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对阴谋文艺进行了猛烈的鞭挞,揭露了阴谋文艺在政治上的反动性、内容上的虚假和艺术上的拙劣,但是对炮制阴谋文艺的这个理论基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却从未进行过批判;不仅没有批判,甚至连怀疑都没有提出过。不少同志似乎认为:文艺过去是“四人帮”向党和人民进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而现在它应该是我们对“四人帮”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结果,群众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一部分作品的反映是:政治上是反对“四人帮”的,艺术上是模仿“四人帮”的。{14}
可以说,政治上反对“四人帮”,艺术上模仿“四人帮”抓住了“新时期”文学的要害,也将人们对文艺的不满提到了反对“四人帮”的应有之义的高度,最主要的,它将为文艺正名的焦点放在了文艺本体的角度,希望文艺能够朝文艺自身的方向发展。这篇评论堪称“新时期”关于“纯文学”的第一篇宣言。随即,《上海文学》受到批判,编辑部又以讨论的形式刊发了大量的反对文章;包括上文对《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现代派”的批判,对单纯提倡文学创作方法的批判等,所有这些,令文学想要获得独立的话语权力这一要求在80年代伊始就蒙上一层阴影。
文学“去工具化”、“去政治化”的努力失败了,文学的“下一步踏向何处”(冯骥才)的问题却依然存在。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包括重新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量优秀作品)在形式上灵活多样的事实令刚刚从“八个样板戏”里解放出来的中国文坛耳目一新,他们受到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如何在依然严密的意识形态体系下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到合法性依据,这个问题随着更多的“现代派”作品的涌入,随着更多的有着“现代派”气息的创作开始萌芽,在80年代初已经到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境地了。如果说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那么将现代派与现代化联系起来,必然将为文学的自由发展赢得最大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刚刚经历了一场现代化“幻灭”的徐迟,在“现代化”、“现代派”、“政治”、“经济”、“文学”与“科学”之间搭起了高超的脚手架,其初衷,自然是为未来文艺的发展寻找到最大的“政治”,赢得最大的空间。
如前所述,《现代化与现代派》之所以最终将论点放在现代化上,首先与徐迟本人的那种现代化情结分不开;其次,徐迟也想通过强调现代化和经济建设将文学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框架内解放出来。他说:“我们这里的评论界,以及学术界是不怎么喜欢谈经济关系的。置政治于经济之上,我们探索问题往往从政治着眼,而无视于经济的因素,甚至经济学论文也是谈论政治大大地超过了经济探讨的。现在,谈现代化建设的文章也是一样,大谈其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意义,很少谈甚至完全不谈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内容。”那么,对文艺而言,谈政治和谈经济又有什么不同呢?徐迟在这里用了经典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非常巧妙地回答说:西方现代派文艺,是西方现代物质生活的反映。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是非常发达的,“特别是60年代以来,其生产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急剧地上升,到了一种令人咋舌的高度”,而他们的精神文明,也就是文学艺术,虽然总的来说,跟不上物质文明,“但很明显它还是并没有拉住了物质文明的后腿”。甚至,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相信,西方现代派文艺也将创作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信心百倍的理想主义的作品”。这段最为人诟病的话明确提出了西方现代派文艺与现代化之间水涨船高的关系,对它们的发展前景给予了乐观和肯定的估计。这与人们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认识显然有了根本的区别,尤其难得的是,徐迟还明确区分了近代派和现代派,他说:“另些人还不能区别那严重污染环境的近代化与高度发展的思维空间的现代化的差别,他们其实还是近代派。”徐迟在此虽未明言,但他显然在反思自己曾经轻信了的中国激进的“大工业现代化”实践。{15}从这种貌似中规中矩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徐迟得出结论:“不久将来我国必然要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
比较徐迟现代化理论的前后变化,我们会发现,一,他首先对现代化命题本身发生了质疑,既然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那中国文艺的性质就值得怀疑;二,“两结合”的文学究竟能否现代化,以及能否超越西方现代派文艺,必须等待现实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三,现代经济带来了现代艺术,那么现代化也必然带来现代派,如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现代派”等徐迟自创的概念便顺带产生了。
徐迟将笔触伸向了中国文艺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忧虑(理由和李准的两篇批判文章虽然贯彻了官方批判文章一贯的作为,但却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论证)。{16} 官方报刊陆续展开了对此类观点的批判。能够抓住文艺发展方向问题展开批判的文章有刘锡诚的《关于我国文学发展方向问题的辩难》{17},但像刘文那样依然主张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才是中国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念,显然已经不得人心了。相反,徐迟的把文学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理论家的支持。尤其在文艺理论界,徐迟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流派。1982年,朱立元在《当代文艺思潮》创刊号上撰文《力促文艺学的现代化》,此后一年多的时间,该刊开设了“美学与文艺学的现代化问题”专栏,其中的许多文章,比如高尔太的《现代美学与自然科学》(1982.2)、李连科的《漫谈文艺学、社会科学及其他》(1982.2)、李祥德的《关于文艺学的科学化》(1982.3)等,都力图将文艺学和现代科学建立联系。由此可见,虽然当时主要的批判意见关注的是现代化与现代派到底有没有联系,引进现代派是否会令社会主义文化变质,但一大批新生的文艺理论家却从徐迟的猜想里获得别样的灵感,他们关注现代化理论中的“科学”意味,希望通过这个万能的工具,实现各自学科体系的现代更新,以此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界,蹈袭这一思路的人其实很多。“意识流”被介绍进来的时候,也曾披着“现代科学”的外衣;“新批评”形式主义文论兴起之时,人们也热衷于在论文中画上表格、归纳数据;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倡导“熵”理论的林兴宅。到1985年所谓“方法论年”的出现,文学的现代化运动事实上已经开始偏离正常的轨道,现代化变成了技术化、形式化,“纯文学”从一柄“去政治化”、“去工具化”的“矛”迅速变成一面护守各色形式探索的“盾”。
徐迟的初衷,是要解决“现代派”和现代化这一最大国家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对80年代文学而言显然至关重要。“那时候,人们对一切新的东西都带有一种近似儿童的好奇,特别是有关‘现代化’——它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如何走向现代世界,而不是现代性的复杂展开过程——的种种言说和观念,不论是非对错,一律受到热烈的欢迎。……如同许许多多令人激动的舶来品一样,现代主义基本上是被视为能够推动‘改革开放’的因素,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当中,是被当作文学的‘改革’和‘开放’的必要动力来对待的。”{18}尽管如此,这一问题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均未获得有力的回答。在政治上,官方简单地认定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不容置疑,事实上是以回避的态度拒绝了与“现代派”的正面交锋;联系社会上已经出现的不可遏止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官方的这一态度表明变革时代的文艺政策自身也处在调整和应变的阶段。尤为可惜的是,思想界缺乏足够的支撑,为以解决文学“怎么写”的万能钥匙{19}面目出现的“现代派”文学及各种新潮批评方法提供更深刻的经济、文化、政治、心理和思想资源。尽管以今天后世者的眼光看去,现代派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最终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合流,但这反而更加阻碍了人们对“现代性的复杂展开过程”作深入而细致的辨析,“人们满足于对现代主义的肤浅了解,对于自己的相关知识只不过都是一般常识这一点,也好像没有什么不安”,{20}这样做的后果之一,便是从根本上放弃了对“现代派”(或现代主义)作文化政治上的认识,而这个“包藏祸端”的“主义”在纯形式的包装下得以顺利进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语境,这令刚刚从一体化文学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新时期文学再次迅速且自觉地融入到国家政治的统辖之下,而对此的反抗,只有当现代化越来越暴露出其内在的不均衡性(heterogeneous)的时候,另类的现代性才可能成为文学发展下一步的根据。
① 徐迟创作年谱见附录二。
② 徐迟:《文艺和现代化》,第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③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见《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④ 徐鲁:《徐迟:猜想与幻灭》,第6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出版。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邵燕祥先生也说:在他决心以写作为政治服务的年月,他是真诚的,没有个人的功利之念。他在1956年真的相信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将建成一个六十万人的大柴旦市;他在1958年真的相信他所眷恋的江南故乡已经成为“无蝇小镇”。他这样歌颂了……我们可以责之以轻信,却不是虚伪。
⑨ 徐迟:《二十岁人·序》,转引自徐迟:《我的文学生涯》,(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⑩ 朱自清:《诗与建国》,载《新诗杂话》,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0月,1版,根据作家书屋1947年排印。
{11} 周扬:《在外国文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1978年3月13日)》,《周扬近期文集》。
{12} 叶君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序》,(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13} 徐迟:《文艺和现代化》,第2~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14}《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4
{15} 作为文学家,徐迟在概念的适用上并不是很严密,但大致上,他把近代资产阶级新兴时期的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时期看作是“近代化”的时期,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社会看作是“现代”时期。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现代化观念,我们无法考证他的思想来源,不过美国著名的现代化理论家阿普特也认为现代化是指除了工业化以外的社会变迁,而通常我国理论家都将工业化包括在现代化的总体框架之内。有关近代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和涵义等问题确实颇为复杂,在此本文不作学术上的梳理。对中国现代化理论有系统研究的有: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大学2005年出版);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6} 张光年日记记录了当时的隐情:1982.10.31 晚吴泰昌来。……说下期《文艺报》转载了徐迟提倡现代派文章,同时发表了李基凯写的“质疑”文章。我觉不妥,但这期已付印了,听后不胜忧虑。半夜醒来,越想越不对,应当提意见。1982.11.1 晨为《文艺报》11期内容打电话给唐达成、孔罗荪。8时唐来,谈考虑转载徐迟文经过。我系统地谈了几点意见,主张停印、抽换,说明这是郑重考虑的参考意见,请他向党组、贺敬之转达。如来不及,就按中宣部意见办,我保留自己意见。2日 唐达成来信,经向贺、冯汇报后,认为《文艺报》11期如果停印,会引起震动,只好在12期补救。5日 晚贺敬之来。他说明天去西安。谈到批现代派,他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也谈到补救措施。7日 下午唐因来谈。表示同意我对讨论现代派问题的意见。1983.1.19晚接文井电话,对《文艺报》批现代派仍然深感忧虑。1983.2.11《文艺报》对“现代派”的批评方法不对,文风不好,脱离了老、中、青作家,值得总结经验。建议抓住徐敬亚文,深入批评,不要扩大化。
{17} 当代文艺思潮,1983.1。
{18} 《视界》总第12辑卷首语。
{19} 李劫在回忆80年代对各种文学形式的探索时说:“要前进就需要不断地换钥匙,而一换就是一个突破——突破自己。”参见李劫:《个性·自我·创造》(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
{20} 同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