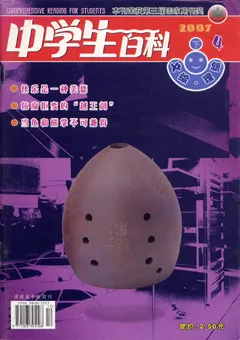“反向歧视”是否符合政治正义
2007-12-29石勇
中学生百科·悦青春 2007年4期
1945年,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幽灵仍然徘徊,一位叫斯威特的人申请进入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法学院就读,但没有被录取。校方的解释是,按当时的得州法律,只有白人才可以进入法学院学习,而不幸他是个黑人。
26年后的1971年,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已瓦解,一位叫德芳尼斯的犹太人申请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但是他被拒绝了。原因是他的分数不够,但是,如果他是一名黑人、一名菲律宾裔人、一名拉美裔人、一名美国印第安人的话,他的成绩足以使他被录取。
德芳尼斯作为一名犹太人,在美国是“强势族群”。犹太人的“厉害”全世界都知道,要钱有钱,要势有势,在美国甚至能影响白宫。但黑人、印第安人等族群则是十足的弱势族群。黑人在历史上是作为白人的奴隶而存在的,一直受到法律的公开歧视和限制,直到20世纪中叶才挣脱了法律的歧视,但观念上的歧视延续至今。印第安人的历史则更是在白人的屠杀和歧视中充满了斑斑血泪。美国的白人强势族群欠下了黑人、印第安人等足够多的“孽债”。
和斯威特一样,德芳尼斯也告了状,案子一直闹到美国最高法院。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
但是,他们的不同是,斯威特认为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因为当时得州的法律不允许黑人学生就读州立大学的法学院,这是对少数民族和弱势族群的歧视;而德芳尼斯认为自己作为犹太人,受到了华盛顿大学照顾少数民族和弱势族群的相关规定的歧视,使自己不能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得就学的权利。换言之,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不过一个认为自己是歧视的受害者,另一个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恍如隔世之间,从歧视到“反向歧视”,都摆脱不了“平等的权利”的“追问”。
从政治正义的角度上讲,公民在权利上必须受到平等的对待,黑人应该像白人一样享有就读法学院的权利。但是,德芳尼斯作为个体,在少数民族和弱势族群在竞争上仍然没有和白人在一个起跑线上而必须“照顾”的背景下,他的权利也戏剧性地像斯威特一样被不公正地对待。对此,最高法院又怎么说呢?
一个强壮的成年人和一个瘦弱的孩子赛跑,他们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我们说这个比赛是不公正的。很多人会说让孩子站的起跑线往前一点,才是公正的。正是基于“起点平等”才能“公平竞争”的考虑,美国民权运动后开始了对曾经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和弱势族群的补偿。通过开展“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在大学招生、财政资助等方面照顾少数民族和弱势族群,让因历史和现实处境根本不能与白人竞争的他们能够拥有接受高等教育以改变底层命运的机会。由于这牵涉到历史上的“侵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补偿”是难以让人指责的。
但是,这就对白人族群构成了“反向歧视”,他们要拿出比黑人等更高的分数才能享有与黑人一样被录取的权利。从抽象的族群关系上说,这当然符合政治正义原则。但摊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头上呢?很多人当然认为强者对弱者的补偿是应该的,但是,这种补偿的代价能够让具体的个人来负担吗?历史上白人强势族群当然欠了黑人等一笔“债”,但又凭什么要由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构成对黑人的实际侵害的具体的个人来“还”呢?不错,制度性侵害只能由制度性照顾来纠正和补偿,但从制度性侵害中得利的并不一定就是从制度性照顾中受损的人。当一个白人穷人因这种“反向歧视”而受到了损害时,这对他是否公平呢?
最终,德芳尼斯案作为一个个案进行了灵活的处理。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并没有判他赢还是输。在下级法院对他作出了有利的判决后,他被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录取了。而最高法院对此保持了沉默。
德芳尼斯案的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平等对待”观念的冲突:在族群层面上,如果录取德芳尼斯,则对那些与之竞争的黑人、印第安人等构成了不公平,因为他们整体上处于弱势,要求他们“平等”地与白人强势族群竞争在某种意义上等于限制了他们的机会;而不录取德芳尼斯,在个体层面上,则又对德芳尼斯构成了不公平,因为就个体来说,宪法平等保护每个个体,你很难认为他必须承担制度所要求的群体层面的补偿代价。的确德芳尼斯并不拥有进入法学院的绝对权利,但你也不能说他没有权利。最高法院的灵活处理和沉默,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
“反向歧视”是否符合政治正义?像其他问题一样,在美国仍然处于巨大的争议之中。而对它倾向于哪种判断,正是美国政治晴雨表的反映。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