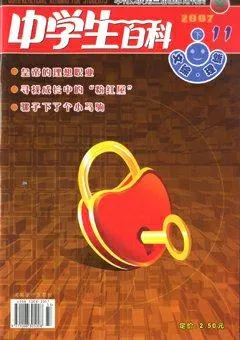龟的结构主义
2007-12-29白波
中学生百科·悦青春 2007年11期
关于乌龟壳的来历,有这样一个故事:
上帝喜庆的时候(我忘了为什么,也想象不出上帝有什么可喜庆的:生日?结婚?升官?)龟没去,因为它不想离开家。于是上帝大怒,惩罚它永远也不离开家——它的乌龟壳。
如果这故事当真,那么这次惩罚已经有两亿年之久——差不多在晚三叠世,最早的龟就已经背着它的家飘游四方了。经过两亿年的沧桑之变,龟有充分的时间和充分的理由把这个家弄得更像样子。你不妨说,它成了个结构主义者,龟壳就是它最精致的结构。
顺便说一句,龟壳与“王八盖子”不是一回事,龟和王八(鳖)是两类不同的动物,当然,它们是表亲——鳖起源于早期龟类。两种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甲壳上:鳖甲即“王八盖子”是一层骨板,从里面看上去有点像人脊椎和肋条,背甲和胸甲可以分开;而龟甲分两层,下面是骨板,上面是盾片,胸、背甲由骨桥连为一体。
龟壳就是这样一个自足、圆满而适度的结构,它的攻守兼备和进退有据是值得称道的:它严密、坚固,可以有效保护自己,同时四肢和头尾又能伸出接触外界,便于运动和取食。这个精巧的结构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它保证了龟最大限度地生存和发展,两亿年来发生了无数腥风血雨的天灾人祸,包括让恐龙全军覆没的“大灭绝”,龟却依然驮着它那温暖、亲切、安全可靠的家优哉游哉地来来去去。不但家族繁盛(1835年,达尔文乘坐着贝格尔巡洋舰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时,漫山遍野的巨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它还成了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这一切不是有赖于龟壳的有效保护和节能功效吗?如果说,其他动物“更高、更快、更强”,也是出于无奈:它们没有如此圆满的体系可以依靠。
当然,这个保护了龟两亿年的结构不可能没有一点代价:龟壳限制了它,它不可能站起来,不可能两手合抱,不可能长出尖牙利爪,奔走如飞,它只能爬,在这个星球的漫长历史中很有耐心地爬。
龟壳带给它的另一损失是名誉上的,由于某种结构上的相似性,龟替某些人背上了骂名。(人类也会把它和别的什么结构“结构”到一起去,这肯定是龟始料未及的。)虽然这对它并无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伤害,但“修名之不立”总是个遗憾——尽管这很有点莫名其妙,有点突如其来。
一种结构,就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它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囚笼。问题是,没有人可以离开结构,只要他活着,就必须找几条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而他自己,也就被这些原则和方法规定起来。正如爱默生对海龟的不屑评论所言,海龟的思想离不开它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说是一只海龟(当然,不是前面一段中的含义)。
由于缓慢,由于长寿,对于人类,龟的结构主义很有些哲学意味。一个小老太太曾经就乌龟的问题教诲了大哲学家罗素,她告诉罗素:这个世界是驮在一只大龟的背上的。哲学家问她:这只龟又站在哪儿呢?“一只更大的龟背上。”小老太太信心十足地答道。
编辑/姚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