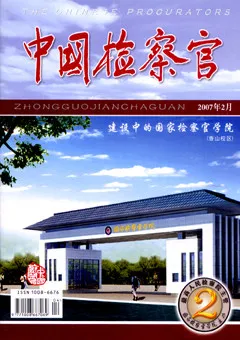《刑法》中援引定罪处罚规定的适用及评价
2007-12-29魏娟玲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07年2期
内容摘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援引定罪处罚之规定,即以某条定罪处罚的规定较为常见,这些规定不仅涉及对行为人的定罪,而且也涉及对行为人的量刑。从法理性质上看,有的规定属于提示性的规定,有的属于法条竞合,有的规定涉及罪数。对这些规定作出合理的评价,对于刑法立法的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援引 定罪处罚规定 罪刑法定原则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援引定罪处罚之规定,即以某条定罪处罚的规定较为常见,这些规定不仅涉及对行为人的定罪,而且也涉及对行为人的量刑。从法理性质上看,有的规定属于提示性的规定,有的属于法条竞合,有的规定涉及罪数。对这些规定作出合理的评价,对于刑法立法的完善有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提示性规定
在现行《刑法》中,以援引定罪处罚的规定有30余处,其中,提示性的规定就有10余处,占了大约三分之一。例如,第163条第3款、第183条、第184条第1款和第2款、第185条第2款、第242条第1款、第271条第2款、第272条第2款、第339条第3款、第361条、第362条、第393条、第394条等。仔细梳理一下这些规定,几乎全部来自于79刑法以后的单行刑法。如果说在单行刑法中确有必要做出提示性规定的话,那么,在修订后的统一的、完备的刑法典中,做出重复性的规定,如果不是立法者的疏忽,那便是立法技术上存在问题。如,《刑法》第185条规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国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和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非国有金融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述行为的,依照受贿罪定罪处罚。在本条中第1款所列人员的上述行为本来就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行为,第2款所列人员的上述行为是典型的受贿行为,事实上,不用在立法中强调也会做出正确判断的,因此,用一个条文作此重复性规定,其必要性是大可怀疑的,建议以后修订刑法时将此类规定予以删除。
二、关于刑法用语问题
在我国《刑法》中,有的援引定罪处罚规定的用语不甚规范,例如,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种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首先,何谓“携带”?如果说随身带着即为携带,那么,将凶器放在被害人看不到而行为人能实际控制并能随时支配的地方也应理解为携带,如是,则极大地混淆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抢劫罪应以行为人当场是否施暴等为准,不以行为人的事先准备为准。如果行为人事先以抢劫为目的并为此作了必要的准备,到犯罪现场以后改为抢夺的,构成抢夺罪。然而,根据本款的规定,要定抢劫罪,不仅会给刑法理论带来混乱,而且会给司法带来麻烦。其次,何谓“凶器”?如果说一切足以致人死伤的器具均为凶器的话,那么,甚至生活用品也可以成为凶器,如水果刀、领带等,如果行为人佩带领带或者携带水果刀实施抢夺的,就构成抢劫罪,很难说具有合理性。最后,既然携带凶器抢夺的,要按抢劫罪论处,那么,携带凶器盗窃的,尤其是携带凶器准备抢劫但到犯罪现场后改为盗窃的,为什么不以抢劫罪论处呢? 鉴于本条款的缺陷,笔者认为,在适用时应作限制解释:(1)携带应具有明示性的特征,即行为人所携带的凶器应让被害人看到或者直接感知到,如果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被害人不能看到或者不能明显感知到,就不会给被害人反抗增加难度,从而不能定抢劫罪,这是抢劫罪本质特征的必然结论。(2)何谓凶器应以一般人的认识为标准加以判断,即一般人认为行为人所携带的器具能对一般人的心理产生威慑效应的,这种器具就可以被认定为凶器。鉴于这种认识,枪支、管制刀具等可以被认定为凶器,而日常生活用品如领带等由于不能对一般人产生心理上的威慑力,不能认定为凶器。当然,修订刑法时,当修改为宜。
三、关于刑罚配置问题
刑法中涉及罪数问题的援引定罪处罚之规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于行为人的前罪行为或造成了前罪构成要件所不能包含的严重结果或实施了前罪行为后又实行了一定的不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而以准依之罪定罪量刑。如此一来,很容易造成刑罚配置不当的问题,这是罪数问题分则立法时尤其应当注意的问题。如,《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里的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是指因实施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非故意地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包括自杀)。 由此可以认为,这里的致人重伤、死亡是非法拘禁犯罪行为的加重结果。从字面上理解,这里的致人伤残包括致人伤害和致人严重残疾两种情况。其中,致人伤害不应当包括致人轻伤,因为致人轻伤已为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所包括。因此,这里的伤残是指重伤和严重残疾。依照准依之罪即故意伤害罪的规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非法拘禁非故意致人重伤(包括自杀)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非法拘禁因非故意导致他人重伤(包括自杀)的法定刑与非法拘禁使用暴力导致他人重伤而构成的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持平,不太妥当。再如,《刑法》第333条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这里的伤害如何理解,在理论上有争议。笔者认为,这里的伤害不应当包括轻伤,因为,根据法理,轻伤结果已被本条所规定之罪的构成要件所包括,因此,伤害应仅指重伤害。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下面的问题:强迫他人出卖血液对他人造成重伤的起刑点为3年有期徒刑,而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起刑点为5年,并且对此应当并处罚金。由此,对前者的处罚可能轻于后者,明显失当。不仅如此,本条规定了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或者强迫他人出卖血液致他人死亡的如何处理,并未规定。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条所规定之罪的法定刑畸重,应予调整。但在调整之前应如何处理,则涉及到价值观念的定位问题。有学者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认为,(1)对于非法组织卖血和强迫他人卖血致人轻伤的,应依照本条定罪。只有非法组织卖血致人重伤的,才依照故意伤害罪定罪;(2)强迫他人卖血致人重伤的仍定强迫卖血罪;(3)强迫他人卖血致人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定罪。该论者认为,不这样作,将严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笔者认为,论者的这种解释貌似合理,但却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我们知道,较之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要高于前者。其基本的精神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本着这一精神,定罪量刑时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一直并将永远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神圣使命。因此,立法上出现了问题应该通过法律的修改加以彻底解决,而不应该通过既不合法又不符合法理的解释加以解决。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在对这种缺陷立法进行解释时,应该坚守罪刑法定原则这个阵地:(1)根据法理,非法组织他人卖血或者强迫他人卖血致人轻伤的,依照本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2)实施上述行为致人重伤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3)强迫他人卖血故意致人死亡的,由于符合牵连犯的特征,应择一重处断;强迫他人卖血过失致人死亡的,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仍应以本条第1款规定定罪处罚。
四、关于犯罪情节问题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有的法条规定的犯罪情节出现了断档的问题,如,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规定在第247条中。这两个犯罪的一个总的特征是,行为人对被害人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摧残折磨,其行为的结果是造成被害者死伤。如果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明知并且是希望或放任态度的,根据本条的规定,依照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行为人对他人死伤结果的发生是过失的,如何处理?如果认为可以在本条所规定的刑档(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内量刑,那么,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国家权力而导致他人死亡所构成犯罪的处罚反而轻于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没有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导致他人死亡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处罚,这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本条的刑度应该调整,《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