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的另一副面孔
2007-07-03子余
子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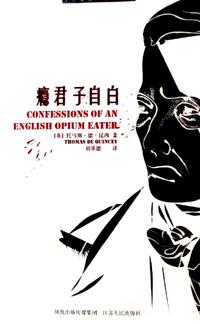
《瘾君子自白》
[英]托马斯·德·昆西 著
刘重德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如果你听到这样一句话:“特别注意一次不要服用25盎司的鸦片酊”,一定会浮现出白衣护士、医生、病房、病人以及一双忧郁的眼睛 ……决想不到这句话的听者却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作家。当一位依靠思想生存的人已经在红、紫葡萄酒中无法获得镇静的时候,科学与愚昧的共同产物之一——“鸦片酊”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一种深刻的亲身经验,通过德·昆西——一位英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批评家口中说出,使人耳目一新。
之所以德·昆西将自己称为“瘾君子”而不是“鸦片鬼”,这不仅因为18世纪西方上流社会的绅士们流行“滴用”鸦片酊而形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按照德·昆西的说法:“我十分遗憾地说,他们的确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在形式上不同于旧中国那种伤风败俗的“抽大烟”,而且在目的上也因为当时的西方绅士们往往将鸦片酊当成一种开启智慧的清醒剂,而不同于解除痛苦的麻醉剂。正如德·昆西非常喜好的那种“一杯不放糖的掺有鸦片的尼加斯酒”。
德·昆西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我就向鸦片寻求聊以自慰的办法。因为鸦片(像一只不加分别地从玫瑰花和烟囱的煤灰中采集酿蜜原料的蜜峰那样)能够万灵地使所有感情俯首听命。这些漫游有时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因为瘾君子是非常高兴观察时间的推移的。”这就是鸦片酊那种能够带着绅士们“穿过时光隧道”的作用。
由于德·昆西对文学创作那般超人的投入,尤其是他称之为“牛津街,你这个铁石心肠的继母”曾经让他无法安宁而导致他的理智产生混乱所带来的那种折磨,德·昆西不得不从1804年至1812年间连续8年服用了鸦片酊。记得有本叫做《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书,描述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德莱尔。他曾经写了一本《恶之花》,坦率地公开剖析了自己的双重灵魂:一种是浪漫的诗性,另一种则是对鸦片酊的沉迷。他就是另一个德·昆西。
在德·昆西的自述中似乎折射出这样一种“道理”:“有节制的疯狂要比无节制的约束更可爱,无节制的约束则比有控制的疯狂更可怕。”这句话即使用在精神无比痛楚的德·昆西的身上,也需要有那种“服用鸦片酊作为清醒剂”的经验去佐证。德·昆西就是这样做的。当然,人们不能因为德·昆西的经验而有理由去亲自服用鸦片酊。因为鸦片酊作为一种介于迷幻剂与镇定剂之间的奇特“药物”,我们实际上已经无法获取。而它的种种替代品——如今被称之为“毒品”的一类却因为人们无法控制它的毒害而贬劣或诋毁了鸦片酊原有的“善良面孔”。
所以,面对这部《瘾君子自白》,读者可以将它当作一种“知识的读物”,比如精致的鸦片酊及其服用特点与粗俗的“鸦片丸子”存在着区别,也可以当作“伦理的读物”,比如德·昆西并不认为“自我征服是能一蹴而就的,而自我放纵是容易受到曲解和怀疑的。”他似乎希望通过非常流畅的8万多字向读者一股脑地证明自己具有一种超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即一种对于放纵之度的自我控制。
在德·昆西看来,在自己每天饮用的尼加斯酒中有控制地加入少于25盎司(约1000滴)的鸦片酊,这就是一种对那世人不齿之劣行所做的一种有控制的尝试。正如德·昆西自己所体会的那样:“罪犯和不幸者本能地怕受公众的注意。”18世纪西方上流社会的“瘾君士们”往往像华兹华斯动人诗句所描述的那样——他们都在“谦恭地表示一种忏悔的孤独寂寞之情”,而德·昆西却是其中最坦荡的一位。
当然,也许他的职业促使他将自己的隐私选作了创作的题材——尽管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题材,甚至难避误导读者之嫌。好在他聪明地选择了一个人们往往忽略或不屑一顾的视角——这就是“鸦片的另一副面孔”。于是,在“鸦片酊”的背后,德·昆西对自己饮食鸦片酊的行为做出了伦理学意义上的剖析。
可见,德·昆西具有超人的自负,不然他就不会说:“一方面我的自我控诉并不等于坦白认罪;即使如此,别人从付出重大代价换取的一种经验教训的记录中所获得的好处,对我在上面评价过的那类感情的任何损害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补偿,同时也可能证明对于这条行为准则(指罪犯和不幸者本能地怕受众人的注意)的违反是不无正当理由的。”就这样,伦理的刀片非常容易地剖开了德·昆西那饱受鸦片酊浸润的肠胃与神经。德·昆西用自己看来并非“自残”的行为为读者们做出了长达八年的“牺牲”,以揭开“鸦片的另一副面孔”。
我们如何来评价德·昆西的这种对读者的“奉献”呢?
说德·昆西美化或夸大了“鸦片的另一副面孔”对那“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的正面作用,这是不确切的。“鸦片颂”是不存在的,而作为世界散文库中的极品,“鸦片酊”已经被化作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让德·昆西能够区别于一般作者而敞开话匣的“由头”,如同那串起珠子的丝线。当人们欣赏与玩味那珠子的绚烂时,他们实际上是看不到那丝线的,至少是他们对那隐藏的丝线是不屑一顾的。这正是德·昆西的妙手之处——他巧妙地将这丝线隐藏在他异常华丽的词句与流畅的思绪之中了。
然而,德·昆西在手法却做了个假:事实并非他所说的那样——在《瘾君子自白》快要结尾之处,德·昆西误导读者说:“明智的读者的兴趣主要在于会集中于它所具有的那种迷人力量,而并不在于那种迷人的阵阵感受。故事的真正主角和兴趣所在的合法中心是鸦片,而不是吸食鸦片的人。目的是演示鸦片的神奇作用,不论是引起快感的作用,还是引起痛苦的作用。如果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故事也就完了。”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认为在那“鸦片的另一副面孔”背后,一定是一张值得人们去伦理的人的面孔,他已经带给读者一串串的为什么了!
准确地说,占据一半以上文字的“《瘾君子自白》之序”的确是一个对于德·昆西灵魂与行为的伦理解剖,而那仅占1/3篇幅的“自白”所说的才是鸦片。我十分自信地认为,读者也会产生一种与我同样直觉的读后感:当智商和激情需要与健康争宠时,“鸦片酊”便有了“出趟”的机会。难怪越来越多的人耳听着“吸烟有害健康”的忠告,却怎么也不会将它理解为“吸烟有害智商”。由于世道越来越残酷,人们在维持生存方面对于“智商”或智力的依赖程度已经越来越大于对于健康的依赖,鸦片一类的“非标准食物”似乎有了悄然泛滥的理由。这的确是一个可怕的事件。
而更为可怕的是,兴奋剂与镇定剂之间原来不可逾越的鸿沟,如今已经渐渐地被“滴剂”的过时或“不作兴”所填平,鸦片原来的两张面孔——迷幻与安定更被不加区分地重叠在了一起。于是,人们提及鸦片便会立即联想到了伤害、狂野甚至东亚病夫和林则徐。然而事实却是:精神与身体同时获得安康依然是当代医学并未彻底解决的难题,这也是一个仅依靠医学所不可能解决的难题。
如此看来,我们不妨可以将《瘾君子自白》这个世界名篇当作一种特殊的心理学读物为好,它至少能够揭示甚至解释一个特殊人群的心理状态——即对于某事物的病态型依赖往往不仅源出于心理依赖,而且夹杂着相当大程度的自信和自负。德·昆西以他的“说”替代甚至拒绝了读者的“做”,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德·昆西在他曾经直面过的“鸦片的另一副面孔”之后,将藏匿在这面孔表情背后难以言表的心理做了一个非常精致的伦理解剖。因此,人们终于能够享受一种难得的、只有在德·昆西接受鸦片酊之安定治疗之后才能创作的美文所带给我们的那种语言的气势、音乐性和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