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记》:女权外壳下的男权突围
2007-05-14张江南
张江南
这就是彭浩翔的那杯茶:“真爱至上”的缠绵絮语从来就与彭浩翔无关,取而带之的是不可避免的两性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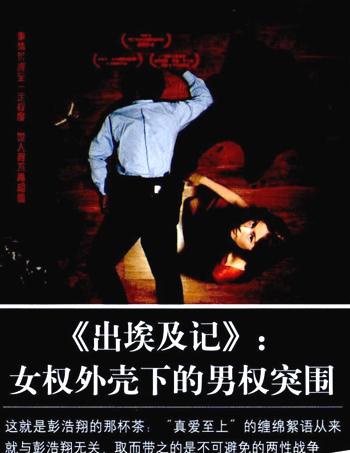
《出埃及记》是香港鬼才导演彭浩翔的最新力作,无论从议题、美学角度而言,还是站在导演彭浩翔或是香港电影整体创作上来考量,它都注定是部会引起争议的电影。
片名出自《圣经》的第三章,所指颇丰:以色列人对上帝从顺服到不顺服的经历,以及埃及法老所受的在多数人听来匪夷所思的巨大灾难。彭浩翔极具创意地将这些缝合进自己的新作:以色列对上帝的关系转嫁到女人对男人上,而埃及法老则化身为男主人公——没有升值机会的警察詹建业,他要面临的灾难是一个同样难以置信的事——“女人有组织地暗杀男人”。导演从这个大胆骇人的创意出发,展开讨论当下现代都市空间里两性关系。
从《公主复仇记》《依莎贝拉》里传统两性关系与价值的崩溃,再到《出埃及记》里惟有杀之而不能解决的两性梦魇,我们已不难了解彭浩翔对爱情、对两性关系的悲观态度。
上世纪70年代,当女权主义兴起时,早有谭家明的新浪潮名作《爱杀》,展示了男人有组织地捕杀女人,道出男权的恐慌与危机意识。30年后,在彭浩翔看来,危机已不存在,当下已是女权上位、泛滥的时代,男人已在事业、生存、女人的夹攻之下,彻底沦为囚徒。
正如我们看到片中任达华扮演的男主人公詹建业所面临的:妻子支持其事业,却又嫌怨他对家庭不上心;岳母只将男人作为赚钱工具来评判,俨然一副瞧不起男人的嘴脸;邵美琪扮演的警队上司更是对其施加直线强权,威逼利诱……女人仿佛是一张无形的巨大蛛网,成为某种意义上秩序的象征,男主人公被牢牢地困于其中,只能喘息,毫无生气。
已入不惑之年的詹建业,多年来对事业家庭都尽职敬业,但他显然不快乐,也不满足,因为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网络里,他没有权力、地位、乃至尊严。同样作为男性的詹建业的警察同事关炳文,在女洗手间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所谓惊天“真相”——世上有个女人组织,正进行歼灭全世界男人的计划。她们发明了一种会令男人打嗝至死的药,死法如此正常,以至于无人怀疑是谋杀。
这对詹建业一潭死水般的生活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刺激,虽然最初他并不相信。很明显,导演真正要点明的元凶是“现实”——女人参与建构及所代表的新型秩序,这个秩序能在日常生活中让你窒息,垂死。
詹建业的调查不断深入,关炳文的死以及来自女人的种种阻力,让詹坚信“真相”确实存在。调查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人公求索、解惑的心路历程,还有必然的出逃与回归。男主人公最终在外遇中,于秩序外的爱欲关系中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权力与自尊,回到家中又与妻子重修旧好。纵然女人多么仇恨男人无情,男人还是最终掌握了局面。

片尾,詹不断打嗝,暗示其即将死去。导演显然是同情他的,比他罪恶的是那些只能杀男人的看似强势却无力的女人。
导演主观地给男人外遇在道德上以合理化借口,有一定的开脱之嫌。不过不必惊讶,因为导演此前名作《大丈夫》里男人集体出走“偷食”的疯狂行径都情有可原。影片有一个看似女权主义的外壳,但上演的却是男人如何对抗女人以求幸免的悲壮故事,地道的反女权的男权叙事。这就是彭浩翔的那杯茶:“真爱至上”的缠绵絮语从来就与彭浩翔无关,取而带之的是不可避免的两性战争,是充斥嫉妒、仇恨、占有、权力、欲望、责任等字眼的两性游戏。
《出埃及记》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中男人的处境的描绘,看似无比荒谬,但不可否认它是有其现实参照系的。何况,“男人末日”女性复仇的命题以及巨大的悬疑设置,只不过是叙事策略上的诱饵。今次导演彭浩翔的野心显然不只是再次讲述一个耸人听闻的都市声色黑色小品,而是从两性关系角度建构现代都会寓言,明摆着要向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靠拢。
经过《依莎贝拉》的成功尝试,彭浩翔这回明显在刻意打造个人美学风格(长镜头及风格化的场面调度),尝试用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克制来控制影片所有元素,这是本片最凸显的变化。彭浩翔的拥趸们一定会抱怨观影乐趣大打折扣。争议不可避免,但面对有如此严肃思考的作品,我们还能要求彭浩翔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