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市镇的自然发育松绑
2007-05-14秋风
秋 风

究竟是由民众自发地进行城市化,还是由行政权力催生城市?
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城市化,这一点无可置疑。那么中国究竟该如何实现城市化?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争论这一问题。有人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以充分利用聚集效应;有人主张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农业大国城市化的惟一选择。这样的争论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在这些讨论背后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理性与权力的自负:专家或者政府有能力事先知道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才最好,且政府可以用权力强制所有地区走那条被人发现的正确道路。
不过,在现实中,权力的支配十分强大,上面的争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了。大城市和所谓的“小城镇”都在发展,但基本上都是权力造城运动的产物,两种城市化模式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了。
权力造城运动的畸形格局
一个城市看起来要像个城市的样子,需将必要的资源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品供应。按照目前的制度,只有建制市才能够享有相应财政资格。而建制市的设立,完全是行政当局的事情。省城、地级市自然地享有建制市的地位,驻于该城市的省政府、市政府对其下辖的市县又享有几乎不受节制的权力,包括在财政谈判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为它掌握着下辖市县官员的升降大权。而每级都要创造好看的政绩,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造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每一级政府都致力于利用权力把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源投入到自己驻在的城市。地级市政府所在的城市除了自留资源外,市政府还可以利用其权力,集中全市资源用于发展该地级市。县政府也努力争取把本县变成建制市,即便不是建制市,县政府也会利用其权力汲取全县资源发展县城。
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权力主导之路。城市化当然有自然演进的因素,但也有太多权力主导的成分。由于权力本身是上下森严的,所以,城市也被人为地划分为三六九等。占据权力最高位置的城市占有最大优势,于是,国际大都市层出不穷,由此往下,大城市迅速膨胀,中等城市急剧扩张,曾经被视为小城镇的县城也差不多发展成中等城市了。
可以说,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城市化是权力掀起的造城运动的产物,这样的城市化进路,看似捷径,但这些繁荣的城市很可能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诸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因此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损失了很多,付出了很多机会成本。没有市建制、而很可能具有城市之种种自然要素的县城的发展,普遍受到地级城市的限制,普通城镇又受到县城的剥夺。即使它们已经具有城市之实,也无法享受城市的财政待遇,不能筹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
这样的进程形成的城市格局必然是畸形的,那就是头重脚轻。本来,这些普通城镇如果具有起码的基础设施,就可以吸纳大量人口。但由于这些城镇的资源被居于权力上位的城市夺走而无法建设基础设施,移出乡村的人就沿着城市级次向上流动,纷纷涌入地级市、省城、大城市及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大城市为了保卫自己本来就紧张的基础设施,必然倾向于利用现有户籍制度,设置那些违反宪法的人口流动壁垒。这一壁垒固然阻止了乡村、外地人口流入本地,反过来又阻止本市人口分流。于是,在大多数人口还没有城市化之时,种种城市病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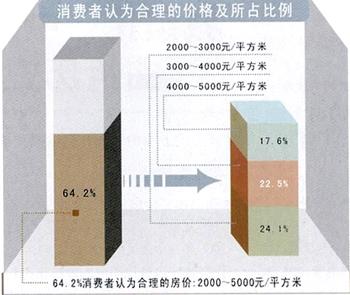
面对这些问题,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恐怕不能不思考关于城市化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是由民众自发地进行城市化,还是由行政权力催生城市?
市镇化的前景有多大
社会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只可能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这种市需要具备很多社会、文化、政治与经济条件。政府尽可用其支配的资源建造起高楼大厦,但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来一个市需要具备的文化、精神、社会等条件,而政府以权力支配城市扩张本身就意味着,该市不具备“市”的根本特征:自治。
当然,无数民众追求改善自身境遇的自发性努力过程,总是会顽强地表现出一种创造出健全的“市”的趋势。近些年来,在很多地区已能看到一种趋势,即乡村大量人口向县城和镇集中。有的是在外工作赚钱之后在此购买房屋,有的是乡村人口为经商、子女就学、养老等直接迁入居住,还有一些则是追逐工业迁入,甚至包括外来人口。
看起来,这些城镇有点像费孝通先生80年代提出的“小城镇”,但对费老设想也有所超越。费老把小城镇定义为:“一种比农村社区更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从目前情况,随着城镇深度卷入现代经济网络,这些城镇未必与乡村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今天已经出现另一种情形:大城市人口的郊区化,郊区可能出现某种新型市镇。
费老下述断言似乎也值得推敲:“小城镇是个新型的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许多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乡村社区的性质,但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小城镇其实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城市,如果正确地理解“现代化”的含义的话。现代化意味着城镇居民享有“市”的自治治理,享受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品,假如制度安排合理,这一切在小城镇完全可以实现。
但无论如何,费老的基本构想已在现实中获得部分证明,费老的构想本身又具有历史依据。古代的“城”与“市”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城”是官府进行权力统治的节点,“市”却是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以“市镇”来称呼费老所说的小城镇,可能更为恰当——这也可以与托克维尔所谈论的美国的township相对应。
历史上,中国各地市镇是十分繁荣的,尤其是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市镇数量与规模均持续扩大,到19世纪末,江南已有一千余市镇,其中颇多拥有数千户至万余户人口的巨镇。这些市镇乃是彼时江南社会、经济、宗教、教育等活动的节点,是经济繁荣与社会秩序的枢纽。5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控制资源、权力控制经济,这个市镇网络被严重侵蚀。地区、县、乡所在城镇被赋予了特权地位,不少“市”被改造成“城”,丧失活力;大量的“城”也冒充“市”。即便如此,后来的社队工业和乡镇工业,也仍然是以市镇为依托发展起来的。

费老在小城镇再次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生命力之时就预言,小城镇将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仅成为人口的“蓄水池”,而且将是商品的集散地和经济、文化的中心。对此笔者愿意补充说,以此为基础发育而成的“市镇”,也仅有此类市镇,有可能成为市民的自治实体。历史上市镇的自治确实是相当发达的,这是市镇的社会、经济、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市”民的价值理念终究是不同于城民和乡民的。以自然发育之“市镇”为基础,不仅是城市化的正途,也有助于以自治原则重塑中国的治理体系。
问题在于,尽管乡村人口在向市镇集中,但现行各种制度安排却并不与人口的这种流动趋势配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镇被权力制约,无法建立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自治的治理架构,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建设城市化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品供应体系。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配套,则小城镇发展也不过是重蹈大城市发展的覆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