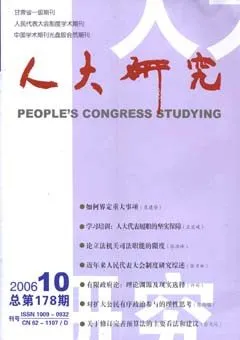对《人大扩大权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法治》一文的质疑
2006-12-29缪士鼎
人大研究 2006年10期
《中国新闻周刊》载文《人大扩大权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法治》(下称《权文》)说,广东、浙江地方人大扩大权力有利于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文章在人大制度、人大职权等国家政权的根本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很值得研究和澄清,否则将带来误解、误导等消极后果。《人民代表报》刊文指出:《权文》中国家政体观点是不正确的。笔者尚感言犹未尽,就几个主要观点分别一陈管见。
一、我国的政体不是“议行合一”,是“议”决“行”为。
《权文》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可以说是‘议行合一’。”这是不正确的。
所谓政体是指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 (根本政治制度),即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用什么方式来行使政治权力,它是由国体决定的、为国体服务的,又是国体的必然表现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政体,是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我们党在政权建设中走群众路线的最好的、最有效的形式。”(吴邦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是由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的、为国体服务的,又是国体的表现形式,舍此,工人阶级就无法组织和巩固自己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曾说过,人民的政权要议行合一,立法权同时又可以是执行权。这一点,马克思只是就巴黎公社70多天的政权组织方式的总结。国内也有专家认为,行政权不能与立法权相抗衡,至于此两种机关是合一还是分开,只是形式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议行合一”不利于人民政权发挥作用。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曾有过“议行合一”的经历和教训。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周恩来同志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作说明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至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在此期间,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政权组织形式都是“议行合一”。1954年宪法制定后,中央的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分开。地方情况有所不同,此时,虽然地方政府专指地方行政机关,但由于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不设常设机构,以增加会议次数(县级以上每年两次,乡镇四次)解决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经常性行使职权问题。这就带来两个突出问题:一是闭会期间的领导人变动,人大无法及时处理;二是经济建设、财政预算等年度性的事项,很难作为半年一次的人代会审议议程。为此,195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地方各级行政主官和法院院长缺额补充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方人民委员会行使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职权。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民委员会这一由地方人大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代行人大常设机构的职权。人大会议和人大选举,都由人民委员会召集和主持。这一时期的人民委员会集治权(政府权力)与政权(人大权力)于一身,实际上仍是“议行合一”的体制。
代议和执行两种机构的价值目标、权力特性及其组织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实践中存在行政权逐步膨胀的倾向,权力机关的权力渐渐萎缩,这使人大的各项职权难以得到实质性的行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了一句空泛的政治口号。
为解决地方政权“议行合一”的组织形式,从1954年制定宪法时有人提出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到1981年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普遍设立;从人民委员会代行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职权,到“议行”一分为二,真正确立人大在地方政权组织中的主体地位、经常性地独立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力,党内外有识之士经历了近30年的探索和努力,实属不易。这是我国地方政权组织一项突破性的重要改革,也是我国人大制度建设的一个重大发展。我国的政体从理论到实践,不应该也不可能回到“议行合一”的老路上。
二、人大的权力不是扩大,是虚置甚多
《权文》说:“人大扩大其权力,是有利于推动整个政府照法治规则运行,有利于防范政府任何一个部门滥用权力。”此话原则性的失缺在于“扩大权力”。
宪法法律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有明确规定。在法定权的限定上,“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行;私权力,法无禁止皆自由。”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派生的行政、司法机关,皆属国家权力,是公权力。其任何“扩权”均属违法行为,结果必得其反:政府“扩权”带来违法行政;司法机关“扩权”带来违法办案;人大“扩权”干扰行政、司法,违背“不直接”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家机关“扩权”等同于滥用职权。
事实是,由于具体制度的缺失,人大权力的虚置是众所周知的。有学者指出,预算监督:最实的往往是最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预算的审批和监督,处于“程序合法,实质虚置”的状态。手段:最硬的却又是最软的。撤销同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罢免或撤销由本级人大选举或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这是最能体现中国人大民主特色的刚性手段,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是例行公事,很少行使自己的人事监督权。选举任命:“个别”的往往是“一般”的。法定的国家机关正职选举,“个别”的“也可以等额选举”,成为“一般”都实行等额选举;副职的“个别”任免,成为常规性的“一般”任免。决定:看得见的却又是摸不着的。重大问题决定权,全靠各地自行摸索;决定授予地方荣誉称号权,很少见到行使。可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权无力、有的无矢、有职无权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李静美:《人大的应然与实然》,载《人大研究》2005年第8期)。
“扩权”之说没有理论依据和事实基础,只有给人大带来“争权”或“滥用”权力之嫌。《权文》提及的广东、浙江地方人大现象,是对人大行权机制的有效探索。人大要真正职权到位仍要做更多的努力,但无论人大如何创新行权机制,均在法定权力范围之内,旨在职权到位,决非权力的扩大。
三、人大“硬起来”不是“可能带来弊端”,是必然要求
《权文》说:“从长远来看,一个硬起来的人大,也可能会带来某些弊端。”“导致一权独大,则整个政府体系的运转就会出现问题”,似有“杞人忧天”之感。
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吴邦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国家性质的核心内容和本质特征。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好形式”,它主要从“三个方面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一是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二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集中人民的共同意志,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三是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人大“一权独大”是法律的应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制约制度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实行单方向的监督制约制度。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司法机关的关系,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也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协作的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它能够对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监督实施。国家行政机关是人大的执行机关,执行人大决议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其不能脱离或者违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意志。只有人大真正“硬起来”,使法律的应然变为实然,行政、司法机关才可能依法定位,各国家机关才能沿着法定轨迹,协调一致、有序高效地运行,才能使“整个政府体系的运转”不出问题。
(作者单位: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区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