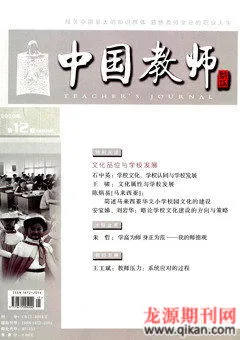给我一串钥匙
2006-12-29史晓风
中国教师 2006年12期
天色渐渐暗了,除了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车厢之间轻微的碰撞声,软卧车厢里一片宁静。
小时候,家里穷,用不起电灯,用不起煤油灯,连桐油灯盏也舍不得用三根灯芯,这迫使我养成一个习惯:睡觉之前,黑灯瞎火地、默默地把白天的功课温理一遍,记诵,思索,咀嚼(像牛的“反刍”),消化。旅途也不例外。
叶圣陶先生以为我睡着了,拿过一条毛毯,准备给我盖上,我赶紧翻身起来道谢,告诉他我没睡着。他问:“想什么呢?”听了我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叶先生感慨地说,逆境磨练人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要是家境好,也许还养不成这么好的习惯呢。
我说,学校里的地理课,课时不算少,但学的知识,考完就忘。听叶先生讲了“左阜右邑”、“阴”和“阳”,好像给了我一串钥匙,不但不会忘,而且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能够打开地理知识的宝库,为我所用。由此想到,咱们的各科教学参考书(专供教师用的)是不是也应该这么编:先提纲挈领地讲点规律性的东西,以帮助教师更快更好地使学生掌握一串钥匙。然后,提供一份参考书目,摘编一些精要的参考资料,因为有些大部头的书,教师买不起,借不着。
叶先生说,我也早有这个念头。最好编两套:一套叫“教学指导书”,就是你说的“一串钥匙”;一套叫“教学参考书”,要精选,不要“捡在篮里就是菜”。不过,从经济上考虑,从出版、发行上考虑,现在还只能编一套。你的想法,我们在进一步研究编辑方针的时候,会考虑的。
我说,这大概就是教育学上说的“启发式教学法”。最近听吴伯箫同志(时“萧”不作“肖”,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从长沙参观回来讲,毛主席学生时代办“平民夜学”的《夜学日志》还在,那上面他记了“用启发式教学”。无怪乎1929年12月,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写了十条“教授法”,其中第一条是“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第十条是“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大概是他青少年时期受到的新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西学东渐’的影响。
叶先生说,“启发式教学法”不是新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不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在我国古已有之。你回去可以查查《论语·述而》。我记得原文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两点:一是孔夫子把“启发式教学”跟“举一反三”合在一起说的;一是孔夫子连用了“(学生)不……(我就)不……”的句式,说明什么呢?用现今的哲学语言来说,“师”和“生”的矛盾,“教”和“学”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生”,在“学”。也就是说,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起码要做到“举一反三”。譬如刚才讲地名中的“阴”和“阳”,如果你不“举一反三”,就提不出“江阴”的问题来,我就不讲后一半,因为讲了也没有用。还有,编教学参考书,虽然是给教师看的,但你落笔的时候,心里想的、面对的还是千千万万个学生。想想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能,需要和可能掌握的知能,哪些是关键,哪些是难点,怎么讲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教育方法是为教育目的服务的。教是为了逐渐达到不需要教,使学生日后成人(合格公民)成材(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材)成器(“大器晚成”的“器”)。
(作者曾任叶圣陶先生的秘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