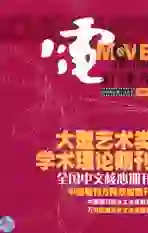用利刃解剖人生的奥秘
2006-12-01王利华蔡宁
王利华 蔡 宁
[摘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曹禺以写人为核心构筑了他的艺术世界,在借鉴西方现代戏剧内向化创作思潮的基础上,将创作视角注入到人生内部;用犀利之笔剖析了人性的矛盾,人生的困惑,人类的挣扎。形成了其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特点,成为中国话剧史上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师。[关键词]内向化生存困境人生困惑
内向化戏剧是十九世纪后期出现于西方的一种戏剧创作思潮。代表作家主要有易卜生、梅特林克、契柯夫、奥尼尔。虽这种思潮的称谓并不一致:有“心理象征剧”、“静态的悲剧”、“沉默的戏剧”、“内在戏剧性”等多种名称,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对人的内在生命的关怀。以往的研究者们或许更多地关注了曹禺剧作外在形式上对上述作家的学习和借鉴。但实质上,西方大师们对人的内心生活的关注,对人生奥秘的解剖更是曹禺所要借鉴的精神精髓。也正是由于对这一精髓的体认与吸收,才使曹禺的剧作摆脱了表面地追求矛盾;中突的激烈性、巧合性而把矛盾的视角引入人的内心世界,摆脱了“社会剧”的暂时性、功利性而走向了“人生剧”的永久性、超越性。从而使曹禺的话剧艺术走向了空前的完美,走向了中国话剧的最前沿。
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生存竞争日益残酷。世界大战及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体察到人的困境,长期积淀而成的人类文化传统在规范人们生活秩序的同时,也成为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桎梏。因而,无论是在哲学还是文学领域。人们都在反思着自己的时代,力图重新认识人的处境,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弥漫在我们的家园。“人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几乎成为现代作家的共同追询,在文学领域,现实主义思潮也发生着潜在的变化,作家们似乎渐渐把自己的目光从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书写转向对人类困境的关注。“人无路可走”,这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发出的哀叹;而在奥尼尔笔下,人的境况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程度的‘爱玛,而这个程度取决于是否善于妥协。我们或者无望地企图抓住自己的幻想,而最后却代之以某种廉价的代替品;或者我们盼望过最好的生活,而发现时间本身嘲弄地向我们提供了代替品,不过它是这样贫乏,以至对它可以不予理睬。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是悲剧人物。”[1]这种思绪发展到荒诞派作家笔下就成为“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的无奈。
曹禺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对“人”的处境最为关注的作家之一,在他前期剧作的创作意图中.对人的关注远远大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因而在《雷雨》发表后他屡次申明他所写的不是一出“社会问题剧”:“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诗的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赢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3]应该说,这种意识贯穿于他的所有剧作。如《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都像笼里的困兽,无法逃脱。侍萍承受不了被遗弃的痛苦而投河自尽。却被救了起来三十年风风雨雨使她明白了“人性太弱,太容易变”,对生活中可能引起的纷争与不幸,她采取处处回避的态度,但命运偏偏选中她与她周旋,在她稍有疏忽时悄悄找上门来,在她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在她女儿身上继续下去了。周萍不止一次地要离开恐怖而又郁闷的周公馆,他痛苦着、行动着,也躲避着,可是繁漪的一再阻拦,双重乱伦的打击,使他终于无法离开,并以死亡为终结;繁漪向专制、无情的家庭、丈夫挑战,近于枯竭的生命开始复苏,然而她很快便发现周萍并非是她所能依靠的男人,却又不甘心就此罢手,她开始行动,作出周密安排,万般无奈下甚至表示愿意周萍带她和四凤一起离开,但得到的却是周萍轻蔑的一笑,这迫使她不顾一切地作最后一搏,与周家一起毁灭。至于剧中那个冷酷而又矛盾的周朴园,难道他不也在苦苦地挣扎么?他要挣脱的是三十年前薄情寡义留下的阴影和苦果,他也无法逃脱——苦果和惩罚最终还是降临了。这里弥漫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这里有着“最‘雷雨”的女人,也有着如“一棵弱不禁风的草”般的男人,有在岁月中历练得冷酷但仍残存着一丝温倩的老人,也有对生活尚充满幻想的孩子。在这最浓缩的时间与空间里,所有的人都在纠缠着,挣扎着,或为了实现救赎,或为了追求梦想,或为了保持一点眼前的平静.可一切的努力都是无力的,最终的毁灭无可避免。在此。作者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命运,人对于一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的恐惧”和“不可言喻的憧憬”。
同样,在日出这部浓郁的社会写实作品中,在其社会批判的内涵之外,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的挣扎。李石清是由“不足者”努力挤上了“有余者”的地位——从小职员,经理秘书,刚刚提升为银行襄理(相当于经理助理)。作者说他有一个“讨厌而又可悯的性格”。为了向上爬.为了活得像个人样,他不惜在潘月亭面前,忍气吞声,谄媚逢迎,但最终还是被玩弄。潘月亭何等威风,何等呼风唤雨,又何等绞尽脑汁:但最终又同样免不了一切落空。黄省三想靠着自己的劳动来养活一家老小,可在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他辛苦一生到头来还是被逼得家破人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陈白露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有着自己活泼、纯真的“竹筠”时代,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沦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她厌倦上流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她虽然不能自拔,却还想救人,当她亲眼目睹“小东西”等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摧残、被蹂虐,痛苦地在生活中挣扎,而想有所反抗,尤其是当她知道小东西打过金八,便连声自语:“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陈白露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所缺乏也希望有的东西。她承认太阳要出来了,但太阳不属于她,她只能沉没在黑暗中,所以,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巨额债款无法偿还时,她只得在日出前服毒自杀。
由此看出,曹禺的作品不仅仅是对某个人的或某群人的生活历程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展现人的内心的自我纠缠,人的生存境况。正是这种生存境况才使人物长期处于焦虑之中,使他们感受到内心深处那种无言的苦痛。那么又是
什么造成了自我纠缠的生存境况?沿着这一思路轨迹,作者用他的犀利之笔开始了向纵深处的挖掘。
首先,曹禺看到了外在伦理规范与个体本能欲念的矛盾。人总是本着“快乐原则”行事,因而,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冲突,造成内耗,干扰了团体生活的有序运转,为此社会逐渐构建了一整套伦理规则,它在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但这也使人付出代价:它在抑制贪欲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人生的压抑,扼杀人的生气。特别是中国伦理体系发展到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已大大丧失了使个体平安相处的本旨。对人的本能欲念的压抑可谓登峰造极。曹禺笔下人物就是在此背景下挣扎着,其最典型代表是周朴园,当年,他由于顶不住伦理规范的压力,而忍痛遗弃了心爱的人,这既给对方造成终身痛苦,也使自己一辈子都走不出心灵阴影倘若不是社会习俗这一“笼子”的笼罩,他完全可以与侍萍比翼双飞在爱的蓝天之上。
其次,曹禺看到了人性异化与天然本性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从出现了私有制,便开始了人性异化的历程。或者说,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被异化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是建立在付出了人性异化的代价基础上的。但种异化由于违背了人的天性而造成了人内心的矛盾。如《雷雨》中的周朴园,其三十年前的爱情故事无疑符合中国古代男子“始乱终弃”的典型,富贵公子与美貌但地位低下的女子相恋,最终在父母的压力下,在金钱、地位的诱惑下抛弃了旧情人,奉命与名门千金成婚。这是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富贵公子人性异化的表现,异化的人性使他们抛弃了真正的爱情。但是,人的本性的呼唤又让他没有完全麻木,于是异化与本能造成冲突便形成了他的痛苦。《日出》中的陈白露曾经有着纯洁的心灵,曾是一个天真纯洁的书香小姐,但无力抵抗金钱的诱惑,堕落到人间最丑恶的地方做起了高级妓女。以出卖肉体来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在她的心灵中,魔鬼与天使始终在搏斗,一方面她为堕落而痛苦,在逢场作戏的同时也为出卖自我而疯狂地诅咒与忏悔另一方面,她却又无力摆脱金钱筑成的人间地狱,异化已成为习惯,本性又时时挑战习惯,醉生梦死中又痛苦万分,一部人生悲剧便如此自然而然地展开。《原野》中的仇虎又何尝不是异化与反异化的矛盾体。当剧中的仇虎以一个“复仇者”的形象出现时,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承负着强烈的文化指令的符号,“复仇者”是仇虎别无选择的命运,又是他无可奈何的角色。于是,在文化指令与个人意志的矛盾纠缠中,仇虎终于陷入了迷狂状态。
或许有人会说,曹禺的戏剧固然写出了人生的内心,写出了人的生存困境。但他把人生写得过于悲观,把人写得太无路可走。他没能给人指出一条可走之路。但是,能给人指出一条光明之路的文学固然是优秀文学,而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光明之路的文学也未必不是优秀文学。即解决问题固然是文学应当承担的义不容辞的任务,而提出问题更是文学当仁不让的主题。或者可以这样说,对于文学而言,提出问题或许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十分艰难的问题,不十分艰难的问题或许就不需要用文学来探讨。这也正是许多经典的不谋而合之处——当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敏锐审视人类的时候,便发现了众多人类前所未有的难题,于是,他们把难题呈现给我们,让我们思考,让我们体味。曹禺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与此——以他的善感之心,怜悯之心,写出了他看到的人生的困惑,人生的挣扎——他是让我们共同思考——我们如何走出这种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