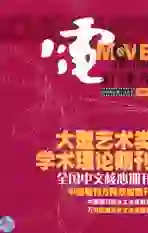《中国式离婚》:男性意识论略
2006-12-01刘高峰
刘高峰
[摘要]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播出后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该剧探讨了当代中国人的婚姻状况问题,从而显现出女性在男性意识下生存状况的无奈和悲凉。[关键词]《中国式离婚》男权意识无奈和悲凉
在中国古代,婚姻一旦被固定下来就很难动摇,当然这主要是传统的观念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男性的观念。在当代中国,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男性意识虽然有所淡化,但在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依然是女性服从男性,女性是甘愿作出牺牲的。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存观念支配下,男性意识往往会渐渐滋长,甚至发展到威胁婚姻的程度。在这种意识下,女性只有任凭男性的摆布,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家。2004年秋,由王海瓴编剧、著名演员陈道明、蒋雯丽领衔主演的23集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探讨了当代中国人的婚姻状况,提出了人到中年后如何“保养”婚姻的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男性意识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该剧以一个普通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为点,深刻剖析了三对夫妻的情感和他们各自在婚姻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凸现出在婚姻契约下的男性意识。
男性意识首先表现在宋建平、刘东北和林父身上的自私。在林小枫看来,造成平凡生活的主要原因是丈夫宋建平的无能,这就把男性推向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林小枫以承担全部家务而被迫下岗,成就了宋建平由国营医院到合资医院的转变,实现了家庭生活的根本好转,但这种好转“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1]作为代价的。这是女性怎样的一种无私呀!正是这样的一种无私,才加大了林和宋两人的距离,林开始感到了婚姻的危机,以致做出了被动的选择:监督。为监督她采取了种种极端的措施,甚至将双方的矛盾闹到了宋的医院,宋终于爆发了他潜在的男性意识,忘记了林为他今天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他离家出走了,把林置于尴尬的境地。这是何等的自私!在刘东北和娟子离婚后,刘还渴望在情感上占有娟子。当他怀疑宋建平和娟子有染时,就粗暴的用酒瓶打了宋,也许会有人认为他这是在爱娟子,但爱就可以欺瞒对方而自己就能随心所欲却还想占有对方的感情吗?在不少男性的观念中。自己可以心灵出轨或身体出轨,但却希望哪怕是将要分手或已经分手的妻子仍就死心塌地的忠于自己。这不是男性的自私是什么?林父和林母结婚后,在下放期间林父竟又好上了一个女子并生下了林小枫,这同样是男性的自私。
其次是宋建平和刘东北表现出的男性意识的欺骗性。宋建平为了达到不和林小枫在一起的目的。到医院找熟人开了个假证明,说自己的性功能有问题:为了得到离婚的目的,他导演了林小枫和刘东北的网上恋,导致林处于尴尬的境地。刘东北和“生鱼片”偷情被娟子发现后,竟说出这只是为了“解决一下生理问题”。这些都足以说明他们男性意识中的欺骗性。这一点和鲁迅《伤逝》中的涓生一样,他把不爱子君的理由说成是“免得一同灭亡”,无怪乎帕特里克·哈南在谈到涓生时说“在《伤逝》中,那个叙述者尽管满心悔恨,却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他“并没有特别说谎。但却都没有充分反映事实,也没有真正凭良心说话”。[2]这句话用在宋建平和刘东北的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林小枫被宋建平的遗弃,造成了她在话语上的无奈和悲凉。说什么呢?就说宋建平不要她了吗?她是教师,是知识女性,这足以说明她能讲出很多道理,可她讲出道理了吗?大喊大叫不属于知识女性的语言,那是属于所有家庭女性谁都能说出的话语,实质上她失语了,至少是在宋的面前。语言是精神最原始的冲动,是人类最根基的本质,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有赖于语言而得以可能。犹如海德格尔的诗意描述:“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凭借存在物的首次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3]解构主义者福柯的话语理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话语不仅仅是思考和产生意义的方式。而且决定它所力求控制的主体的身份的本质、意识与无意识、思想及情感生活。身体和思想感情都不能外在于它们的话语的描述而拥有意义。女性的情感、生命的实现终究有赖于语言的实现,没有语言的呈示,没有话语的权力,女性本体的种种欲望只能处于黑暗的遮蔽状态,缺乏生存的根基和栖息的家园。[4]在剧中我们分明看到了林小枫对欲望、思想、情感的无奈,她像沉默窒息的鱼,显得那样的悲凉。她曾努力地挣扎过,但这种挣扎只能增添她在男权意识下的悲剧感。她的多疑、无奈,甚至流露出的凄然、苍白,竟成了宋建平逃避她的借口。她的情感与宋建平不是对等的。正是这种男性意识对女性思维、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和话语的禁锢,使女性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剥落了作为人的完整性,失去了自我。
林小枫、娟子和林母不是没有责任。那就是她们内在的依附性人格。依附性人格是指一个人依附他人而存在,或是对经济的依附,或是对权力的依附,或是对精神的依附。林小枫为了过上现代大都市的生活,甘心为宋建平失了工作;娟子因为刘东北想要孩子,即使自己不想要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林母为了林父,无怨无悔的抚养着并非自己亲生的林小枫。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她们放弃了追求独立人格的权利,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另一个叛逆女性——娜拉,她“当初是满足的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她毕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5]娜拉走出的这个家庭是当时中国那些讲自由恋爱的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幸福家庭”。可以说,当娜拉早已觉悟而从这样的家庭走出之后,中国的女性却又在向这样的家庭走进:当娜拉想不作傀儡的时候,中国的女性却还在想作这样的傀儡。这是女性何等的悲哀!当然林小枫、娟子她们也有自救的意识,尤其是娟子,她在一开始就有抗争的意识,不过她们的自救是建立在灾难性的意识之上的,就像唐毅说鲁迅《伤逝》中子君的那样:“子君的全部骄傲和全部悲哀,在于她有一种自救意识,但是这个自救意识本身,是对“男权”社会的依傍。”[6]
林小枫是代表了中国太多的女性,她为了家庭能过上现代人的生活,不惜牺生自己而成全自己的丈夫。凭心而论,林自愿放弃自我这本身并没有错,这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她错就错在她的依附性人格。她以宋建平为中心,好像宋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去经营。宋建平跳槽后。她确实感受到了作为“夫人”的荣耀,那时高飞有求于宋在第二次老同学聚会上把林作为聚焦点,回家后,他无不荣耀的说:“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夫贵妻荣的滋味。”林小枫的这种依附性人格,从人性的角度讲是清纯的.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从生活的角度讲则是空虚而无力的,并且还隐藏着林潜在的奴性、卑怯。林小枫对自己独立精神的放弃,最终导致了宋建平的厌烦。事实上,在林依附性的人格上,折射出宋的一种男性意识。
不过,林小枫、娟子毕竟是新时代的知
识女性,她们为了自己的婚姻也曾在不断地和男性意识进行着斗争,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林小枫先是不愿意离婚,后来醒悟了。在欢送宋建平去西藏的大会上,她请求宋留下来并同意离婚,这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娟子对直接伤害她的刘东北,不是妥协而是离开,这同样是对男性意识的抗争。但她依然有依附性人格的一面,面对刘东北的不负责任,他把宋建平当成了救命稻草,她爱上了同病相怜的宋。相反刘东北像泄了气的皮球,围着娟子团团转。这是女性意识对男性意识的一次颠覆!是对精神自由的一次挑战!唐毅说得好:“女性和男性的所谓平等,只能是真正的、最后的、精神上的完全平等,这是一个前提,也是一个底线。”[7]
在古代的中国,男性总是渴望通过建功立业或寒窗苦读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达到光耀祖宗、封妻荫子的目的。他们要求女性只要管好家、照顾好老人、体贴丈夫、抚养好孩子就是好女人、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女性也总是以管好家为己任,把男性的需求当作自己的意愿。十里长亭,送别时虽有“执手相看泪眼”的痛处,也有慢慢等待中“悔教夫婿觅封候”的幽怨,但仍幻想着有朝一日夫君功成名就后能过上“夫贵妻荣”的生活,由此而上演了无数出或悲或喜的人生悲喜剧。
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男性意识依然占领着女性世界。鲁迅是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这样一位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伟人,同样存在着男性特有的意识。鲁迅有过两次婚姻的经历,一次是1906年,鲁迅奉母命从日本回国和一位极传统的女性朱安完婚。鲁迅曾对许寿裳谈起过这次婚姻:“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6]所以婚后仅四天就返回东京了。此后朱安一直在尽心尽力地侍奉着他的母亲,在痛苦的期待着鲁迅的到来,耗费着自己的青春。鲁迅为了母亲“有个人陪伴”,竟然牺牲了朱安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幸福,这在人性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何等的残忍。另一次是1925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许广平的相爱。许广平是29岁的新女性,立即提出了和鲁迅公开同居的计划,却被鲁迅“分头苦干两年,挣足可维持半年生活的积聚”为由拒绝了。事实上,他两次婚姻最终都是唯自己的意识为上。对朱安的冷酷。对许广平的推诿,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鲁迅观念中的男性意识。
进入新时期,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一些女性逐渐从男性意识中挣脱出来,她们走上了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岗位,发挥着她们的光和热。最近焦作电视台新增了个栏目《天南地北焦作人》,其中也不乏成功的女性,她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她们有较强的女性独立意识,但是我们必须充分地看到太多的女性还不同程度的被男性意识困扰着,“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化观念和思维模式还没有彻底改变。职业女性一面要承受工作的压力和辛苦,同时还要承担维持家庭的重担。家庭妇在生活上完全依靠丈夫,她们因没有经济来源而更加小心翼翼的侍奉着自己的丈夫。因此,作为女性在事业上就很难与男性比翼双飞,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
几千年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是不能一下子改变的,它还在继续吞噬着现代中国人的意识,于是女性还在为男性作着牺牲。丈夫上班,妻子就得准备饭菜:丈夫出差,妻子就得准备“行头”:过年过节,最忙得是妻子,就连妻子过生日,恐怕还得自己准备生日宴。俗话说,“成功男人的背后站着一个女人”,“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话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是颂扬!是赞美!可这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女性的悲哀。《中国式离婚》正是抓住了现代中国人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心态,从现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塑造切入,揭示了现代女性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和追求,但她们又把这种希望寄托在终日厮守的男性身上,正如编剧王海瓴所说,本剧主要写的是一种心态,因为现在社会上多数女性心态还是妻子将家庭的前途寄托在丈夫身上,为此女性甘愿为家庭为丈夫牺牲,甚至失去自我。这种女性特有的“夫贵妻荣”的心理期待,始终困扰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了男性意识的滋生和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