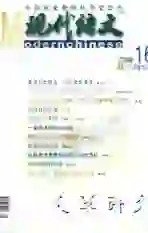用爱拯救孤独
2006-09-21焦晓燕
埃里希·弗洛姆(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集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于一身。他潜心于弗洛伊德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禅宗思想,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把心理分析与社会学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研究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各个具体问题,并引入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思想,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新精神分析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尤其在他的《爱的艺术》、《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等著作中关于爱的一系列理论论述,打破了传统关于爱的观念,认为爱不是无师自通的情感,而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一种能力和艺术。弗洛姆从全新的角度对爱的根源、性质、目的、作用、组成要素和各种表现形式以及爱的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给人们新的启迪,对我们深刻分析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很有启发性。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是围绕着自己设定的一个中心目标展开的,即奠定一种“人道主义伦理学”,纠正被扭曲了的人性和拯救被异化了的社会,促成一个“健全的社会”。而关于爱的理论则是这一中心目标的核心内容。在他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和所谓的健全社会中,爱占有中心的位置,成为他解决人和人类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基点。正如他所言,“任何爱的理论都必须以一种关于人和人类存在的理论为起点”,“爱——对人类存在问题的解答”。[1](P236)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应在爱的普照下和谐健康的发展。这是弗洛姆千转百回于扭曲人性和异化社会问题之后提出的最终理想愿望。
那人类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人类存在的问题包括哪些内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人类生存空间和时间的拓展和延续,人类存在的问题处于一种消长的状态中:旧问题或解决或待解决,新问题不断出现。现世我们人类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这是人类无法逃避也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它已经内化为我们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并致力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奔波只是为了问题的完满。在这里,弗洛姆主要强调的是人类的分离。人降生在这个不确定的、易变的和开放的世界中,当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存在的生物,也就意味着,“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分离的实体,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促;他意识到自己生不由己,死亦不由己。他意识到他将先于他所爱的人死去,或者他所爱的人死在他的前面;他意识到自己只身一人,孤苦伶仃,在自然和社会的压力面前无依无靠,这一切使得这种分离不和的存在对他来说成为一个不堪忍受的牢狱。”[1](P237)人类最深切的需要,就是要克服这种牢狱,摆脱这种分离。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与国家中,人们都面临这一问题,即“怎样克服分离,怎样实现结合,怎样超越个人的自身生活,并找回和谐。”[1](P238)弗洛姆认为只有爱,只有爱才能使我们在不断分离与求和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中得到安慰,树立信仰,增加自信。反之,没有爱的重新结合,人类分离的意识,就成为羞耻心的根源,同时也是负罪和焦虑的根源。弗洛姆讲道,人类最根本的生存的两歧包括:第一,生与死的矛盾;第二,人的长远想象和人的短暂生命的矛盾;第三,意识到孤独和必须与他人联系的矛盾。这就是说,人类的孤独感无法彻底消除。它是人类生存的必然伴随物。正如他自己所说:“实现这一目的的绝对失败意味着理性的丧失,因为,只有通过这样一种从外部世界的根本回撤,已是分离干净时——因为这个使人分离的外部世界似乎已经消失了——才能克服这种令人恐慌的完全孤独的状态。”[1](P238)这意味着什么呢?死亡!严重的精神失常!甚至不能思维(例如植物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不知道自己与周遭一切事物的关系。只有生理需求,而丧失精神追求的行尸走肉般的人才能做到从外部世界的根本撤回。正常人都有孤独感,都有消解孤独的渴望。弗洛姆就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人类做了分析。他认为,对于婴儿,刚开始他感到与母亲是一体的。只要母亲在场,他便不会有分离感。他的孤独感为母亲的身体、乳房和皮肤的在场所弥补。随着婴儿自我意识的增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母亲的身体在场不足以治愈他的孤独感。此时,新的孤独感产生,新的克服方式也随之产生。人类也是一样。在幼年时期,仍然感到他和自然是合一的,自己与动物是相同一的。随着人类思维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他开始意识到自身与外界的分离,开始寻求和谐。新途径也就应运而生。人永远在对消除孤寂的渴望中艰难悲苦的前行。弗洛姆提出四种克服分离与孤独的方式:第一种是各种各样的狂欢状况。例如酗酒、吸毒以及在迪厅的狂舞等等。在暂时的狂欢中麻痹自我忘却现实。这种靠麻痹精神的方式,只能是短暂的虚假的自欺欺人的逃避孤独与恐惧。亢奋的背后是无力,癫狂的背后是哭泣。狂欢过后是更加的寂寞难耐,脆弱的心灵只有再次寻找狂欢,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对狂欢活动产生了依赖,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发展。第二种是西方社会里普遍采用的方式,与群众的融合。这是一种对于权威,对于大众的遵从,也是一种更能迷惑人的方式。表面上一片欣欣向荣,充满祥和,其实却是不自觉的自我教化,个性泯灭,自我迷失。人们丢弃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原则,且往往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采用了这种方式,而事后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弗洛姆说的经典:“人们想要遵从的程度远远高于他们被迫遵从的程度。”[1](P241)第三种方式是创造性活动,即生产性工作。他在此强调的是程式化、机械化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人成为了机器和机构的附属物,成为机械化的符号。“在生产性工作中所实现的联合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在狂欢的聚合中所实现的联合是短暂的联合;凭借一致所实现的联合仅仅是虚假的联合。因此,它们都只是对存在问题的片面回答。”[1](P244)
在否定上述三种方式的同时,弗洛姆提出了最佳方式,即爱。他说:“全面的答案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融合,在于实现与另一个人的溶合,在于爱。”“没有爱,人类不能存在一天。”[1](P244)但并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克服孤独与分离的感觉。例如共生性融合,包括消极形式和积极形式。其消极形式表现为“受虐狂”,即通过使自己成为别人的一部分,依靠别人,来躲避不堪忍受的孤独。他处于一种屈从的生活状态,没有独立性和完整性。其积极形式是“统治”,表现为“施虐狂”,即通过使另一个人成为自己的重要部分,而逃脱自己的独处和监禁感。“他通过使另一个崇拜他的人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的方式来抬高和强化自己。”[1](P246)这种共生性的融合,是一种伪装的爱,让我们看到的是个别人龌龊的内心和灵魂。例如《巴黎圣母院》中的教父,他对伽西莫多的爱(如果算是一种爱的话,这种爱也是一种隐性的统治。)就是一种共生性的融合关系。他利用自己对伽西莫多的恩情和伽西莫多的善良来实施他罪恶的欲望。我们不禁要问他起初对丑陋的伽西莫多的关爱还包含有真心的成分么?一切似乎已经演化为他实施罪恶行径的借口。我们看到的是教父伪善的嘴脸和丑恶的内心,而伽西莫多在他的长期“仁慈的善待”下,没有意识到这一伪善,或者是不想承认教父丑恶内心与阴险手段的事实。到后来,在爱斯美拉达爱的滋润与熏陶下,才认识到真正的教父。伽西莫多将爱斯美拉达传递的爱的内涵付诸行动与教父共生性统治的爱作反抗。这里爱斯美拉达传达给我们的爱就是弗洛姆后面讲到的与共生性融合形成对照的成熟的爱。“它是在保存人的完整性、人的个性条件下的融合。”[1](P246-247)这种爱是人的一种主动能力,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弗洛姆在此强调这种爱是与罗曼蒂克的爱不一样的。他说:“如果对某个人的爱导致了对他人之爱的转移,那么这也不是真正的爱。只能为一个人所体验的爱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共生联系。”[2](P129)同时弗洛姆强调这种成熟的爱,是一种生产性的爱。“爱是人与他人、及与自己之间关系的生产性形式。它包含着责任、关心、尊重和认识,包含着他人成长和发展的愿望。它表现了两个人在互相保护完整性条件下的亲密关系。”[2](P114)爱不是占有,不是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安嘉和对梅湘南暴力的爱。“以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所体验到的爱则是对‘爱的对象的限制、束缚和控制。这种爱情只会扼杀和窒息人以及使人变得麻木,它只会毁灭而不是促进人的生命力。”[3](P50-51)安嘉和把妻子梅湘南当成自己的私有物,嫉恨一切与之接触的男性,也不能容许妻子与任何男性接触,并对他们进行恐吓与报复,致使他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一种爱么?爱不是毁灭。爱是人类生命的另一种延续。它的对象可以是这个世界的种种,可以触发、唤起和增强我们的生命力的一切事物。“真正的爱植根于生产性之中。”[2](P108)人类就是在这种生产性的爱中消解孤独的困惑。
孤独在人类生活中的必然性存在,成为爱产生的根源。爱又消解了人类的孤独与分离感。正如弗洛姆在《为自己的人》中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的存在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特征的,即人是孤独的,它与世界是分离的;人无法忍受这种分离,他被迫寻找与他人的关系,并与他人结为一体。人实现这种需要的方法很多,但只有一种方法才能使他保持其为一个唯一的实体而不变;只有一种方法才能使人与他人相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人之存在的矛盾是,他既要寻求与他人的接近,又要寻求独立;既要寻求与他人结为一体,同时又要设法维护他的唯一性和特殊性。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只有生产性才能对这一矛盾及人的道德问题作出回答。”[2](P102-103)弗洛姆的这种观点对我们现代人和当下的社会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现代人更加宣扬自己的个性,狂热追求所谓的个性与时尚,当然并不全然是坏事,但是我们秀出自己的个性了么,穿出自己的时尚了么?所谓的个性也不过是一种趋同,所谓的时尚也不过是同一种色调。我们现代人走入了一个误区,渴望用这种个性的趋同、时尚的媚俗消除自己内心与周遭世界的分离感。我们害怕被这个世界抛弃,被周围的亲朋好友遗忘,我们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引起他人的注意,证明自己的存在,并没有与大家落下距离。可能更多的人错解了个性与时尚。每个人都有对孤寂和恐惧的本能抗拒。什么能够消除?也只有爱。听起来似乎很遥远,很是奢望。的确,用爱拯救我们的孤独似乎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遥想,但是乌托邦的才是我们真正的渴望。多一份爱总比少一份好。爱的宽容总比冷漠好。
注释:
[1]引自《为自己的人》后附录的《爱的艺术》,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2]《为自己的人》,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三联书店 ,1988年版。
[3]《占有还是存在》,弗罗姆著,关山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焦晓燕,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