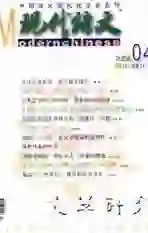永恒的鸣凤
2006-03-03鹿月华
《家》是巴金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小说通过描写一个正在崩溃的封建大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猛烈抨击了封建统治势力的罪恶,塑造了一批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整部作品情节曲折、人物众多,而在纷繁复杂的人物中,我最欣赏的是鸣凤这一形象。
鸣凤这一形象在作品中所占篇幅并不多,但她却是一个极具个性与震撼力的人物,在历经人生种种悲苦不幸的际遇后,她以死向命运抗争,加之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使这一形象更具永恒性,而这种永恒性正是通过其投湖的瞬间得到充分体现的,故而可以说:鸣凤在投湖的瞬间便铸就了其永恒的形象。
一、鸣凤的死可以看作是其人生的飞跃,而这种飞跃是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的。
1.生的无奈——身世的可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却难以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鸣凤出生在封建社会一个贫苦的家庭,自幼丧母,又被卖到高公馆当婢女,一干就是七年,其间吃了不少苦头,在她脑子里只有一种很简单的信仰,那便是:“命啊,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她认为命运的安排是无法抗拒的,她只有忍受。十六岁,花季般的年龄,她也有许多天真美好的幻想:“假使我的命跟小姐们的命一样多好!”“她也曾梦想过精美的玩具、华丽的衣服,美味的饮食和温暖的被窝。像她所服侍的小姐们享受的那样。”然而梦毕竟是梦,一切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冰冷的现实一次次击碎她的梦想。她的出身也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她是没有地位可言的,她只会是受剥削、受压迫的对象,而且她的一生也只会是一场悲剧。
2.生的无助——人生两大希望的幻灭。生活中没有希望就如同没有阳光。鸣风的生活是有希望的。从她进入高公馆以来,在吃苦受累挨骂之余,能给她一丝慰藉与欣喜的便是大小姐。她说:“我一辈子就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妈,一个是大小姐,她教我读书写字,又教我明白许多事情,她常常照应我……”对于大小姐的照应,她是感恩不尽的。也许是缘于她的善良和纯朴,当她受到别人哪怕是一点微薄的爱,她都会铭记于心并渴望用尽自己所有的爱去回报。然而不久大小姐的去世就带走了她人生的第一大希望。随着时问的推移,她又有了人生的第二大希望——觉慧。觉慧是鸣风短暂生命中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与鸣风之间的爱情是纯真而稚气的。作者把他们的爱情关系同他们对各自命运的挣扎结合在一起描写,使读者从关心人物命运的高度去关注他们的爱情生活,从而深化了主题。他们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其性格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鸣风十分清楚自己与觉慧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她并不奢望与觉慧平等地生活在一起,而只希望能陪伴在他身边,一辈子在公馆服侍他,做他的丫头。她对觉慧说:“你不晓得我多尊敬你!……有时候你真像天上的月亮……我晓得我的手是挨不到的。只要一生一世在你身边就满意了。”鸣风把觉慧看作生活的最大希望,并把那份纯洁真挚的爱情当作精神支柱。鸣凤对觉慧的爱是无私的,她的爱在含蓄中显露直白,在细微中带着执著。她甘心情愿为爱付出一切,虽然这个世界对她有太多的不公平,但只要能拥有觉慧的爱,她就已经感到万分地满足了,因为她爱觉慧胜过一切。然而生活对待弱者总是太残酷,当她得知高家要把她送给冯乐山做姨太太时,“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人们甚至连她所赖以生活的爱情也要给她夺去了……那一线纯洁的爱情所带来的光明也给人家摧残了”。在孤苦无援的境地中,她记起了觉慧的“誓言”,企望觉慧做她的“救星”。当鸣凤带着最后一线希望来找觉慧,并渴望由此改变命运时,一切好似没有开始便结束了一般。觉慧对鸣风的事还被蒙在鼓里,几天来他只顾忙着自己的事而忽略了鸣风,当他发现鸣风满眼忧郁的神情时,他便用温和的笑和暖心的话安慰鸣风,并承诺“再过两天就好了”。之后,“他一阵感情冲动,连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他忽然捧住她的脸,轻轻地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又对她笑了笑”。或许这一吻蓄含的力量太大,让地位卑微的鸣凤无法承受,此刻,她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觉慧对她的爱。“她终于得到了安慰,得到了纯洁男性的爱,找到了她崇拜的英雄,她满足了。”她是一个极易满足的人,尽管觉慧没有救她,她知道,即便觉慧救她,也不见得救得了她,所以她不愿让心爱的人因为她的事而苦恼,她只愿自己为这份美好纯洁的爱情去付出。事实上,也正是这份爱让鸣风有了勇气和力量去选择抗争的路,更加坦然地面对死亡。她的死如同她的生都是孤寂无助的。
鸣凤的一生是“无奈”和“无助”交织的一生,正是在这样凄苦的人生中,鸣凤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悲凉。她知道,在那个时代,像她那样的人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她已忍受了十六年,十六年中命运剥夺了她的自由,泯灭了她的希望,甚至连爱的权力也不给她。正是在人生苦难的积累下,她认识到自己是无法获得幸福的,所以当不幸再次降临时,她为自己选择了道路,在湖中找到了归宿,一方面求得自我的解脱,另一方面也完成了人生的飞跃。
二、鸣风的死完成了其人生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1.飞跃的内涵。关于鸣凤这一形象的塑造,作者说:“我写鸣凤,我心里充满同情和悲愤。”作者一方面同情她一生的遭遇,一方面对社会迫害青年而感到愤恨。鸣凤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而且有美好的心灵,在她身上秉承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诸多优点,她勤劳善良、温柔贤淑、知事明理、讨人喜欢、让人怜爱。然而,在生活的逼迫下,“这张美丽的脸上总是带着那样的表情:顺受的、毫不抱怨的、毫不诉苦的。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连一点吼声也没有”。这便是她性格中逆来顺受的一面。我觉得恰恰是这一点使鸣凤这一形象更为真实,她没有脱离时代的局限,是时代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鸣凤是真善美的化身,由此我们不免对这一形象产生同情、喜爱之情。其实鸣风的形象魅力绝不仅仅在于此:她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觉慧相爱,又不甘心命运的摆布而走上了绝路。“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励我的源泉。”作者是肯定和赞美青春的,然而作者却将鸣凤的青春及生命置于毁灭的境地,正是这种毁灭给读者心灵带来了震撼,除了对她年轻的生命抱有惋惜之情,我想多数人还会从内心生出一些敬意来:一是为她敢于恋爱的勇气,二是为她敢于抗争的精神。事实上,这也体现了鸣凤的人生价值。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鸣风的一生是一场悲剧,它的意义在于不仅给人以警醒,更重要的是能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深层思考。
2.飞跃的外延。鸣凤是美的化身,而她最终却遭到毁灭,这不仅让人发问:是什么导致了美的毁灭?是爱情希望的破灭,是冯乐山的荒淫,还是高家的威逼?我想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她生活在封建社会那个大环境中,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已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高家成为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些封建余孽们从肉体上摧残年轻一代,从思想上腐蚀新生的一代。高家这只怪兽吞噬了多少
年轻而可爱的生命,像梅芬、瑞珏、鸣风、婉儿等都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及家族利益,是一堵横亘在青年幸福之门的巨型黑墙,是一张撒向青年自由天地的险恶罗网,是套在青年身上的沉重枷锁。在这如磐的黑暗里觉慧与鸣凤相爱,无异于带着脚镣跳舞。高老太爷不只是一个垂死的老头子,而且是封建家长制、宗法制的集中代表,是这个黑暗制度在高家的代理人。因此,当鸣凤被迫嫁给冯乐山时,太太周氏无力相救,觉民只能叹惜,觉慧也只能空白呐喊。这就注定了鸣凤只能在以泪洗面、在痛苦自熬之后,孤寂地走向死亡。整部作品正是通过鸣凤这一类受害者形象来触及社会,进而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深层思考。鸣风人生飞跃的完成,更有力地反映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当然作者刻画这些形象,目的是唤醒广大青年,不要再甘愿做受害者,应该像觉慧、琴那样去抗争,去争取幸福和自由,没有反抗,就没有出路;只有反抗,才会有新生。
三、鸣凤的人生飞跃诠释了其形象的“永恒性”。
鸣凤死前最后一句话是“三少爷,觉慧”,可见觉慧在她心中地位是何等重要,她全身心地投入而无私地爱着觉慧,即便到死也没有丝毫的改变。对于觉慧没有解救她,甚至一点帮助也没给她,她都没有任何怨言。她害怕的不是以后要忍受的无终局的苦刑,而是亵渎她美好的感情,剥夺她爱的权利;她害怕的也不是失去生命,而是失去那份至高无上的爱。所以最终她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爱情,这便是鸣凤形象“永恒性”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则表现在她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即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形象,在她身上有封建性的特点:脑子受到封建思想浸染,认为命运的安排无法改变,对苦难与不幸逆来顺受。但她又有与之不同的一面:她敢于和觉慧相爱,这种勇于释放感情且敢爱敢恨的精神,与梅芬和觉新的软弱且拼命压抑感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当残酷的现实击碎她生活的希望,夺取她爱的自由时,她以死来抗争,最终摆脱了“孔教会”遗老冯乐山要把她变作玩物的凌辱。她死后,高家又把婉儿作为替代品送给了冯乐山,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成为了垂死的封建势力的祭品。由此看来,同样是死,鸣凤死的价值要比梅芬、瑞珏等高得多。事实上,鸣凤临死前的内心独白也反映出她已开始思考人生悲剧产生的原因“难道这一点她也没有权利享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还活着,她在这样年轻的年纪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我的生存就是这样的孤寂吗?”虽然她没能够找到答案,但我们却能真切地感受到她已经不是那个柔弱的、逆来顺受的小姑娘了,她已经有了觉醒的意识,在她身上已经能够看到反抗并勇于主宰命运的希望了。
综上所述,鸣风是封建社会中最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她的一生短暂、凄凉而又悲苦,同时她也是一个矛盾的个体,因为在她身上有着封建性的一面,也有敢于反封建的一面。自戕是消极的,但在没有别的反抗道路的时候,比起受蹂躏、受凌辱却要壮烈、崇高、有力得多。这种行动本身虽不能给予统治者以打击,却是一种示威,一种抗议,一种警告,说明奴隶并不都是可以随意摆布的:对受迫害者来说,是一种警钟,一种催促,一种鼓舞,说明并不是只有屈从才是出路。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矛盾个体却在投湖的瞬间完成了人生的飞跃,这种“飞跃”更为清晰地展示出她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对命运的抗争,这些都有力地诠释了其形象的“永恒性”。
(鹿月华,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