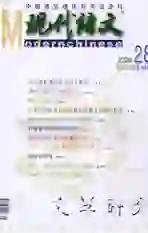林海音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2006-01-30关园园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是台湾第一位女作家,也是台湾文学中女性意识最早的呼唤者和奠基者。”(《台湾地区文学透视》,古继堂,黎湘萍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林海音的小说,不管是以北京为背景还是以台湾为背景,几乎全都是以女人、婚姻、家庭为中心,叙写了女性的种种不幸和悲哀、忧愁和痛苦、忍受和反抗;通过她们的悲剧命运,揭示出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性人生的强制性规定和深深的戕害,表达了中国妇女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呼声和愿望,并隐含了这样一个典型命题:女性自我意识、自我价值追求在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女性解放的艰巨性、长期性。
林海音总是以饱含深情的笔墨,生动细致地描绘出不同时代里,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女性的婚姻和命运。根据各自不同的性格、命运,可以将她们做如下的分类:
1.封建道德伦理统治社会,男人处于强势地位,被压抑、被摧残的女性。
这里既有处于社会低层的普通劳动妇女,也有一般的知识阶层女性,还有处于中上层家族中的太太、姨太太等上层女性。这是一群处于现实和传统夹缝之中的旧式妇女。她们不论贫富贵贱、文化高低,都遭受了被压抑的命运,在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林海音在小说中从不同角度为这些女性的不幸命运哭泣和悲叹,深刻地揭示出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和不公。
《城南旧事·惠安馆》中的疯女人秀贞,曾经是个活泼可爱的女性,她把自己对爱人和孩子的爱当成她生命的全部寄托。然而,在爱人一去不复返、刚生下的女儿又被父母扔到城外的双重打击下,精神失常发了疯。但她的爱是如此之深切,竟使她仍然固执地做着准备,要去寻找他们,最后却惨死在火车轮下。在这里,林海音把秀贞的爱表现得十分充分,但这却在深层次上向读者揭示了秀贞的多重悲剧性命运:追求美好爱情与幸福生活而不得的悲剧;亲生女儿被抛弃、欲做母亲而不能的悲剧;思想行为不能为父母、社会所理解、所容纳而遭受压抑的悲剧;等等。作者正是通过秀贞这个“最具体的个人”的凄惨命运,深刻揭露了封建道德传统对女性无情的摧残和扼杀。
从《婚姻的故事》中的那个女画家怡姐的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个对自己的婚姻毫无把握,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女性形象。所不同的是,林海音着重从怡姐的女性心态和精神入手,更多地揭示了女性对待自己命运的麻木和不觉悟。怡姐“很早就死去了丈夫,没有子女”,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她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舍己精神”,为了使那个身患严重肺病的男人好起来,顺从了旧式的冲喜婚姻的迷信。结果结婚才一个月,丈夫就死了,最后一生孤独。
怡姐是痛苦的,她的痛苦是“失去了丈夫”的痛苦,却不是认为“那种冲喜的迷信婚姻方式害了她”的痛苦。作品中提到这么一个小细节:怡姐同小叔子家的关系可谓不错,在小叔的孩子们中,“她最喜欢龙龙,因为龙龙长得像小叔一样”。由此不难看出,他对小叔不是没有一点好感的,由此“爱屋及乌”也是情有可缘的。但是,小叔“守旧礼”奉承她,而她自己也是个“被扔在旧时代里没逃出来的人”,教她新,她“也新不起来”。她有对爱的欲求,却只能把这种渴望深深埋藏在心底,只能靠着回忆那不着实际的一月新娘,作为她一生甜蜜而又痛苦的生活。女性遭受制度压迫的命运是悲惨的,但是受压抑而不自觉更是悲哀的。在怡姐身上,我们感觉不到她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自主意识。在争取爱情自由、个人幸福方面,她没有任何主动的表现,我们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强烈地产生了“怒其不争”的怨愤。作为经济独立的知识女性,竟然向荒诞无稽的迷信婚姻妥协,连一点自我解放的意识都没有!对命运的顺从,构成了她枯寂无味的人生。她没有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力量,摆脱不了紧紧束缚她的传统礼教,因此只能在困惑、迷惘中感受将要被时代抛弃的凄凉和恐惧。这是一个在新旧文明夹缝中找不到出路的迷途的羔羊。她的命运提醒人们,女性要摆脱封建传统束缚,争取独立自主的命运是何其艰难。
在描写被压抑、被迫害的女性时,林海音从不同的侧面下手,向封建制度开刀,其中之一就是沉痛地控诉封建婚姻的纳妾制度。“纳妾制度不仅是抽在小妾身上的鞭子,也是捅入大妇心窝的刀子。”被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称为“题材可怕”的《烛》、《金鲤鱼的百裥裙》等作品中都描写了这类女性撕裂人心的故事。这两篇作品分别从正室和小妾两方面入手,重重地抨击了“一夫多妻制”给妇女带来的灾难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大妇的痛苦,主要是精神的,内在的。在某种情况下,她的内在的痛苦还可以用外在的优越感和强势进行一些抚慰和弥补。而没有正当名分,地位低下,倍受歧视和虐待的小妾,命运比大妇更加悲惨。内在和外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和不幸,双管齐下地对她进行撕咬和绞杀。即使生命完结了,精神和灵魂也不能获得解脱和超越。”(《台湾地区文学透视》,古继堂,黎湘萍等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居于统治地位,男人占本位的家庭世界中,女性只能是边缘人的角色、她们必须服从别人,而且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和迫害。胡适就曾指出:“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棒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贞操问题》,《胡适文存》(1),黄山书社1996年版)
2.身陷困境,却勇于同制度奋力做反抗和斗争,相对自主、独立,把握了自己命运的女性。
几千年的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女性没有任何地位,她们一生都从属于男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且,“在经济上,女人寄食于人者,从谁便寄食于谁,在心理上,女人从谁便屈服于谁,这便从经济与人格两方面排除了女性对任何生产资料或生产力的占有权。”(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上海文论》1989年第二期)要想摆脱不幸的命运,就必须同这种状况做勇敢的斗争。于是,林海音在塑造了被摧残而委曲求全的“女奴隶”形象的同时,还在作品中安排了不甘任人摆布的反叛的女性形象。她们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却具有反抗的意识,勇于同压制自己的封建势力做斗争,希望获得人格、人权和人性的自主。
《城南旧事·兰姨娘》中的兰姨娘是封建社会孕育出来的一个“畸形人”。二十五年的生活对她来说充满了侮辱与损害,迫使她不得不逃离那罪恶的家庭。后来,当她与德先叔真诚相爱,并受到他的启蒙与影响明确了自己的追求时,她立即变成了另一个人,与流里流气的旧日相比,她实现了脱胎换骨。兰姨娘确实同自己的悲苦命运作了反抗,而且也算是一位“很有志气的敢向恶劣环境反抗的女性!”在她最终的选择里,我们可以看到她的未来,虽然她还不是一个各方面都已经完全独立自主的女性,但她的选择已使她跨入了现代女性的行列。
女性在人的解放、个性解放的过程中,首先要争取的就是爱情的胜利。《婚姻的故事》中描写三嫂的文字并不多,而且自始至终没有让她正面出场,没有让她开口说一句话。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叛逆性格的塑造。她对那种冲喜式的迷信婚姻是怀着叛逆的精神而采取了实际行动。虽然同三哥的悲剧婚姻对她未尝不是一场抹不掉的伤痕,但她最终还是实现了与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作者并未交代三嫂重新开始的生活状况,但与那位仅靠回忆过着甜蜜而又痛苦生活的怡姐相比,肯定是决然不同的。
理想的爱情,幸福的家庭是新女性追求的目标,但生命的全部意义是否仅止于此呢?除了爱,女性是否还可以有其它的追求呢?《婚姻的故事》中的芳这一形象的塑造就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这里,林海音对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分析和灵魂探索,塑造出另一个“以实际的行动对她的命运叛逆”的女性形象。芳生活在一个愁闷的家庭里,这一家人,除了她自己和大的两个孩子以外,仿佛都是不健康的;这一家人太爱护她了,反而使她痛苦起来。许多的愁闷和压抑引起了她强烈的“反感”、“嫌恶”和“叛逆”的心情,于是在她的反抗的潜意识中,便与健康、精力充沛的沈先生接近、而成为相携出入的一对了。这在深层上包含着一个女性除妻子身份以外的另外一种权利——她仍然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感情天地和人格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揭示了人的感情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种丰富性和多元性是客观存在的,也同样是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体现。这从芳的举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丈夫死后,她不愿为丈夫穿孝,因为她不愿自己是个“寡妇相”,“使得别人以不同的眼光注视着她”。作为无助的女人,以这种方式来反抗她所不愿承受的命运,就冲破了社会的某种禁忌,真是可悲可叹可敬的遭遇。作者因此指出,女性要想寻求自身的解放,获得人格、人权、人性的真正自主,就不能哀求,更不能寄奢望而向压制势力屈服和妥协。而是应该自己站起来,实现自身观念的更新嬗变。从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角度看,芳较其他女性更进一步的地方在于:当别的女性还在为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努力奋斗的时候,她已经触及到了更深一层的问题——女性自我价值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
3.由于不被尊重而“堕落”的女性。
同古时的优伶一样,现代歌女也是毫无社会地位可言的。在畸形发展的社会中,她们的悲苦命运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无论如何挣扎和反抗,都不可能摆脱受人凌辱的境遇。《孟珠的旅程》中歌女雪子的遭遇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变态的歧视。雪子遭受的是精神与人格的双重摧残和虐待。种种的不被尊重,使她产生了变态的心理:她疯狂地在男人身上报复,反倒害了自己;她玩世不恭,却有自己的思想。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一块烂泥”,只能被人扔掉;所以,一旦有人想要从泥淖里拉她一把的时候,她却没有了勇气。她的沉沦更具有悲剧性:她的自尊心驱使她不甘被人摆布玩弄而去玩弄男人,但内心的自卑感又让她深深自责自暴自弃。她倔强地和环境搏斗,但大胆和勇敢的背后,却充溢着懦弱,她斗不过周围的环境,于是倒下了。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一个将雪子从深渊中救赎的机会,最终却没有使其超脱,目的在于使用“最残忍的手段”渲染雪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改变命运的悲苦。这就显示出了人性的复杂,也反衬了台湾社会的黑暗,并使读者通过雪子这一人物形象,加深了对促成她悲剧的社会环境的认识。
其实,身陷困境而不能自拔的又何止雪子一人?在雪子生前唱歌的“曼声厅”里不就有一群同雪子一样的歌女吗?她们为了生活、为了家庭而奔命于歌台,以她们与身俱来的声色资本获得这个职业而谋生赚钱。可悲的是,她们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都是不被尊重、受人歧视、受人捉弄的对象。表面上她们过得那么热闹,实际上却是最寂寞、最无依无靠的人,她们的生活背景,都是残酷而无望的。如果说雪子为了超脱精神与人格的炼狱而最终选择轻生的方式是不明智的,那么这些歌女应该采取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自歌场引退,另外寻找新生,但是生活呢?矛盾的症结就在这儿。她们之所以充满悲哀,问题也在这儿!作为歌女,她们的命运只能是这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因此她们只能在无奈和心酸中认命,而作者似乎也未能指出一条真正解决问题的出路。
4.理想化女性的闪现。
林海音的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形象都是卑微、渺小、柔细、贫弱的,基本上都一度处于被遗弃、被玩弄、被侮辱、被怜悯、被牺牲、被施舍的境地。但林海音同样塑造了具有自立、自强、自主意识的女性,这类形象虽然不多,却在失落与无望中给人以希望,属于理想化的时代新女性。《婚姻的故事》中的“我”不就是如此吗?“我”是以故事叙述人的角色介入作品的,但又不仅仅拘囿于此。作者在让“我”叙述其他女性命运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将“我”的生活片段也零星而又恰倒好处地穿插进去,或过度,或衔接,或对比,借“我”的口阐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倾向。仿佛是不经意而为之,实则展示了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娴熟的写作技巧和不凡的艺术造诣,同时在主题的表现上也达到了烘云托月的效果,由此而在众多的女性当中树立起一个理想型女性的典范。值得注意的是,林海音在注重形象理想化的同时,并没有一味地显新避旧,而是让“我”生活在一个新与旧“颉颃互竟”的大环境中,在新与旧交融并存、激烈斗争的氛围中,点点滴滴地塑造“我”的个性:“我”从小就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动性,并且没有受到过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直接压抑,成人后又有独立的经济支配权,整个环境对“我”而言是比较宽松和自由的。“我”的生活环境似乎是依“我”的思想性格特征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我”确实是一个已经真正独立自主、拥有人权的女人了!在“我”的面前,显示出的是家族的渐渐衰败与散落,旧制度的无力与妥协,“我”始终是自己命运的主动者与支配者。所以说,这个形象的出现,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既是真实的,又是理想的。
女性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从因袭封建传统的旧式女子(如怡姐)到半新半旧的过渡型女子(如兰姨娘),再到赢得婚姻自主的新女性(如“我”),林海音笔下的女性用各自的声音,诉说着女性的情绪、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各种生存体验,揭示了中国妇女由女性→人→女人将要经历的艰难历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至今仍在继续、发展的过程。
读过林海音的小说的人都不难发现,作品中的女性原本都是善良而美好的,本质上都是质朴的(可以说没有出现一个俗不可耐、无事生非的灰色形象)。但作者将她们置于特定的时代与命运中,使文本呈现出来的形象的性格特征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发生了“变异”,她们或者精神失常,或者忍辱求全,或者沉沦变态,或者勇敢反抗,这就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女性如果没有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没有主体意识的充分觉醒和成熟,没有精神上的真正解放,即使有了物质、经济保障,都还不能得到真正的、完全的解放。
另外,林海音在作品中反复述说着女性的或顺从或反抗或畸形变态的命运,却没有将人物形象类型化、格式化,而是一人一面,各有自己的个性。同是抨击“一夫多妻制”的罪恶,《烛》和《金鲤鱼的百裥裙》选取的却是两个针锋相对的视角,呈现出的也是正室和小妾两种同样具有悲剧命运的形象的代表;同是控诉封建冲喜婚姻制度,怡姐和三嫂却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当然相去甚远;同是表现被迫害者的沉沦和变态,雪子和琼(《婚姻的故事》)的遭际亦各不相同:前者被爱人抛弃后,一次又一次地以报复的手段,玩弄爱情于掌上;而后者在抛弃第一个“丈夫”后,一次又一次地被别的男人抛弃,被他们玩弄于掌上。通过各种手法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栩栩如生,性格特征复杂多变,林海音运用写作技巧、驾驭材料的娴熟程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她笔下的女性才能以各自不同的生动性、真实性、复杂性和感染力立体地跃然纸上,以整体的力量感染着千千万万的读者。
(关园园,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