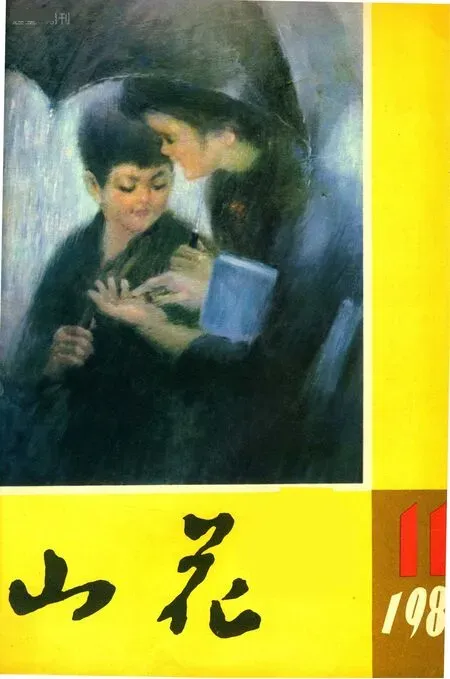把短篇小说的写作进行到底
2005-04-29王祥夫段崇轩
王祥夫 段崇轩
鲁迅文学奖与当前的短篇小说创作
段崇轩(以下简称段):祥夫,你的短篇小说《上边》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而且名列榜首,作为老朋友,我很为你高兴,真诚地表示祝贺!鲁迅文学奖是国家级大奖,代表了—个国家文学创作的水准。它是从1995年开始起评的,至今已有10年时间。就短篇小说讲,第一届(1995——1996)获奖作品有6篇,第二届(1997——2000)获奖作品有5篇,第三届(2001——2003)据说参评作品多达189篇,而获奖作品只有4篇。前后共9年时间评出15篇作品,一年平均不到2篇作品,真是沙里淘金呀!这也说明鲁迅文学奖是极为严肃的。但是,如此严肃、严格、认真的评奖,在读者、文坛、媒体中却不大买账,反映平平,而且这种“冷漠”似乎一届比一届更甚。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曾经风光无限的短篇小说究竟怎么了?是读者、作家、评论家的审美趣味出了问题?还是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真的衰落了?亦或致力于短篇小说的作家创作上滑入了“误区”?第三届的4个获奖短篇和一部分人围作品我都读过了,我觉得绝大部分确实不错呀,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比起新时期文学的短篇小说并不逊色。这些作品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它们有了一种开阔、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艺术表现上也显得很纯熟、很自然。特别是你的《上边》,这种艺术特色表现得更明显。但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得不到更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同呢?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王祥夫(以下简称王):阅读与欣赏从来也都是呈宝塔状的,你不能期待短篇小说会有更多的读者,如果短篇小说的读者要比金庸琼瑶的情爱武侠小说的读者还要多那就是怪事。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一般会有两种考虑,一是没动笔之前考虑的是这篇小说会有多少读者,另一种考虑是这篇小说应该写到什么高度,我可能属于后一种,写作的时候很少考虑到作品会有多少读者这个问题。但我会考虑我的小说的读者群体应该是哪些人。就艺术这个层面讲,现在的短篇小说不是“比起新时期的短篇小说并不逊色”,而是要更加成熟得多,好得多。因为毕竟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摸索,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更加成熟,新时期好的短篇相对要少一些,中篇好像要多一些。短篇小说需要的是极其敏锐的艺术感觉,而中篇则需要更多的内心感受和生活积累。你说得对,现在的短篇小说得不到更多的读者的喜爱,因为短篇小说真正是高屋建瓴的文学式样,也许可以说,读者相对减少倒是好事,是因为短篇小说越来越纯粹了。
段: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的遭遇,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前整个短篇小说的生存状态,它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20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短篇小说可谓一方重镇,可谓文学的“排头兵”,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涌现一批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诞生一批优秀的短创、说作品,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爆发的70年代中期。短篇小说已成为一个经典文学谱系,载入文学史册,并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文学积淀和精神财富。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从“伤痕”到“反思”,从“改革”到“寻根”,从“实验”到“现实主义回归”,短篇小说始终充当着思想“启蒙”和艺术创新的重要使命,与社会的推进和文学的发展—路同行。但从90年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开始,短篇小说突然落伍了、失语了,在读者的视野中渐行渐远了,成为一种落寞的文体。为什么呢?因为对大众“启蒙”的使命,让思想文化读物、各种媒体给抢走了,它们比短篇小说更快捷、有力。而从反映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角度看,短篇小说的优势又明显弱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90年代之后是一个艺术回归的时代,回到文化传统、现实主义、本土经验成为一种潮流,这样艺术创新的使命也不需要短篇小说来承担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文学背景下,短篇小说就有点“穷途末路”了。不过,当我回顾了90年代以来的短篇小说轨迹时,我惊喜地发现,它又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优势和位置。那就是表现对象上的底层性,思想内涵上的文化性,艺术品格上的严肃性。它依然坚守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当然不是每个短篇小说都具有这种特色,但它确实是短篇小说的一种基本趋向。现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随笔等等,都有点禁不住诱惑,同世俗合流了,惟有短篇小说贫贱不移,坚贞如故。它反映现实、提出问题的优势也许有所丢失,但在表现生活的纵深、人物精神的高远、审美境界的精湛方面,它又向前拓展了一大步。譬如从第一届到第三届的鲁迅文学奖获奖短篇小说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短篇小说在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强化和扩展,这是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的一个新变化。
王:阅读其实很简单,一般读者希望在小说里看到更多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好像一般都不喜欢在艺术上动脑子,希望直接、或者是希望来得更直接一些,昆曲和其它剧种受冷落与这也分不开,快餐在街市上大行其道,快餐文学也不示弱,就是这么个道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像,如郭敬明和韩寒二位的小说,二位的读者可以说是红男绿女满坑满谷,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他们的东西就很好。我认为用某种文学现象并不能真正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你说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真是很对,可以说,好的短篇小说就是这么个立场,要是某个短篇小说一下子拥有了一两亿读者那就是怪事了。短篇小说不是那回事。长篇中篇与世俗同流合污这句话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儿,小说就是要通俗,就是要努力通俗,就是要与世俗一起江河俱下。这里里谈到的是文体的品格,好像是,短篇不能这个样子,一是容积,二是由容积带来的种种限制,如果说长篇和中篇是让人们来看,而短篇却是让人们来想,问题是现在的人们不怎么爱想,不怎么爱思考。短篇和中长篇最大的区别我认为是在这里。当然还有另一种型态的短篇,比如希区科克的悬念小说。但我说的不是这类短篇。说一下刘庆邦,庆邦的短篇成就有目共睹,但他的短篇你要是让一般读者来读,他们会不会喜欢?会不会掩卷深思,我想不会,但我会,我算不算读者一分子,当然算,我代表了哪些读者?问题是,你面对一个短篇,一是不要希望它给你更稠密的故事。二是短篇要是写到三四万字它还会不会是短篇。短篇小说的型态太像是一颗手榴弹,看上去是小小的一颗,炸开来却是一大片,烟雾腾腾鬼哭狼嚎的。但一般读者更希望看到一个弹药库在那里,有琳琅满目的内容,这一点,短篇小说永远也办不到。短篇小说恐怕难以以宽广取胜,但可以深,是一眼细细的深井,让人一下子看不出有多深。
短篇小说的困境及其原因
段:短篇小说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实在是有着复杂的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的。也就是说,短篇小说是在外患内忧的夹击下才开始衰落的。从外部原因看,短篇小说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新时期文学阶段,国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那是一个崇尚精神的时代,文学有主流意识形态支撑,文学也靠国家养活。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社会逐渐展开和
大化的经济规律成为人们所有行为的主导观念。文学作品的全部生产机制——如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纸等,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读者?能不能赚钱?长篇小说、纪实文学有利润,就拼命地出。短篇小主要赔钱,对不起,靠边站。大小书店的长篇小说快要“泛滥成灾”了,但你能看到纯粹的短篇小说集吗?别说是一般作家的短篇集,那些著名作家的短篇集也不敢贸然去出。出版社是这样,报纸副刊则几乎取消了短篇小说栏目。文学刊物(特别是月刊)过去是以发表短篇小说为主的一块园地,现在也逐渐在变,有的发开了长篇或长篇节选,有的则以中篇小说为主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权威刊物,现在中篇小说把短篇小说挤得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了。发表园地的大量流失,怎么会有短篇小说的振兴呢?从短篇小说的阅读市场来看也不容乐观。现在人们的阅读趣味越来越向通俗、休闲、纪实几个方面分流,而短篇小说很难提供这样的东西。有人说短篇小说是一种“不走运”的文体,这话有道理。
王:这真正是一件让人悲伤的事情,去一趟书店还真是有这种感受,短篇小说集子越来越少,出版社向钱看这谁也没有办法,你总不能让他们朝短篇小说看齐。这就更需要作家坚守,这是对作家的一种考验,主要问题是,读者还是想在小说里看到更多的东西,就像是饿汉,要吃大量的东西,这说明我们的读者还处在相对低级的阶段,还不会精挑细选。另一个原因还在于,现在的书籍和出版物定价太高,一本纯文学杂志的价格是火车上卖的车厢本的五六倍,一般人,读书并不是为了受教育和接受艺术培训,而是为了消遣,一本书,看过就扔,从这一点出发,他们更可能选择车厢本,便宜热闹。打动他们的是故事和情节。可以说这是短篇小说不景气的外部原因。
段:从短篇小说的内部层面看,我想问题主要在作家身上。据一份文学调查报告说,现在的读者还是喜欢读短篇小说的,但好的短篇小说却日见稀少,因此使读者“冷落”了短篇小说。而作家不能提供更多的优秀短篇小说,原因又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经济原因,我们的稿费制度始终是以字数计算,写一个短篇小说并不容易,但稿费只有几百元,且基本没有如长篇小说那样的后续利益(如再版费,改编影视剧费等)。这大大挫伤了作家写短篇小说的积极性,而我们现在的作家是很看重稿费的,有些作家要靠稿费生存的。因此,我对那些坚持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始终怀有敬意!其次是作家在短篇小说上创新不够。短篇小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对作家的要求很高。在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短篇小说如何“与时俱进”,如何适应读者的审美需求,对作家又是一个新挑战,这就使短篇小说的创作难上加难。面对这种种考验,我们的不少作家放弃了在思想艺术上的艰苦探索和执著追求,使短篇小说难能有大的突破和超越。因此,短篇小说今天的不景气,作家是“难辞其咎”的。
王:首先要说的一点是,短篇小说很难给一个作家带来大收入。这一点简直是要命,比如说,你有一片地,你要考虑种什么?是种能赖以度日的庄稼还是种只能看几眼的牡丹?可能许多作家都基于这种考虑,短篇的产量小这可能是一个主要原因,中篇就要好得多。但最最根本的问题我认为还是短篇小说在写作上要求太苛刻。是可遇而不可求,就好像雨后你到林子里采蘑菇的那么个意思,东找西找,找老半天没有,不想再找了,却突然发现前边有一个大蘑菇在等着你。说到短篇,手头技术是一个大问题,你可以在冰场上滑冰滑得很好,但你很难在桌面那么一大块冰上千姿百态。说到家,小说的长度不同,对语言和叙述的要求就有所不同,长篇的开头可以一下子就来三四千字,而一个短篇也许全篇才只有三四千字。
短篇在写作上让作家感到尴尬的是,你写了一个短篇,又写了一个短篇,你写了十个短篇,跟着又写了十个,问题就来了,看一看自己的短篇小说,你有种感觉,就仿佛自己站在波斯菊的花圃旁,你会发现所有的波斯菊的花朵都是那个样子!让你感到不安的是,你的短篇在手法上竟然差不多,一个作家,要摆脱自己很不容易,中篇可以由故事来让这一篇和那一篇有明显的不同,而短篇却是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个人认为,他始终是在寻找着以前没有用过的一种结构,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的手法。你说得对,短篇今天的不景气,作家“难辞其咎”,短篇这种形式太难把握了,你把一种结构方法把握得纯熟了,也就说你已经死亡了,你要再生,必须再把握新的方法。一句话,我同意你的说法:短篇小说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对作家的要求都很高。所以,这就要求作家一次次潜到深水里去,你感到你快要憋死了,你也许才会发现有一个珍珠蚌在你的眼前。
短篇小说的“写什么”和“怎样写”
段:文学创作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写什么”,另一个是“怎样写”。我觉得中国作家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操练,在短篇小说的艺术表现上,“怎样写”的问题不能说完全解决,也可以说障碍不大了。而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却常常显得很不自觉。因为表现的对象或者说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表现方式方法只有相对稳定性。回顾10多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们会发现一些优秀作品的表现内容,正在发生一种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如史铁生的《老屋小记》写的是“文革”时期,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几个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他们黯淡的人生和不息的追求。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写的是一个人赘女方的老农民失手打傻了养子,他一辈子的悔恨和赎罪。如刘庆邦的《鞋》表现了“文革”年代,一个农村姑娘淳朴美好的人性和她对爱情的忠贞、神往。如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写一个上等兵与驴的有趣故事,营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你的《上边》,用你的话说写的是人情温暖,养父母与养子之间那种浓郁的亲情。但其背景是农业文明的衰落与现代文明的取而代之,小小的事件背后有一个宽广的文化背景。这几篇小说都是鲁迅文学奖的代表性作品。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90年代以后的短篇小说,不再粘滞于现实生活的具体事件和具体问题上了,而是把笔触指向一个更深广的社会认生、文化哲理层面上,努力强化小说的纵深度,创造一个丰富而幽深的形而上的精神天地,让读者自由地去想象、去思索、去审美。扩展小说的纵深度,这自然届于“写什么”的范畴。
王:崇轩老兄,我不太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摆在面前的问题应该是“怎样写”。因为一个听起来不怎么样的故事却往往可以写成一篇特别好的短篇,而恰恰是一个听上去十分好的故事却有时候无法写成一个好短篇。王安忆的那个短篇《羊》,要是给一般人绝对是无法写成一个短篇的,而王安忆写了,而且很好,这里就有一个写的问题。还有就是贾平凹最近的一个短篇,说来巧,题目是《羊事》,也写得十分漂亮,平平地写起,平平地叙述下去,到了结尾让人吃一惊。老贾的这篇小说要是让一般人写也是无法写好,或者是根本就无法写成一个短篇,但老贾做到
了。这里也要说到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中篇小说确实是要考虑写什么,当然也一定会考虑怎么写?但更重要的是写什么。而短篇更重要的是怎么写。还有就是刘庆邦的《梅妞放羊》,给一般人也是无法成篇的,但刘庆邦把这个短篇写得有多么动人。所以说,短篇小说写作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怎么写”。这要看一个作家的本事如何,所以说短篇小说的写作“写什么”倒不是很重要。
段:许多短篇小说作家说过:短篇小说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艺术。记得王蒙讲过:短篇小说的最大特征是“机智巧妙”。短篇小说必须有一个自然天成而又妙不可言的故事情节,这样的故事情节是很难想象出来的,要靠你在生活中的发现,要靠你的灵感闪现。过去有这样一个故事情节,经过作家的精心编织、简练叙述,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篇好短篇来。但现在短篇小说对作家的要求就不那么简单了,它不仅要求有一个好的故事情节,同时需要作家把全部的感性、思想、个性、境界等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形成一个独特的文本。这里关键在于你的生活阅历的广度和深度,你的感性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你的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的广度和深度等等。没有作家主体的广度和深度,自然就不会有短篇小说的纵深度。我在给你写的作家论中,特别阐释了你创作中表现的“人文关怀”精神:你对底层民众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你总是站在文化的角度去观照乡村和城市,你的小说浸润了一种古典文化的底蕴。正是这种人文的、文化的东西使你的短篇别具一格,脱颖而出。这跟当前短篇小说的文化走向是不谋而合的。
王:那妙不可言的东西往往是隐藏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事情里边,要靠慧眼去发现,我常说作家要有“白日见鬼”的本领,也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作家,他的思维要与众不同,只有有与众不同的思维才可能有与众不同的表现。令人激赏的那些短篇之作往往是让人看了之后会吃一惊,会让人想,这几乎无法写成小说的东西怎么会让这位作家写得这样动人?好的短篇往往不是那种千奇百怪的东西,好的短篇常常是从平平常常的事件里生发出来的一种不平常,千奇百怪是侦破小说的事。说到文化,文化是个好东西,文化可以是一个潜水装置,有了它,你可以深入到水底,水底世界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你深入不到那水底你就看不到那些东西。我更注意情感的深度和广度,这个深度和广度有时候要比生活和阅历的深度和广度还重要。这也许就是你说的作家主体的深度和广度,我认为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说到“人文关怀”,还是那句老话,一个作家要有同情心,要有正义感,要有斗争性。古往今来的好作家大都如此,你说《西游记》没有这三点吗?《红楼梦》就更不用说。我不敢说我的小说别具一格,但我愿继续努力,争取写得更好—些。
为什么要把短篇小说的写作进行下去
段:小说是一个成员较多的大家族,但现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影响了整个小说质量的提升。长篇小说最热闹,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繁荣期,但虚肿现象严重。中篇小说稳步发展,有质量的作品时有涌现。小小说(亦称“微型小说”)近年来很是活跃,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惟有短篇小说,不仅数量在减少,高质量的作品也越来越难产。它是最恪守小说的本质精神的,但它的处境最尴尬。
认真读一读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你会觉得它现在成熟多了、厚实多了,而且依然有许多实力派作家,对短篇写作痴情不改,孜孜坚持。譬如王安忆、铁凝、苏童、迟子建、刘庆邦、阿成、聂鑫森等等。这是可以让人感到安慰和自信的。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短篇小说现在处于一种困难时期。就它的本身看,我以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我并不主张短篇小说都去“零距离”地反映现实,但它也不应该一味地去回避现实生活。既要敏锐地贴近现实而又能透过现实表现出更深广的世界来,这大约是应当把握的一个“理想距离”。二是它的思想探索。短篇小说坚持探索—些社会、人生中的严肃问题、深层问题,这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是这些问题一定要同广大读者能够沟通和共鸣,这样才能走向社会、走向人心。三是艺术创新问题。现在作家的艺术技巧熟练多了,但越是熟练就越要警惕它的模式化、机械化。我觉得目前作家在短篇小说的艺术探索上,存在着动力不足,目标不高的倾向。
王:短篇小说和其它文学形式都不应该回避现实,就好像生命不应该回避血液和呼吸一样重要,小小说的活跃是正常的,所谓的车厢文学就是要以小小说为主力军,人们的时间很有限,在厕所里,在枕头上,在车上和飞机上人们不可能读大部头小说。时至今日,读大部头小说是一种奢侈,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事情,我不是说读大部头不好,是现在的人们很少有那种时间,但读小小说还是可行的。仔细想一想,我倒有些憎恨电视和电脑,它们使文学萎缩,我小的时候想看一回电影都不很容易,关在家里没事想看也是书不想看也是书,这倒从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我。现在的年轻的一代正受着各种媒体的迫害,脑子越来越被动,一双眼随着电视屏幕活动的时候脑子其实也被牵了鼻子走。这很可怕,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与动脑子分不开的,我小时候想要让父亲买一把玩具手枪,父亲不给买,我就自己做一把玩儿,做的过程就是创造的过程。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看《说唐》与《瓦岗寨》看到李元霸那一节,他手里的锤让我激动不已。我在心里想像那个锤会是什么样?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这也是一种创造,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是通过电视看,不用想像,我们这一代和现在的孩子们的最大区别之一我认为还是想像与不用想像之间。想像是一种创造。你说的短篇小说存在的三个问题很重要:反映现实,思想深度,艺术探索。尤其是艺术探索;短篇小说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加突出,众多的作家在那里探索,其实就是要自己不要模式化、机械化,不要自己抄袭自己,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短篇小说是一种很容易让一个作家不断重复自己的文学形式,中篇和长篇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就不多。短篇小说会把一个作家写死了,这很可怕。所以说,短篇作家在写写短篇之后—-定要写写中长篇,让自己摆脱一下,也是一种调整。目前写短篇,不是目标不高,而是没有目标,不知道目标在什么地方,不知该往什么地方发力。
段:雷达先生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们都应该提倡短篇小说,鼓励短篇创作”。这是明智之言。从短篇小说的社会价值看,它所探索和表现的往往是一种有关社会、人生的深度思想,而市场经济社会所流行的是一种功利主义式的浅度思维,这对于抵抗庸俗、维护思想的尊严是一剂“良药”。从短篇小说的文体价值看,它不仅是一个作家写作训练的最佳途径。同时它在整个小说家族中,有点像足球场上的“前锋”队员,肩负着引领、突破、压阵的作用,它在思想上的探索和艺术上的创新,对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乃至小小说创作,都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目前整个小说创作中的媚俗、虚肿、粗糙等现象,无疑跟短篇小说的疲软有关。因此我们期待着短篇小说的重振雄风。你作为一个有志于短篇小说的作家,也期待着你写出更多更好的精品来。
王:我认为为了与这个时代合拍,也应该提倡短篇小说,鼓励短篇小说的创作,但最最要命的是功利主义在现在大行其道,我们知道短篇不可能给作家带来更多的金钱,所以媚俗、虚肿、粗糙会纷至沓来,沙子从来都多于金子,要是中国一下子出现一百个优秀短篇小说家那倒是一种怪事,宝塔的顶部永远只是那么一点点,坚持者自在坚持,不坚持者且让他们流向他方,这不是能够强求的事,世事如此,何况文学,何况短篇小说。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行为是一次次生命的焕发,作家也是如此,是生命的必然而不是技巧的演出,他必须从生命深处喜欢这件事,我惟愿我的生命和情感还能够让我开放出更好的短篇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