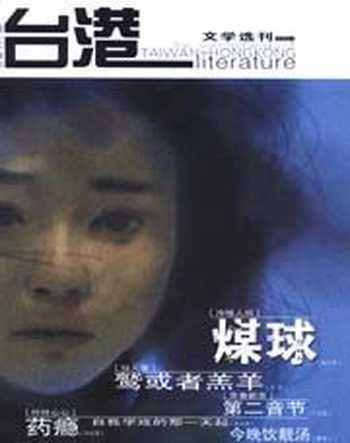说书乐
2005-04-29正芳
正 芳

从前在中国大陆,一般民间娱乐场所,除了电影院、戏园子,应属说书场吧。说书场地方都不大,能容下五六十个听众的已经不算小了。有些在茶楼酒肆中附设的说书场,只有二三十个座位,甚至更少。座位多为长条板凳。讲台上(有的没有台)是一张小书桌、一把椅子。桌上放一杯茶、一本翻开的书;但说书者从来不看,书上的情节对话,他早就背得滚瓜烂熟。说书先生的样子多半很斯文,身着灰布或蓝布长袍、青布鞋,天热时手上还少不了一把折扇。他像老师上课一样走到讲台上,常常是先坐下来开讲,讲到兴起时便眉飞色舞地起身离座,随着书中情节而表演。声音表情、肢体语言并用,听众便不由得不跟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如痴如醉,以致不少人每到说书时间,必会前去捧场,很像现代有些人迷电视连续剧一样。开讲的内容包罗很广,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济公传、西游记以及社会言情、武侠小说等等,都是说书的好材料。当时,教育不普及,不能阅读的人很多,借着听书可以增进不少知识。这确是一项很好的社会文教活动。
三十多年前在台北的淡水河畔,曾有一处露天说书场,在夏季营业。星期日约二三好友,闲坐其中,一面喝茶,一面听书,河上清风阵阵吹送,心情十分愉悦舒畅。
在我家里也曾有过一个小小说书场,听众只有四人,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湘西沅陵,与县城隔着一条河的太常村里,沿河一条小路边,有茅屋三间,就是我的家。一对年纪不算大的夫妇带着一女两儿,住在那里过着简朴得近于穷困的日子。但是,由于对抗战胜利都怀着希望和信心,生活虽然艰苦,仍在苦中有乐。记得那时最感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到图书馆去借书。正巧那时县立图书馆为防敌机轰炸,从对岸搬到了乡下。由我家走完一条村中大路,再穿过几条田间小径,不到一小时工夫,就到达图书馆了。我们姐弟三人常常跑去借书,每人都借好几本带回家看。闲暇时刻,一家人除了母亲坐在椅上纳鞋底外,都捧着书本看得津津有味。母亲小时没正式念过书,自学的一点词汇有限,没有能力阅读。
有一天,我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念书给母亲听?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从那天起,晚饭后就成了我家的说书时间。到时候先把煤油灯加满煤油,擦亮玻璃灯罩,把灯芯捻高,泡上一壶茶,便准备开始说书。由父亲、大弟和我轮流任说书人,母亲和尚在念小学的小弟是纯听众。说书与讲故事或念书不同:讲故事不够细腻,念书则生硬无趣,而说书有点像上演一人兼饰数角但不化妆的连续剧,外加旁白,颇能引人入胜。
一开始,我们这三个说书人只能对着书念,略去或变换书中比较难懂的词句。渐渐地熟能生巧;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都能把书中的对话在语气、声量、音色等方面尽量说得传神,叙述部分也尽量投入感情,控制声音的抑扬顿挫,终于使念书步向了说书的境界。母亲和小弟都听得十分着迷。为了慰劳我们,在夏天,母亲常煮好一锅价廉味美的绿豆汤给大家消夜。喝完绿豆汤,休息一会,大家再拿起蒲扇,轻摇着进入大观园或花果山,直逛到深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冬天,我们常在火盆的炭灰里埋入一些红薯或苗人背下山来兜售的板栗,一时烤红薯发出甜香,栗子噼啪轻声爆裂,这时屋外虽有微雪,而在这间茅屋里,每个人的心里却都装满了快乐与安宁。
一批书说完了,赶紧又去换借一批。两三年下来,图书馆里较精彩的小说几乎都让我们说完了。接下去便借翻译小说。无论哪一类,母亲都爱听而且十分专注地听。母亲的记忆力极好,说过的书她都记得。每当谈起书中人物,像诸葛亮、宋江、多九公、虎妞、金燕熙、沈凤喜、孟丽君……甚至洋人大卫·克博菲尔、简爱、郝思嘉等等,她都对他们熟悉得像谈起亲朋好友一样。母亲好像交了许多新朋友,心里非常高兴。
回首前尘往事,匆匆已逾四十年。如今父母亲均已作古,弟弟们则天各一方,但每次想起昔日在斗室中的说书情趣,怅惘之外,仍能感到一些温馨与甜蜜。
(选自台湾《一条流动的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