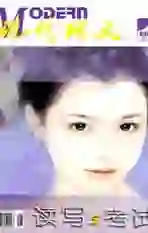蟋蟀的住屋(节选)
2005-03-11法布尔
法布尔
在朝着阳光的堤岸上,青草丛中,隐着一个倾斜的隧道,这里就是有骤雨,即刻也就会干的。这隧道最多是九寸深,不过一指宽,依着土地的天然状况或弯曲或成直线。差不多像定例一样,总有一丛草将这所住屋半掩着,其作用如一间门洞,将进出的孔道隐于阴影之下。蟋蟀出来吃周围的嫩草时,决不碰及这一丛草。那微斜的门口,仔细耙扫,收拾得很广阔;这就是它的平台,当四围的事物都很平静时,蟋蟀就坐在这里弹它的四弦提琴。
屋子的内部并不奢华,有光泽、但并不粗糙的墙。住户很有闲暇去修理任何粗糙的地方。隧道之底就是卧室,这里比别处修饰得略精细,并且宽大些。大体上讲,是一个很简单的住所,非常清洁,没有潮湿,一切都合乎卫生的条件。在另一方面说来,假使我们想到蟋蟀用以掘地的工具的简单,这真是一件伟大的工程了。如果我们要知道它怎样做的和它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们一定要从蟋蟀刚刚下卵的时候讲起。
蟋蟀像白面孔螽斯一样把卵单个的产在深约一寸的四分之三的土里。它将它们排列成群,大约总数有五百到六百个。这卵真是一种惊人的机械。孵化以后,看来如一只不透光的灰白色的长瓶,顶上有一个圆而整齐的孔。孔边上有一顶小帽,像一个盖子。这盖的去掉,并不是因为蛴螬在里面冲撞而破裂,而是沿着一条环绕着的线——一种预备下的抵抗力很弱的线条——自己裂开来的。
当它出去以后,卵壳还是长形的,依旧光滑、完整、浮白,帽子挂在口上的一边。鸡蛋的破裂,是被小鸡嘴尖上生的小硬瘤撞破的;蟋蟀的卵做得更机巧,和象牙盒子相似,能把盖打开。小动物的头顶,已足够做这件工作了。
当它脱去襁褓时,蟋蟀差不多完全是灰白色的,开始和当前的泥土战斗。它用大颚咬出来,将一些毫无抵抗力的泥土扫在旁边和踢到后面去。它很快的就在土面上,享受着日光,并冒着和它同类冲突的危险。它是这样弱小的可怜虫,还不如一个跳蚤大。二十四小时以后,它变成黑色,它的黑檀色足以和发育完全的蟋蟀媲美。它原来的灰白色所仅遗留下的,只是一条白带,围绕着胸部。它非常灵敏和活泼,不时用长而时常颤动的触须试探四周的情况,并且激烈的到处奔跑跳跃。总有一天,它会胖得不能如此任性的耍闹。
我花园中的蟋蟀,被蚂蚁残杀尽,使我不得不跑到外面去寻找它们。八月,在落叶中的草还没有完全被太阳晒枯,我看到新生的蟋蟀已经比较的大,现在已全身都是黑色,白胸带的痕迹一点也不存在了。在这个时期,它的生活是流浪的;一片枯叶,一块扁石头,已足够应付它的需要了。
一直要到十月之末,寒气开始迫人时,它们才动手造巢穴。如果以我观察关在笼中的蟋蟀来判断,这项工作是很简单的。掘穴决不在裸露的地面着手,而是常常在莴苣叶——残留下来的食物——掩盖的地点。这是替代草丛的,似乎为了使它的住宅秘密起见,那是不可缺少的。
这位矿工用前足扒上,并用大颚的钳子,拔去较大的砾块。我看到它用强有力的后足踏,后腿上有二排锯齿;同时我也看到它扫清尘土,推到后面,将它倾斜的铺开。这样,你可以知道它全部的方法了。
工作开始做得很快。在我笼子里的土中,它钻在底下两小时,它不时地到进出道口来,但常常是向后面不停的扫着。如果它感到疲劳,它可以在未完工的家门口休息一会,头朝着外面,触须无力的在摆动。不久它又进去,用钳子和耙继续工作。后来休息的时间渐渐加长,使我有些不耐烦了。
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完成。洞有两寸深,已足供暂时的需用了。余下的是长时间的工作,可以慢慢地做,今天做一点,明天做一点。这个洞可以随天气的变冷和身体的增大而加深加阔。即使在冬天,只要气候还比较温和,太阳晒在住宅的门口时,还是可以看见蟋蟀从里面抛出泥土来。在春季享乐的天气里,这住宅的修理工作仍然继续不已。改良和修饰的工作,总是不断的在进行着,直到主人死去。
四月之末,蟋蟀开始唱歌;最初是生疏而羞涩的独唱,不久,就成合奏乐,每块泥土都夸赞它的奏乐者了。我乐意将它列于春天唱歌者之首。它们的歌单调而无艺术性,但它的缺乏艺术性和它苏生之单纯喜悦正相适合,这是惊醒的歌颂,也是萌芽的种子和初生的叶片所了解的歌颂。摇荡在日光下,散布着芬芳的欧薄荷,把田野染成灰蓝色,即使百灵鸟停止了歌声,田野仍然可以由这些淳朴的歌手得到一曲赞美之歌。